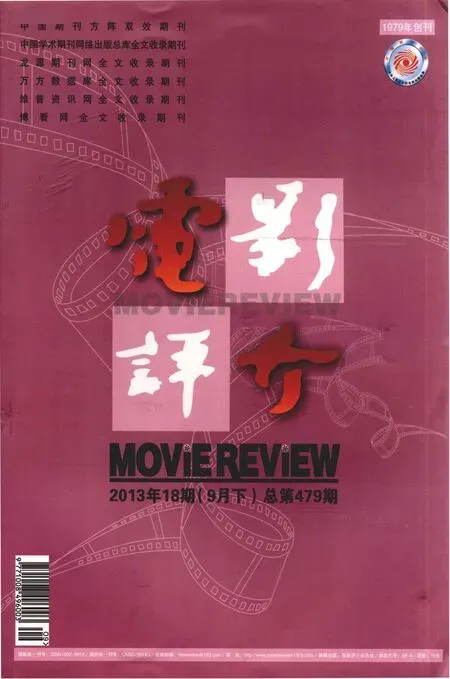昆汀·塔伦蒂诺:从《低俗小说》到《无耻混蛋》——论独立电影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融合
□文/宋书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生

电影《低俗小说》海报

电影《无耻混蛋》海报
“独立电影”,传统地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指“非哥伦比亚、迪斯尼、米高梅、派拉蒙、环球或华纳兄弟公司制作的任何故事片”,其通常具有低成本、去明星化、代表少数族裔及边缘亚文化等特征,也正是基于其低成本、低投入和简陋的道具布景,为了强化影片质量,80年代催生了独立电影对艺术品质和艺术创新的强调,而以艺术片为主流形态呈现,艺术追求普遍大于商业诉求。因而当时的独立电影,无论在价值取向还是艺术表现上都与主流商业的大制片厂体制呈截然对立之势。
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独立电影人艺术理念、独立制片发行公司财政状况、主流制片厂的市场策略、技术进步等主客观因素的变迁,独立电影界的面貌自内而外受到了新的冲击。期间出现了以昆汀·塔伦蒂诺作品为代表的一部分集艺术品质与商业潜力于一身的优秀电影,即通常电影人所指的“中间地带”影片。市场逻辑开始广泛渗入独立电影人思维,使他们自发地致力于开掘商业与艺术双赢的“中间地带”电影,意图借助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将独立电影所负载的价值理念注入到受众中去。
1994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的《低俗小说》可以说是昆汀·塔伦蒂诺第一部大规模成功的“中间地带”影片。一方面它斩获1994年法国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一方面以850万美元的成本预算收回全球2.129亿美元票房的商业成功成为第一部票房超亿元的独立电影。而2009年公映的《无耻混蛋》作为昆汀以电影作者的身份自编自导的一部作品,并取得了当时票房上的空前成功,它保留了昆式电影的纯正血统,并包含着距《低俗小说》15年时差的昆式电影发展动态。以下本文将从四个角度对比两部影片的异同。
一、叙事策略
《低俗小说》全片采取了片段化叙事的策略,中间3个片段分别标有小标题,各段落内部基本保持着线性叙事的规律。各片段前后间没有顺承关系,而每一段落各有自己的情节侧重点,每一段落的主角也各有千秋。文森特这一人物虽贯穿全片,但在各个片段中的地位有主有次,在段落4中他已死去,却又活着出现在段落6中。事实上作者颠覆了观众对传统电影线性叙事的审美陈规,将影片的时序打乱,巧妙利用一系列线索镜头将各个片段连接成一个整体,使全片叙述呈环状。
《低俗小说》叙事策略的高明在于这种拼贴并非无意义的游戏,无论这种效果是出于导演的主观或偶然,影片通过这一整个人物系统错综复杂的前后关系,反映出个人命运的无常感和历史的偶然性,而这与电影故事中朱尔斯对“神迹”的顿悟有一种似非而是的天然关系,可以说实现了形式为主题服务的功能。对于电影观众而言,虽然全片的事实尽收眼底,但通过叙述的多重视角、对时序的打乱,对事实全景的掌握却并不信手拈来,这更像是与导演的一场智力博弈,在这里,观众不是像主流商业电影中一样一味地被动接受视觉奇观,反而作为一名参与者要绞尽脑汁玩一场“拼图游戏”。
影片《无耻混蛋》的叙事仿照了章回体小说样式,将全片分为5章分别命名。表面虽延续了昆汀的片段式风格,但与《低俗小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不难看清其分为两条线索:一,法国女孩肖桑娜的复仇,这部分内容由一、三、五章叙述;二,“无耻混蛋”对纳粹的破坏活动,由二、四、五章叙述。两条线索都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情节,两股线索在第五章交会,从而达到全片的高潮。汉斯·兰达在两条线索中都作为关键人物出现,此外还有较次要的线索人物盖世太保、希特勒等在其中穿插,使得影片具有整体感。
昆汀给观众安排了一个全知的视角来呈现,观众在观看体验中是被动的主体,在电影精神分析学学术语来说,它更接近于主流商业片观看的“口腔期”观影状态,更为下文将要分析的暴力奇观的呈现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暴力呈现
暴力呈现问题是谈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而他的暴力美学从早期到眼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从表现形式到价值理念,都表现出一种与主流市场需求融合的倾向。
《低俗小说》中的暴力呈现可基本分为以下三类:1.对暴力场景的间接口述。对话成为描述暴力的工具,对暴力场景及其后果的感知更多依靠观众能动性的联想。2.强调暴力动作,不直接展示暴力效果。在这些镜头段落中,昆汀集中表现的是施暴动作,摄影机对准枪口,但不表现被杀对象或一掠而过,不着重突出被杀对象的惨状,而用这部分内容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3.暴力动作和暴力效果血淋淋的呈现。对于这些镜头的表现,影片遵从了现实主义原则,全无艺术手法的渲染,全部使用自然音响,用以假乱真的血浆,以一种黑色的、近乎冷酷的逼真扑向观众。
因此《低俗小说》的暴力是一种中立性的暴力,它摒弃了传统电影深厚的道德感,既没有对暴力作出负向的评价,也没有通过艺术手段对暴力进行美化,只负责忠实地表现暴力而不评价暴力。“就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说,其实是一种把责任和选择交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电影不再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电影也不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它认为电影提供的是一种纯粹审美判断。”(郝建:《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载《当代电影》2002年5期,95页)
《无耻混蛋》的暴力与《低俗小说》的暴力有所不同,首先它完全将施虐与受虐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直观呈现,没有丝毫含蓄的空间。并且在此基础上其暴力呈现还显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对暴力场景的逼真展示,但在这种真实展示中还掺入了更多创意,将重心放在突出杀人方式的新奇感和仪式化。这种做法将暴力作为一种奇观和视觉刺激来满足观众的窥探欲,散发出浓重的戏剧化、浪漫化气息。除了在剧本中营造强烈的戏剧冲突,昆汀还充分调动近距离特写、快速剪辑、升格镜头等各种镜头语言,辅以音响、配乐、服装舞美极尽渲染,透出一股浓浓的香港电影暴力美学的诗化魅力和唯美主义,显现出一种经过包装的商品式的被兜售的美。
综上所述,《低俗小说》用虚实相生的暴力表现充分调动观众观影的能动性,用真实感、纪实性把对暴力的价值判断还给观众。这是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所造就的暴力美学。而《无耻混蛋》通过加强暴力场景的奇观化、仪式化、浪漫化和戏剧化大大强化了影片中暴力的尺度和暴力的可看性,迎合了好莱坞“商业美学”,却造成了“暴力美学”背后精神理念上的困境。
三、明星符号
昆汀·塔伦蒂诺电影并没有继承80年代独立电影去明星化的特质,但他的电影总是竭力把明星还原成一名演员,服务于电影本身。
《低俗小说》的演员表是典型的“瓶颈期演员+性格演员+新人”的“卡岑伯格”式卡司,这种状况为电影带来三重效果:一是能够最大程度削减片酬、压低预算;二是凭借瓶颈期演员过去的号召力和积攒的影迷基础为本片版权出售制造有利条件,提供高关注度和票房保证;第三,昆汀巧妙利用明星制为之打造的既定形象为《低俗小说》制造了对应于类型片的间离效果。间离效果是来自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一个概念,旨在破除舞台的真实幻觉,使观众跳出被动接受的状态,转而能对舞台表演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在昆汀语境中,“英雄”布鲁斯·威利斯化身落魄拳击手,卷赃款潜逃,歌舞明星特拉沃尔塔则变身黑社会小弟被老大的妻子逼着跳起一段畏首畏尾的扭腰舞。利用对明星既定形象的颠覆,破除了类型片幻觉,在充分灵活利用黑帮、暴力、毒品、性等等类型片元素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同时,又在观众心理进入类型片轨道之时忽而利用后现代舞台语言——在这里表现为变相错位的明星符号——取代类型片语言,使观众跳出一种语境进入另一种语境,造成鲜明的心理落差,在这种落差之间使观众充分体会昆汀电影的审美独创性和后现代电影的魅力。
《无耻混蛋》的明星构成则截然不同,相对保守地启用了布拉德·皮特和黛安·克鲁格。布拉德·皮特身为好莱坞2000万俱乐部成员,具有无可匹敌的明星号召力,中年转型后用“十X罗汉”系列等影片建立起痞子英雄形象,而黛安·克鲁格则是近年德国影坛到好莱坞发展最为顺风顺水的女演员之一,通过《特洛伊》、《国家宝藏》系列塑造起美丽典雅的智慧女性形象,并仍处于事业上升期。
客观地说,两人在《无耻混蛋》中的角色基本秉承了他们的既定形象,选角考虑的也许更多的是明星身上的票房贡献率,因此对明星魅力的突出也就成为了影片宣传活动的重点。以《无耻混蛋》的主宣传海报设计为例,布拉德·皮特全身像占据了前景处最靠前的中心位置;布拉德和黛安两人上半身基本正处于画面3:5的视觉中心,在区位上占据绝对强势。虽然黛安·克鲁格在片中的角色与起穿针引线作用的梅兰妮·罗兰的角色相比重要性要小,在影片宣传中却占据了仅次于布拉德·皮特的高曝光率。
四、价值理念
在《低俗小说》阶段,正如某些论者所言,昆汀所依赖的源泉就是政治不正确。除了上文提及的在叙事策略中巧妙贯穿的命运感和无常感的思考外,本片还包含着一种类似于“盗亦有道”的思想精神,将视线投向黑帮分子和社会底层人物,将他们的行为逻辑和昆汀意义上的真实面目呈现在主流社会面前来澄清此前好莱坞电影为其塑造的冷酷、堕落、卑鄙的类型化脸谱,将情义、侠义、尊重、信仰等价值观分片段阐释。在这个意义上,《低俗小说》时代的昆汀,他的故事和他的价值观还是一体化的,故事尚且是阐释其观点的载体之一。
事情发展到《无耻混蛋》,昆汀·塔伦蒂诺开始学着讲一个主流化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协约国一方仁人志士在与之斗争的历程里作出的艰苦努力和英勇牺牲。这是二战题材电影的常用套路。然而当观众津津乐道导演用天才的想象力篡改历史将希特勒炸死在电影院的时候,昆汀却并不严肃地想借此展开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而是借用这个故事框架无所不用其极地展示花哨的暴力片段,用以暴制暴的简单逻辑来搪塞观众的和平热情,打着历史的幌子应付主流社会的诉求。《无耻混蛋》里昆汀以一种顽童的态度戏说历史,正是这种态度构成了其负载的反叛性理念。此时,故事与理念是相互剥离的,但无论主流观众或黑色Cult电影的偏门影迷,各个层次的观众都能在这部影片中挖掘到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意义。
从《低俗小说》到《无耻混蛋》昆汀·塔伦蒂诺自始至终都称得上一名独立电影人。其早期创作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秉承了独立电影所褒扬的创造性精神,同时又灵活运用好莱坞文化工业的类型片符号为自身创造利润;到近期,则根据商业电影运作规则在“独立”这一命题的两个维度的权衡中作出了策略性调整:1.弱化电影题材的先锋性和尖锐性,呈现迎合主流价值的故事,却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将其极力简单化、框架化,将作者世界观、价值观的表达拖出故事之外;2.利用好莱坞主流电影对奇观性的强调与后现代电影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在照顾受众接受能力的前提下着重用各种手段在艺术表现上进行挖掘深化,反映出颇具有后现代性的精神反思。这种转变在昆汀看来也许只是其艺术风格顺其自然的延续,而对于独立电影产业而言却更是一种故意而为之的策略。不可否认,这种对策在实质上是某种程度上是妥协,而这种妥协是资本主义社会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必然结果。
- 电影评介的其它文章
- 《阿甘正传》:平民英雄形象的深层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