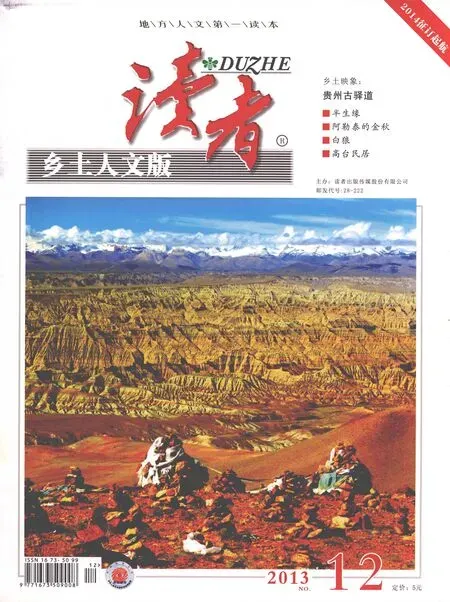行走的玉米
文/孙文胜 图/郭德鑫
行走的玉米
文/孙文胜 图/郭德鑫
种一茬玉米,汉子并没有获得太多想要的东西。但播种或劳作的过程,就像是和一些守信的朋友、敦厚淳朴的兄弟姐妹相处一段日子,有滋有味。来年,他还会种满地的玉米。这是一种默契。

从落地到收获,一百来天的生命之旅,玉米的一生注定是匆忙的。
开阔的田野里,锐利、金黄的麦茬亮铮铮的锋口直指苍天。黄牛在前面犁沟,汉子弓着腰身,在后边点种,一尺一窝,一窝两粒。地是施足了猪羊牛粪的,黑黑的、暄暄的,有一种待孕母性的丰满与厚实。
笸箩里那些黄灿灿的种子,是精心挑拣过的。女人点下一窝种子,就揉碎一把土坷垃,用潮湿的细土薄薄地盖好它们。那几天,汉子天不亮就进了地。在起初的天光里,他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随着太阳渐渐升高,迷离的光线里,会让你以为那是一个褐色的运动着的土疙瘩。汉子的颜色与土地的颜色是一样的。但走近了,你会看到细密的汗珠爬满了他的后背。那一颗颗晶莹的汗珠里,都映着一颗太阳。汗珠儿愈聚愈大,慢慢地汇成了一道小溪,然后顺着他的脊骨悄然流下。
播完种,要是恰逢一场大雨,那当然是上苍的恩赐;要是天旱,只能头顶骄阳往地里灌水了。地是睁眼地,加上麦茬绊磕,只见源头水流,不见地里水动,大半天也不见浇完一垄。地头送饭的娃娃,手搭凉棚,眯缝着眼,仰起锅盖头,对着一疙瘩云朵唱道:“龙王龙王你下来,我给你和面摊煎饼……”
汉子急,种子也不消停。它们躲着透过土粒渗进的阳光,拼命地吮吸着地缝里的湿气。吸着吸着,身体就发福了,还长满了抓紧泥土的毛爪子。这时想让它们死掉就不容易了,因为土地成了它们的娘。
浇完地,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孩子突然发现地角高处的几窝没浇上水,心里很是着急。父亲说:“不怕,玉米有灵性哩,能闻见水汽。”娃儿不信,第二天一早偷偷刨开一看,玉米种果然已经喝得滚圆滚圆了。
浇完水第三天,汉子轻轻地用小齿耙顺了一遍地。隔过一天,满地就蹦出了绿芽子。那星星点点的绿,在苍茫的原野上显得特别惹眼和惊艳。一阵风儿刮过,一场大雨落过,那苗儿就像初生的牛犊,带着一股蛮气,“噌噌”地往上蹿,不几天,满眼都被染绿了。
一路旅途劳顿,但夏末秋初时节,玉米却像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迎来了最妩媚的日子。那一阵儿,玉米的个子已高过了额头,舒展的叶子像柔软的手臂随风轻拂,那些穿着青衣的玉米棒儿,飘着粉色的璎珞,像少女羞涩的浅笑,让人怦然心动。它的顶上还冒出了鹅黄的穗子,那些仰天散开的发梢上,缀满了发夹样可人的小花。蜂蝶可以嘤嘤嗡嗡,人可不敢贸然采撷它,因为玉米叶边上的细刺,会在人的手上刻上一条条不太痛的印痕。
踏进白露,玉米完全像一个丰乳肥臀的孕妇了,它叶片粗大,秆儿高壮,怀里胖乎乎的棒子渐渐分身。剥开皮儿,珍珠般的粒儿密密地排列着,圆嘟嘟的颗粒已灌满了浆汁。早饭前,娃儿娘踩着露水扳回了一篮玉米棒子。汉子坐在门槛上磨锄。娃儿娘说:“娃儿念书太劳心了,青棒子补脑哩。”汉子不说话,手里的活儿也没停。棒子被剥了皮、摘了须,丢进锅里,一袋烟的工夫便满屋溢香。
屋里来了客人,娃儿娘又端出一盘煮熟的棒子。客人怕烫,娃儿娘就用筷子插上把儿。客人夸奖棒子,汉子低头不语,但磨锄的“嚓嚓”声更有力、更响亮了。吃饱了,喝足了,客人提起了大娃儿的婚事,汉子脸上落了一层愁意。客人说:“愁啥呢?你不是有满地的好玉米吗?”汉子扬起脸,眉头上已挂着喜色。那晚,汉子留下了客人,他端出了柿子酒,拿出了好旱烟。娃儿娘在地头摘回了鲜菜、棒子,又炒又煮,男人和客人直喝得月移西山、坛立人倒。
走过中秋,空气里弥漫着庄稼成熟的香气。玉米浑身金黄,硕大的棒子坠至腰间,已完全显出了老相。汉子吃完了月饼,就安排收玉米的事了。玉米能换来娃儿的学费,娃儿想帮忙,学校却要补课,娃儿手里拿着书本,心里就乱慌慌的。等回到家,院子已立满了一座座“金塔”。娃儿没事,就剥了棒子晒颗粒。娃儿想的是爆米花,娃儿娘想的是酸辣搅团、苞谷糁,汉子想啥呢?
种一茬玉米,汉子并没有获得太多想要的东西。但播种或劳作的过程,就像是和一些守信的朋友、敦厚淳朴的兄弟姐妹相处一段日子,有滋有味。来年,他还会种满地的玉米。这是一种默契。
(章 程摘自新浪网孙文胜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