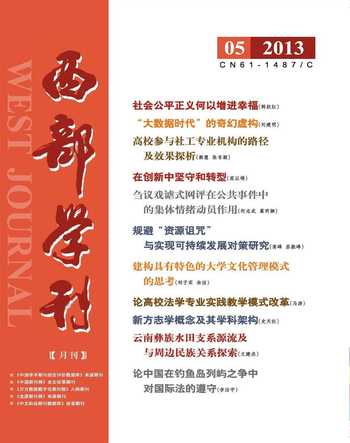检视启蒙:闰土之于鲁迅的独特意义
韩明港 高颜平
摘要:少年闰土是鲁迅《故乡》中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但是,如果认为鲁迅只是借闰土来怀想曾经的少年岁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闰土,作为一个内心纯白的少年,正符合鲁迅对“立人”——或说“国民性改造”——前提的设定。鲁迅试图以《故乡》对启蒙之路进行检视,少年闰土身上寄托了鲁迅对唤起民众的可能性的期待。闰土的变化,深深地动摇了鲁迅对启蒙的信心,因而,对故乡的亲近与逃离,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叙事结构,呐喊与质疑的混响,希望与绝望的复调成为作品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闰土;鲁迅;启蒙之梦;检视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故乡》中,“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似乎是“专为了别他而来”,为了搬家。但在叙述中,搬家显然不是主要内容,大量的笔墨最终落在了闰土身上,而鲁迅的希冀也伴随着对闰土的怀想和与之相见而发生着变化。
闰土,不仅是鲁迅寻找的旧友,也是鲁迅寻找的启蒙之梦。
一、鲁迅的启蒙之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道,“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P437这未被忘却的梦,就是鲁迅的启蒙梦。
面对家国危难,鲁迅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在努力探求着救亡强国之路,而鲁迅的设计是比较独特的。
在南京求学时,年轻的鲁迅已深受严复、梁启超的影响,到日本后,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日渐成熟。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2]P487后来鲁迅明确提出“立人”的解决办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在鲁迅的设想中,中国的危机根本上是“人”的危机,而解决的方式是人的重建,首要的问题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也就是国民性改造,因此鲁迅决定“首推文艺”,不是“黄金黑铁”的实业兴邦或“托言众治”的制度变革。只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P57
启蒙的关键是让人皆获此“自性”,“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国民精神发扬”,“大其国于天下”。其方式是,首先由“先觉者”发为雄声,振起国民。民众闻此妙音“灵府朗然”,“发扬踔立”而后“邦国亦以兴起”。显然这是一条由“首在立人”而终在“立国”的启蒙之路。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民皆可以“立”。在鲁迅看来,真正的人之“本心”,或被统治者“不撄人心”的“治心”政策湮灭了,或被“物欲”遮蔽了,不但失其本心,甚至参加了“吃人”的行列,故而难见“真人”。但是,有两类人应该还保存着这份纯白之心,一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一是“气禀未失之农人”。[3]P30
少年闰土,应当是有如此“纯白”之心的孩子,而成年的闰土,也应当是一位“气禀未失之农人”。
二、与闰土相遇:启蒙之基的动摇
鲁迅是抱着对少年闰土的良好怀想来到故乡的。他要寻找的是人内心的“纯白”,而这种“纯白之心”正是启蒙得以展开的前提。少年闰土健壮、勇敢、朴素、单纯,正符合鲁迅所设定的启蒙前提。在《故乡》灰色的调子和灰色的人物之中,少年闰土无疑是最鲜亮的,月下戴着银项圈的闰土是鲁迅深刻的记忆。鲁迅不惜用大量笔墨描写少年闰土,这不只因为闰土是鲁迅的乡情的寄托,更是因为,闰土寄托着鲁迅启蒙的梦想。
但闰土的出现击碎了鲁迅的想象。
闰土到来了,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却又不是“我”记忆中的闰土了。“我”回到了故乡,悲哀地发现闰土已经由一个“小英雄”变成了一个“木偶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是原因,但最让鲁迅失望的莫过于闰土的沉默与顺从,那一份健壮、勇敢、单纯、朴素的“纯白”之心已荡然无存。
正如前述,在鲁迅的想象中,由“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诗人”、“握拨一弹”,国民“心弦立应”,“灵府朗然”,而 “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此“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终“国民精神发扬”,自觉至,内曜外华,“人各有己”,必“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 [1]P45-120
但这里并没有鲁迅想象的“上征”之力,没有“白心”与“内曜”。“木偶人”的闰土,是麻木的、衰弱的、让人失望的。这并不是鲁迅要找的,有些内在真诚、纯白、朴素品格的闰土,这不是“气禀未失”的闰土,而恰是气禀皆失。当闰土叫出一声“老爷”时,“我”便知道彼此之间的对话已经不可能了,“我也说不出话”,因为“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白心”、“内曜”是鲁迅设定的启蒙的前提,“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灵府朗然”,是鲁迅想象的启蒙的方式与效果。没有“纯白”之心和未失之“气禀”,麻木闰土与“我”已无法交谈,对话的必要与可能也就不存在了,启蒙无以立基,方式效果,也无从谈起。
“我”要离开故乡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故乡,确切地说,是故乡的闰土,曾经不但牵扯着我的乡情,也寄托着我的梦想。而现在,“……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忽地模糊”了的闰土形象,正是鲁迅忽地模糊了的启蒙之路,这种“悲哀”并非只是乡情的溃散,而更是启蒙想象的破碎。
故乡,是鲁迅试图亲近的地方,也是鲁迅寻找启蒙之基和建构希望与梦想的地方,梦想溃散时,故乡自然“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而本有的希望也正在动摇之中,于是鲁迅只好逃离。
“我”忽然害怕起来,“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鲁迅的“希望”,是打破“铁屋子”的希望,是启蒙,而此时这个希望却因闰土的出现似乎已经变得“茫远”了。
三、闰土之于鲁迅的独特意义
鲁迅的设计是一条由“立人”而“立国”的启蒙之路。
人性善或可以向善是“人国”建立的必备条件,如果人性恶,那么“沙聚之邦”不可能“转为人国”,正如儒家哲学中必须设定人有“四端”——仁、义、礼、智——作为性善的保证,也是道德理想国的保证,荀子设定“人性恶”,但必须可以“化性成伪”,也就是改恶迁善,才能够保证他的国家逻辑的建立。
本善之人性和民众的“心弦立应”直接决定着启蒙的成败。在《故乡》中我之所以要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就是要寻找记忆中的“纯白”之心,找到那种“内曜”和“上征之力”。可以说,闰土身上寄托了鲁迅的启蒙想象。
与闰土的现实相遇,动摇了鲁迅的启蒙设计。鲁迅自己本十分确信的小英雄闰土能够确证自己的启蒙之路,而闰土的出现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鲁迅的启蒙想象,满怀的希望与期待也就变成了惶惑与失落。
闰土,是鲁迅设定的对启蒙的一个验证者,当然,他本希望让闰土确证自己的启蒙想象,然而闰土却最终拆解了启蒙,拆解了鲁迅的梦想。
长期以来,对《故乡》尤其是对闰土形象的解读,并没有从鲁迅的启蒙理想和启蒙之路来解读,所以并不能很好地领会到《故乡》的丰富性和鲁迅的复杂性。
四、“呐喊”与“质疑”:鲁迅启蒙小说的双重意味
在日本时的鲁迅就曾试办《新生》,但是很快“逃走了资本”,离散了同志,不能“纵谈将来的好梦了”。《新生》的失败使鲁迅明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如果说《新生》的失败,鲁迅只是对自己的能力的怀疑的话,多年之后在北京的鲁迅,则是对启蒙之路充满了疑虑。
曾经,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对启蒙非常地确信,但经过太多的人生变故和社会经历之后,显然鲁迅变得更加深沉。
面对老朋友钱玄同的力邀,鲁迅最终答应请求,但他给自己的定位,中介一个“呐喊”者。一方面,自己“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而另一方面自己对启蒙并不像以前那么确信。“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虽然答应了钱玄同,但是鲁迅并未放弃自己的怀疑,“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之所以答应写文章,一方面是因为“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一方面也为着自己摆脱无聊与寂寞。但是,鲁迅并未表现出对启蒙之路的学理意义上的赞同。
“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1]P439鲁迅的确信就是他的“怀疑”。
正因如此,《呐喊》与之后的《彷徨》,不只有鲁迅呼喊的声音,也有鲁迅质疑的思索,鲁迅试图用小说来验证启蒙。
首先要验证启蒙的前提。《狂人日记》将启蒙的希望寄托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在《故乡》中则进一步在这个健壮的孩子身上寻求“白心”不泯、并且健康成长的可能,而闰土的出现,的确让鲁迅深深地失望了。在另一篇作品《孤独者》中,鲁迅似乎要进行再一次的验证。“我”曾跟魏连殳讨论过孩子的问题。魏连殳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而“我”随便地否定了,“那也不尽然。”魏连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孩子,他说“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而“我”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三个月后,魏连殳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4]P88“白心”、“内曜”渺不可闻,而“坏根苗”却已昭然,鲁迅的启蒙失却了内在的依据与前提。
其次,即便有“白心”、“内曜”作为基础,启蒙的成功还需要一个条件:启蒙者与民众之间的心灵共振。“……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1]P70但事实并非如鲁迅设想。
“我”与闰土相见,“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说不出话”,否认了启蒙者与民众之间对谈的可能,“握拨一弹,心弦立应”,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了。正如在《药》中,革命者的血最终并未能唤起民众的觉醒,而是被做了治病的馒头。
闰土的出现,不但否定了启蒙的前提,也质疑了启蒙的方式。这种质疑和否定,也是鲁迅自身对启蒙的疑虑。它表明,随着经历的丰富,热情渐冷的鲁迅更加走向了深刻与成熟。
鲁迅不少小说,如《药》、《祝福》、《孤独者》等,都如《故乡》一样,一面是鲁迅试图为慰藉不惮前行的猛士所发出的呐喊,同时又包含鲁迅对启蒙的质疑和更深层的思考。这种质疑与析解,又让鲁迅感受到一种希望溃散的痛楚,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往往是呐喊与质疑的混响,希望与绝望的复调。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许寿裳.鲁迅回忆录(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