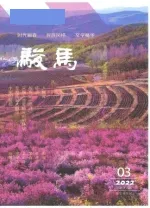根河故事
陈晓雷(蒙古族)
陈晓雷
蒙古族。创作小说、散文、剧本、文学评论200余篇(部)。著有小说《冬树的风筝》《旱草原》《混血铁匠》等,散文集《生活的位置》《生命的河流》《我的兴安我的草原》。散文曾获全国第四届“乌金奖”和2009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奖。
我让你躺在阳光明媚的大地,像母亲照料婴儿那样甜蜜。
大地会变成柔软的摇篮,将你这个痛苦的婴儿抱在怀里。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卜留克往事
近日,读巴金先生的散文《黑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何艺术家们对东北流油的黑土高原发声不强烈,甚至于集体失语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将军作家李存葆先生以审视历史为“经”、以直面现实为“纬”,写了篇以我的故乡内蒙古东部黑土高原为人文底蕴的“大散文”——《呼伦贝尔记忆》,这篇非凡力作让我眼前大亮!将军描述的发源于大兴安岭古代鲜卑人的悲欢离合、爱恨交加、历史变迁等诸多故事,让当今世人知晓了黑土高原先民们的昨日足迹,让我对黑土高原上生活的先祖们有了崭新的认知。
今年6月23日这天,我随作家采风团在根河市金河镇“冷极第一村”吃晚饭,我因临时跑到一位老退伍军人家采访而耽搁了吃饭。当我赶到餐厅时,桌上饭菜已食酒过半,人们情绪高涨,大声喧哗着,呼伦贝尔市文联主席、作家艾平指着桌上一个炒菜,对我大声招呼:“晓雷,快坐下,这是炒卜留克丝啊!”
在这“纷乱”的环境中,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她的这句话,也不知道她为何特意提示我的真正用意,然而这句话对我来说,不仅具有尝鲜的味道,关键是她道出我一个特殊时期的生活秘密,我为此心头阵阵发热……我联想到我故乡的黑土地,和许多关于黑土故乡的往事。
当年,我走出大山的时候才十二岁,尽管自己降生在黑土丰厚的大岭深处,却对自己尚未悟化的土地没有感知,一切都司空见惯。那个时代孩子的童年清贫、简单、快乐,甚至有点傻里傻气;那时好像我们对世界的感受皆在玩和吃上,每天能吃到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干什么更重要。
说起这“卜留克”的由来,这里还有个流传了近百年的故事:
上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暴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红军和老沙皇的旧势力之间打响了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战争,烽烟席卷了广袤的俄国大地,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尤其远东地区许多村庄在双方的“拉锯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一个冰雪尚未融化的初春傍晚,中年农夫康斯坦丁·尤里领着全家六口人逃离家园。他赶着一辆四轮马车匆忙逃亡,马车上载着妻子薇拉和一男三女四个孩子,最大的哥哥九岁,最小的妹妹才两岁。车上除有够五天用的饮水和面包外,细心的尤里竟然在忙乱中没忘记带上少量的农具和两包种子:一包是向日葵籽,另一包就是卜留克籽。
尤里的马车避开大路,走乡间小路,在急迫紧张中行进,日夜不停,疾命奔逃,这一家人只有人困马乏时,才躲进森林休息。他们就这样一连走了三天四夜,穿过茫茫草原,跨越涅尔斯琴克山脉,沿着乌鲁利云圭河谷一直向东奔行。终于在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他们跨过了冰雪覆盖的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在离得尔布尔河很近的一个山谷盆地里安下了家。这里地势平坦,林茂草丰,避风临水,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尤里望着这静静的山谷,心中洋溢着一定要生活下去的渴望和激情,他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和家人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骄阳灼照的七月,大地生机无限,当地人看见尤里家的四周开遍了金灿灿的向日葵,人们还发现尤里家门前新开的黑土地上长出了一大片绿绿的叶子,地垄上那像馒头大小的东西,俏皮地张望着原野,那副静待收获的样子很让邻人感到好奇。邻人遂忍不住问尤里:“这是什么东西?吃的吗?”
尤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卜——留——克——,吃的。”说完,拔下一棵卜留克,拧掉缨子,用刀子切下一块,先放到自己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又弄一块递给邻人,还用手不停地对邻人比划着说:“吃,吃!”
邻人疑惑地嚼着卜留克块儿,脸上的表情急速变化,由迟疑到欣赏,到溢出笑容,还学着尤里的腔调连连说:“甜,好吃,卜——留——克!”
尤里大笑着再次教邻人:“对,卜——留——克!”
这“卜——留——克,卜留克”的认同声此起彼伏,很快就从尤里家的小院里传出来,当地人都知道了这个由俄罗斯人带到呼伦贝尔来的高寒蔬菜物种,它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可以当水果吃当粮食吃!“卜留克”叫起来响亮流畅,又好记,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
卜留克,是我的故乡独特的高寒蔬菜,它适合在东经115°~126°和北纬47°~53°的黑土高寒区、山地高原区速长成活。它的生长周期最短两个半月,最长三个月,能长成大碗那么大,重量一二斤平平常常。如果在低坡肥沃的河谷地里,它能长到茶盘那么大,重量可达二三斤!
大兴安岭的黑土地肥沃,从卜留克种子落地的五月,到完全长成只需三个月。卜留克种子形似芝麻粒,个儿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它们在湿润的黑土下,饱纳营养,日夜暴长,七八天碧绿的幼苗就破土而出,其茁壮鲜绿的身姿,就像阳光下的青蛙,连蹦带跳,展示着超凡的强势。在人们还未来得及注意它的小半月里,它圆润如扇面的叶子就“扑楞”开来,把油黑的地垄给遮住了。在人们不十分注意它的月余里,它叶子下面的果实已悄然长成拳头大小了,只有当山风刮过,掀起它绿叶裙裾的下摆,阳光照在一半露于地表,另一半深扎黑土地的卜留克上,人们才能看见这一片片、一垄垄圆圆的鹅黄色卜留克,看上去它们很像一排排列队出操的活泼少年,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遇上风调雨顺,当地人到七月中下旬就可以吃上中碗大小的卜留克了。把它们洗净,切成细丝,加盐加酱油加醋加味精,生拌一大碗端上饭桌,这时满屋都飘散着卜留克独特的香味,大岭人饭桌上的枯燥气息皆被它驱散了,即使是面对清贫的日子,人们坚持过下去的劲头也会更足。
我刚出生不足一个月,就赶上1960年那场大饥荒。母亲说,当年怀你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可咱们这儿的黑土地最有劲儿,除山里的各种野菜外,只要是不怕高原寒冷的种子,把它们埋在黑土地里,再遇上好雨和阳光,不出月余就可以吃上小葱、小白菜、水萝卜了。可这些东西不能代替主食,那时咱们家孩子多,主食靠那点供应粮,做的大米查子、窝窝头、高粱米总不够吃,我和你爸爸每年都要在大河边种两三片地,就种咱那儿最高产的东西,最多是土豆,最实惠是卜留克,这两样东西长得快,收获多,还扛吃,咱家就是靠着吃这两样东西,才度过了大兴安岭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兴安岭的冬天是最难熬的。大雪封山之后,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珍贵如金子般的粮食到边远偏僻的大兴安岭林区就寥寥无几了。那时我们大岭人家几乎每家屋内的地窖中都贮满个头儿大大的土豆,与其相伴的就是卜留克。在大冬天里,岭上根本见不到新鲜的蔬菜,孩子们对水果的向往皆变成了美丽梦幻,但我们渴望吃水果的心却从不气馁,于是我们找到了“借代物”,即把卜留克切成片儿,当成水果生吃,我们口中一边嚼着嘎嘎作响的卜留克,一边想象着它们是鸭梨、苹果,甚至是甜杏、鲜桃……特别在寒冷腊月的夜晚,在电灯下切开的卜留克金光闪闪,看着它总让人想到高原夜晚头顶上那轮温暖、宁静的月亮,咬一口又脆又甜,细细咀嚼着,山里孩子心中洋溢着满足,似乎生活中再没有忧愁了。
到深冬时节,卜留克没有土豆那么幸运,屋内的地窖多存储土豆,它们大多数不能入窖,没办法只好把它们堆放在院子里,用草袋子盖上。大雪飘来,卜留克堆上盖着厚厚的雪,它们冻硬冻实,如河里的鹅卵石,从远处看卜留克堆儿很像一座碉堡,人们坚信,只要它屹立在那里,冬天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吃卜留克时,我们要预先把它们拿到厨房化冻,再洗净泥土放在大铁锅里烀熟,然后切成片儿装在大盆里端上桌,顶着热腾腾的气焰,全家人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就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任务似的,极其开心。
那特殊的年代,土豆和卜留克是大兴安岭人维系生命的重量级食物,它们常常在同一锅里被烀熟,土豆被一切两瓣儿,雪白雪白的,看上去银闪闪的;卜留克多被切成厚片儿,橘黄橘黄的,看上去金灿灿的,它们散发着缭绕蒸腾的热气,装在盆子或盘子里被端上我们的饭桌。此刻,每户木刻楞小房子里的男女老少,皆忘记了寒冷严冬的存在,好像窗子上的霜花也在为这小屋子的温馨含笑绽放。
这时的屋外,正呼啸着寒风,飘着大烟炮儿雪,我们这些山里孩子一手抓着土豆,一手抓着卜留克,就着大葱,蘸着香喷喷的大酱,吃得满头冒汗,一会儿个个肚子溜圆,嘴巴上还沾着残留的大酱。吃饱了不饿的孩子们突发奇想,称:“土豆是我们的太阳,卜留克是我们的月亮……”孩子们见面就问:“吃饭了吗?”对方答:“吃了——月亮!”
当我们胃里塞满的卜留克给全身以热量的时候,孩子们心里就想着外面的冰雪世界了。滑冰、溜爬犁是万万不能饿着肚子的,这些大山里的孩子单薄的身子能抗拒零下四十余度的严寒,就是卜留克发出的巨大热量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卜留克让我们战胜了饥饿、严冬,我们的童年因此而独特精彩。
那时,我是个躁动不安、极其淘气的孩子。
一个夏日的傍晚,姥姥忙忙碌碌地为全家准备晚饭,我听邻家的石头哥哥说烧卜留克好吃,就趁姥姥不注意,偷偷把一个卜留克投进炉灶里。我求吃心切,就不断地用炉钩子翻动它,盼它快点熟,结果把姥姥的炉子捅涝了火,让她贴了一锅的玉米面大饼子全溜了锅,变成了一锅糨糊糊的玉米面粥!姥姥气急了,挥着锅铲子对我喝道:“你个小现世宝,你淘得没了边沿儿!”说完踮着小脚,气冲冲走来欲揍我一巴掌。我像一只惹了祸的小猫儿,灵巧地躲闪着姥姥,尽管这样,我还没忘了从炉灶里掏出尚未烧熟的卜留克,一边跑一边啃。姥姥见我手里捧着烧得黑黢黢的卜留克,嘴角和脸上沾的炉灰把我弄得像唱京戏的“花脸”,这副狼狈相,把姥姥逗乐了,她喝道:“这孩子,卜留克有这样吃的吗?看你那魂儿画的脸,像个小鬼儿,快给我洗洗去!”
晚上,我见姥姥脸上重现平日的亲切慈祥了,才敢上桌吃饭,可心仍怦怦直跳,斜睨着姥姥,担心她把我干的坏事告诉爸爸妈妈。
我刚坐在炕边,姥姥就把一大盘冒着热气的切成厚片儿的熟卜留克端上饭桌,接着又把一小盘卜留克放在我面前,我仔细看,一共四片,是用豆油煎过的,表面一层金黄色的嘎吱儿,像在卜留克片平面上画了几朵金光闪闪的玫瑰。这油汪汪的东西散发的香味儿,弄得我直咽口水,这是姥姥为给我“压惊”特意做的“专供美食”。我早已馋得等不及了,忙伸手去拿,被姥姥一巴掌打在手上:“热啊,烫着你!”我愣愣地住手,滑稽相把全家人逗得哈哈大笑……
这时,姥姥又端上了一道菜:辣椒油、酱油生拌卜留克丝。
姥姥把黄澄澄的卜留克,切得像粉丝一样细、一样均匀,这也是一道全家人最喜欢的美味佳肴。这盘生拌卜留克丝儿,弥漫着大岭菜肴的特殊香味,我看到全家人的眼睛都亮闪闪的,像夜里的星星在小屋子里聚会!
这个晚上,我们家好像开了个卜留克全餐“宴会”,记得爸爸宽宽的额头上的皱纹散了,妈妈的脸颊挂满喜悦。姥姥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儿,说:“傻小子还愣着干啥?吃啊!”这时,我们四兄妹像听到了发令枪声,低头抓起卜留克,一阵风扫残云……
夜深了,我读着巴金笔下深藏情感的文字,慢慢进入他描绘的意境中,上个世纪初,一个流落上海的俄罗斯游子,每每来到咖啡馆里,都会面对自己从故乡带来的一小袋黑土凝视、沉思,然后默默无声地垂泪……相同情景和境遇,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巧合,当年那个从俄罗斯流落到中国呼伦贝尔高原的农夫尤里,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崭新的种子——高寒蔬菜卜留克。因而尤里的命运与上海对着黑土垂泪的俄国同胞大不相同,这两个俄罗斯流亡者的命运证明了“勇敢地融入,无私地传承,不断地创造,就是再生”的人生道理。
巴金动情地写道:“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
读到这里,我这个远离故乡多年的游子,眼睛湿润了,模糊了……
父亲的事
在洁白的野芍药花如繁星绽放的时节,我来到中国的冷极点——大兴安岭北端最高峰奥科里堆山的脚下。我们的汽车逆葛根高勒河峡谷而上,行进不足一小时,这条大兴安岭的命脉之河——根河,就灵光楚楚地伫立于眼前了。
我感到眼前这条蜿蜒远去的大河,款款深情,似低语叙说。
父亲1953年来到大兴安岭参与林区开发建设,自1954年到1959年,他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那五年,是他最难忘的年代,至少有三件大事让他津津乐道,常挂嘴边,这三件大事是:前三年搞“小森铁”工程建设;1958年回辽宁老家领我妈来林区结婚;1959年底他的第一个儿子在大兴安岭上出生。
这第一件大事与根河的开发建设息息相关,因此,我要重点写写这件事。
1954年大兴安岭的第一条森林铁路——“好冷小森铁”就诞生在根河。这条“好冷线”从好里堡到冷布露,全长170公里,是一条直接延伸到原始森林地带的运材路,是后期建设的多条小森铁的开端,具有特殊意义。
当年还是小伙子的父亲,在森铁筑路工地当工长,负责管理8公里长的工地和一百多号工人。他每天除为工人们制订挖土方指标,傍晚验收挖土方的多少外,他还承担一件极具风险性的事——每天要走七里多的山路,到工段财务给大家取工钱。他每天沿着河谷侧羊肠小道步行,翻过一座岭,还要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父亲个子高腿长体力好,往返一趟尚需两小时。
当时招来的工人多是临时工,有关里来的盲流子农民,有城市失业者,还有躲避内地“镇反”的潜逃人员。那年头实行“计件工资”,每天傍晚完工,父亲当场验收工程,双方核对后,用现金兑现,当场发现钞。
父亲后来给我讲了他的那次奇遇。那个夏天,蚊子特别多,雨水格外大,云彩骑在山头总不肯离去,湿漉漉的森林,伴着阴沉沉的天气,让人们的心情沉郁。
那天,我把几沓钞票装进兜子,忙从工段往工地上赶,刚走半小时天就下雨了,进了那片林子天就暗下来,雨越下越大,浓雾弥漫,看不见路,我只好停下来避雨,就靠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松树下。过了二十分钟雨仍不停,天却全黑了,我怕迷路,就顶着雨摸索着往前走,走进坡上那片黑桦林里,雨小些了,雾也淡了,我刚要歇歇脚,就听到前面“嗷”的一声叫,在我前方大约三十米远的坡上有几个绿莹莹的“灯笼”不停地闪动着,像鬼火忽明忽暗,仔细看那是三只狼的六只眼睛!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全身冒汗,来大兴安岭两年多,我首次遭遇狼,竟然是在领工钱的路上!
我镇定情绪,摸摸裤兜里的那盒火柴,摸摸装钱的兜子,心想,我不冲着你们去绕过你们总可以吧?我就往西北走,这仨东西极其狡猾,同我保持相等距离,也跟着我向西北移。我往西南走,它们又跟着移回来。我停下它们也停下来。这么折腾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全停了我居然没察觉到。我喘息不止,像头不敢前行的马鹿,脚步零乱,体力消耗过大。我想,若再继续同它们玩拉锯战,等我疲惫不堪时,它们就会乘机而上……我在一棵粗桦树下,摸着地皮想找几块石头,抠得满手都是黑泥也没找到,最后找到一根胳膊粗的桦木杆子。狼开始冲我嗥叫,“绿灯笼”们一点点向我靠近,我忙抡起那根桦木杆子,“啪啪”地拍打到树干上,声音很沉很响,“绿灯笼”们动了动,离我远了些,一会儿它们又向我靠近了,我的这招儿用过三次后就不灵了。
这几个鬼灵的家伙,看出我意在吓唬,没有攻击的勇气,就得寸进尺,离我越来越近!我知道狼怕火,马上掏出火柴盒,“嚓”地划亮一根火柴,我用一根一根的火柴延续时间、延续生命。我和狼对峙近两小时,估计已近子夜了,它们仍与我保持距离坚守在那里。而我的一盒火柴就剩七八根了,我对自己能否走出这片林子开始忧虑。我想到兜子里的那些钱,就把雨衣的一只袖子撕下,把兜子裹好,以避免这些钱给弄湿了,再爬上身边的一棵大松树两米高处,把兜子挂在枝桠上。我想,我若出了事,这些钱是千万不能出事的……我跳下树,觉得两腿乏软,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再看不远处的那六个“绿灯笼”,我的心又猛地收紧了,那几个“绿灯笼”已变成一排,足有六七只狼正向我迂回过来,我俨然成了它们围猎的一只动物!我紧紧握住桦木杆子,准备拼死一搏……
奇怪,这群狼向我走着走着,阵容突然大乱,很快我听到一阵“咚咚”的敲铁桶、铁盆的声音传来,接着林子那边出现多个手电光柱闪来闪去,伴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传来嘈杂的呼喊声,我知道工友们来救我了,就高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狼群被工友们吓跑了,我瘫倒于灌木丛中,欲哭无泪。
三天后,父亲又遇上一件意外的事,这回可不是狼了,而是比狼更凶残的人。
这段路基逆河谷而上,由于这些天雨水连绵,路基东侧的河不断涨水,河水原来清澈,现在变得浑黄了。这天上午,开工不到两小时,一场暴雨如急电袭来,工地上顿时水雾弥漫,流水成溪,父亲和工人们不得不躲进帐篷里。半小时过去,大雨变成中雨,临近中午雨虽小了却还在下着,工地仍无法开工。
这时帐篷里传来一个粗暴的谩骂声:“操他妈的老天!我老婆孩儿等着我挣钱回去买饭吃呢,今天真倒血儿霉了,这天道就是不让老子挣钱啊……”父亲循声音看去,是住在最里面的被工友称为“李大疤瘌”的壮汉在发脾气。父亲知道工人的情绪烦躁,是被阴雨天搅的,家里老母妻儿等着他们挣回钱来买米下锅,而他们却因下雨迟迟不能干活,挣不到钱还要死死耗在山上,这群脏兮兮、汗淋淋的男人聚在狭小的帐篷里,心情郁闷不堪,正找不到渠道宣泄呢。
这时李大疤瘌又说话了:“他妈的,不是老子不愿干活,今天若挣不到钱,就得让工长给老子发钱!”父亲听出这话刺耳,且知话里有话,就直视过去。不远处的黑壮汉年近四十,大头方脸,身高近一米八,最显眼的是他右眼颧骨侧下方有条很深的刀痕,这是人们称其“李大疤瘌”的由来。据工友们传,他解放前曾干过胡子,当过“国兵”,后又开了小差。他眼里凶光飘忽,从来不笑,说起话来总像咬着牙,在这十二人的帐篷里没人敢不听他的,他最大的乐趣是给别人起外号,干瘦的毛林被他称“瘦猫”,胖子老赖被他叫“墩子”,驼背孙宝被他喊“驼孙”,这三个人早成了他的小兄弟,一呼百应。
此刻的李大疤瘌也正在逼视年轻的工长,对其怀有不敬。见我父亲不答话,李大疤瘌抬高声音说:“弟兄们,验米尺在工长手里,工钱在工长兜里,今天就是干不上活,晚上工长也得给咱兄弟发钱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小兄弟齐声附和:“是啊是啊,工长必须给咱发钱,发钱啊!”
父亲起初并没想到这其中的“猫腻”,就说:“天晴了就能干上活了,下午大家加把劲,把上午耽搁的活抢回来,晚上就给大家发钱嘛!”说完父亲顶着雨到工地上巡查去了。
谁也想不到这场雨一直下到午后两点多,虽然雨停了,天却不放晴,工友们抡镐挥锹,玩命地挖土方,想把上午未干完的活追回来,但事实是当天的计划指标没能完成。
傍晚,青蛙在泡子里哇哇鼓噪。西天总算裂开一条缝隙,一缕霞光透过来,这光亮把东边大半个还阴着脸的天给衬得更灰更暗了。几只老鸹飞过天空“呱呱呱”地叫着,听上去有些瘆人。
很快西天那缕金光掠过树梢映在河面上,河水哗哗,雨后大河又涨水了。父亲匆匆行走于氤氲的潮气中,为工人们检尺验米。今天由于雨水不断,大多数人挖的土方没超过三立方米,那时挖一立方米土只给一块多钱,工人们拿着很少的钱闷闷不乐地散去了。父亲记完账,一转身,见四个汉子直愣愣地立在他身后,他吃了一惊,定睛一看,为首的是李大疤瘌,这壮汉正冲他无声地冷视着,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父亲本能地用手按了一下挎在胸前装现金的兜子,正正神镇定地问:“你们还有事?”
李大疤瘌说:“工长,你给我们验米验错了,开的工钱不对!”父亲说:“我是按立方米算钱,不行咱们再量啊……”李大疤瘌拦住父亲的话:“不行,瘦猫他们要开三块钱,我干得多,必须给我开四块!”他大喊着还挥挥手,瘦猫、墩子、驼孙立刻围上来,包围圈越收越紧。
李大疤瘌又威胁又装可怜地说:“工长,你该放明白点,这钱是国家的,多给少给也不从你兜里拿,你干嘛做损事呀,让我们兄弟饿着老婆孩子呢?”
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动”弄得头嗡嗡作响,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那只手还紧紧扣在钱兜子上。
眼前的壮汉见年轻的工长神情有些紧张,就翻脸威逼道:“工长,不是我无赖,是你无情,今天若不给我们钱,你就别想回去了……”父亲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但他还是说:“我已经按米数给过你们钱啦……”父亲的话没说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呼”地悬了空,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天,他忙说:“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这四个小子连抻胳膊带拽腿把父亲四仰八叉地悬到半空,不管父亲怎样挣扎,他们的手铁钳似的死死掐着他,还抬着他往坡下奔去,直到他听到了哗哗流淌的河水声,才知道他们把自己弄到大河河堤上来了。
这时,李大疤瘌眨巴着眼睛冷笑地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小子死心眼,不给我们钱,就让你去喂鱼……”
父亲当年给我们讲,听到这家伙放狠话,自己眼前发黑,心想这下可能完了,就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他们摇晃着,好像他们要把自己撕碎了,父亲脸上显出无助、无奈,开始有些恐惧。
后来父亲给我讲这件事时说,这四个家伙憋足了劲,只要喊声口号一齐撒手,我就会被抛下几十米深的河谷,浑浊的浪就会把我吞噬!
父亲说,我绝望了,紧闭眼睛,我不再挣扎,可我还是感到自己的身子在晃,脑子在晃,五脏在晃,不知晃了多久……奇怪,我的耳边没有了粗重的喘息声,没有了刚才的狂喊声,四周鸦雀无声,静得出奇,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群山里死了般地静寂。父亲说,就这样又过了几秒钟,我感到自己不再晃了,我的身体慢慢下沉,后背很快落在潮湿的地上。我被弄得喘不过气来,我咬咬自己的舌头,有疼的感觉,我没昏迷,我睁开眼睛,见四个男人的脑袋全“盖在”我的脸上,他们几乎与我脸贴脸,他们以为我被吓死了。我看着他们惊恐的脸,“嗤”地笑了……李大疤瘌叹了口气,话变软了:“笑?你小子不怕死,还有心笑?”父亲说:“我死了是为公,可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李大疤瘌声音小了:“咱哥俩商量商量,你给我四立方米的钱,也是在我小兄弟面前给我面子,不然,我们打断你的腿,就往山下跑不干了!”
这时完全冷静下来的父亲心生一计,说:“给钱可以,这钱若糊里糊涂地给你们,这世上还能上哪说理去啊?”李大疤瘌懵了,不知工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试着问:“糊涂?这……到底有什么说法?”父亲坐起来,挨个看了这四个家伙一眼,说:“这样吧,不就是为了那几个钱嘛?我们来打个赌,我若输了,我立马掏腰包给你们钱。”李大疤瘌一听此话来了神:“你说,这赌怎么打?”父亲说:“我们来赌摔跤论输赢怎样?”李大疤瘌用蔑视的眼光瞟一眼个子比他矮的工长,说:“摔跤?不怕摔断你的腰?”父亲镇定地说:“对,摔跤,一对一,你们中的任何一人摔倒我都算,我认输掏钱,可有个条件,我只和你们中的两个人摔,我要是赢了,你们中就必须有一人回家抱孩子去,路费我来拿,这事完后不许声张,我也当没发生过……”
李大疤瘌及其小兄弟不知道我父亲是蒙古人,来林区前他曾在科尔沁草原上生活过两年,练得一身的好功夫,被体育老师赞为“鹰博克”。父亲身高一米七八,摔跤时,雄姿矫健,动作灵敏,虎虎生风。那天父亲只用两个回合,李大疤瘌就被父亲摔个狗啃泥!胖墩子喘着粗气扑上来,父亲一闪身,顺势脚绊扫过去,墩子就像装满粮食的粗麻袋,重重摔在地上!
第二天,李大疤瘌真的不见了,父亲后来对我说:“我从自己工资袋抽出五块钱,准备好了等着他来拿,这小子还真讲究,没敢来见我就溜了……”
父亲说,那天我不知何时天晴了,只记得晚霞像团火映红了大兴安岭的山峦。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