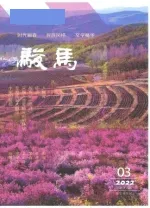你不是鄂温克,你不知道树
耿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缅想的灵地》入选“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悲哉,上将军》入选“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六届老舍散文奖、孙犁文学奖第一届散文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遮蔽与记忆》2010年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转载。
一
我们到达敖鲁古雅阿龙山玛丽亚·索部落时,看到了猎人安道正坐在一堆木柴的前面,那时午后,天蓝得让人不敢相信,猎人安道的脸是酱色的,他的身边是一柄劈柴的斧头,很安静。
人们说安道老人最擅长打制猎刀,他一天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当时身边是斧头,并没有猎犬,但大家说猎犬是他最近的伴侣,他和猎犬同一碗吃饭,人吃一口饭,狗也吃一口饭,晚上也和猎犬同眠一张床。
当同行的人拿起斧头在安道老人面前笨拙地学着劈柴时,老人笑了。也许在老人看来,文明人也在退化吧。人们告诉我:安道老人用作烧火的劈柴,都是在森林找的枯死的树,鄂温克人从不伐还生长的树做柴烧。鄂温克人从来不会破坏一棵树、污染一条河。在鄂温克人的眼中,这些都是神灵的赐予。他们相信万物有灵魂,这些灵魂可以互相转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鄂温克人把动物植物当成和自己一样的物种,他们有了烦恼,可以对着大树诉说,他们通晓鸟儿的语言,他们不贪婪,他们平和地对待自然。
鄂温克人视树为生命,他们火塘里的柴,都是用风倒木劈出的柴火。砍伐鲜树作为烧柴那是一种罪过,森林中那些枯干的树枝,被雷电击中的树,被狂风击倒的树,被山洪冲下的树,他们把这些失去生命的树弄来作柴烧。鄂温克不像汉族人砍那些还活得好好的树,那些还活着的树就被汉人砍下,劈成木头柈子,垛满了房前屋后还有院子里,像炫耀,他们不理解这种贪婪。
在森林生活的鄂温克人离不开树,他们对树木充满感激充满敬畏,鄂温克原始神话里有:“开地之初,在大地的黄色肚脐上,单立着一棵大树,树上有八条繁茂的树枝,树干一立穿过三层天,树皮和树疖都是银的,树液闪着黄金色的光芒,果实像巨大的酒杯,树叶像张张马皮。从树梢经过树叶流淌着神圣的黄色泡状液体,人们饮过它就得到了大福。”
在鄂温克的传说里,是神树养育了人类、赐福了人类,神树是给予鄂温克人生命的树,鄂温克人对树木最根本也最原始的观念,就是把树看得像是养育自己的母亲,东非万尼卡人就认为“每毁坏一株椰子树,就等于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鄂温克人把树作为祭神的圣所,他们认为神的灵魂寄居在某棵大树中。比如鄂温克族猎民信奉的“白那查”山神。“白那查”的形象是在大树上绘制的一个长须老人的模样。在狩猎途中,猎人从“白那查”旁边走时不能喧哗,否则对狩猎不利。鄂温克人认为一切野兽都是“白那查”饲养的,猎获野兽是“白那查”的“恩赐”,因此,遇绘有“白那查”神的大树,要用兽肉献祭,还要摘枪卸弹,跪下磕头,祈求保佑。如果猎获了野兽,还要涂一些野兽身上的血和油在这神像上。
这是鄂温克的古老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酋长带着全部落的人去围猎。他们听见大山里传出各种野兽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叫声,就把这座大山包围了。其时天色已晚,酋长就让部落的人就地安歇。第二天,部落的人开始缩小包围圈,一天很快又过去了,到了日落时分,酋长问部落的人,让他们估计一下围猎了多少种野兽?这野兽的数量又是多少?没有一个人敢回答酋长的问题。大家知道,预测山中的野兽,就跟预测河里游着的鱼森林里开多少朵花一样,谁能说得准?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有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人开口了,他不仅说出了山中围猎的野兽数,还给这些野兽分了类,鹿几只,狍子几只,兔子几只。等到第二天围猎结束,酋长亲自带领人去清点围猎的野兽的数,竟然与那老人说的一模一样!酋长觉得老人非同寻常,打算问他点什么,就去找老人。明明看见他刚才还坐在树下的,可现在却无影无踪了。酋长很惊异,就派人四处寻找,仍然没有找到他。酋长认为老人一定是山神,住到树里去了,于是就在老人坐过的那棵大树上刻上了他的头像,这就是“白那查”的来历。
二
在鄂温克人居住的森林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长着眼睛的白桦树,我压抑着像看到梦想一样的激动,让朋友帮忙为我留影。
在我的感官中,白桦是一种异域的风情,在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名画《白桦林》前,我曾莫名地潸然落泪,为那种美,为那种秀劲挺拔的树干上,诗意般地围裹着一层厚厚的、白光闪闪的银色。多么纯洁的银色!它使你联想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那些女兵,它使你联想到纯真圣洁,联想到爱人。
俄罗斯民俗学者费德科说:“只要你走进白桦林,就会知道桦树对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其它任何一种树都无法带给你那种纯洁、孤傲和完美的特殊感觉。我认为这就是俄罗斯灵魂的写照。”
诗人普希金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描述过去南方旅行看到白桦树时的喜悦心情:我们穿过了一道道山岭,首先令我惊讶的是白桦树,北方的白桦树!我的心为之颤栗。
这次在鄂温克人家,我看到随处的白桦的物件,那种欣喜可以用断路来形容,我一时头脑空白,为这与美的相遇。
白桦树是鄂温克族人生活的影子。小桥是白桦搭的,猎人坐骑的马鞍是白桦做的,渔人的船是桦树皮做的,一间间尖顶、形似帐篷的“撮罗子”是白桦树翻皮搭建的,院墙也不是砖石垒的,而是清一色的白桦树“木栅子”,甚至吃饭用的桌子、凳子及碗筷,也是桦木或桦树皮做的。在鄂温克民族乡小孩子生下来,也放到白桦做的摇篮里挂在树上。
白桦的汁液,像乳汁哺育着鄂温克人,他们用猎刀在白桦树根那里轻轻划一个口,插上一根草棍,摆好桦皮桶,桦树汁就顺着草棍像泉水一样流进了桦皮桶里。那汁液纯净透明,非常清甜,喝上一口,满嘴都是清香。
鄂温克人打猎、捕鱼、挤奶用的制品很多都是用桦皮制作的。餐具、酿酒具、容器、住房、篱笆、皮船,甚至人死后裹尸都用桦皮制作;鄂温克人许多的服饰也是用桦皮做的,如桦树皮帽、桦树皮鞋。
我看到了一只桦皮船。桦皮船行驶时轻巧无声,就像一条鱼,白白的,所以在水里行走不会惊走水里的鱼和岸边林中的兽。
在白桦林,我抚摸着白色树干上那一只只黑色的“眼睛”,感到了她们在手的抚摸下忽闪忽闪地动,传说用红丝巾遮住白桦树身上的“眼睛”,这样,就能让情人不再看其他的人,而一生一世只爱自己。我想用刀子在白桦的皮上刻下一个人的名字,但怕破坏了那种圣洁,只好作罢。
离开了白桦林,我看到了身后的一只只眼睛,在注视着我。
鄂温克是一个信萨满的民族,他们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神灵,人们要谦卑敬畏,即使是一朵花的开落,一丝风声,一声鸟啼,一声雷鸣,一片雪花,一片桦树的叶子,甚至一粒星子,都有神在远方在看着主宰着。于是,这就有了火神、山神、风神、雷神等等。
其实他们敬畏的就是一个神,这个神就是自然,他们对自然充满敬畏,顺从自然,不背拗,不狂妄,不贪婪,不过分索取,于是收到敬仰的神就赐予他们更多,让他们得以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他们相信万物的轮回,人的前世可能是熊托生的,虎托生的。于是,他们认为他们和熊啊,鹿啊,灰鼠啊,猎鹰啊,都是出自一家,对它们,只是饥饿时,不得不打猎时才出手。他们认为呐,他们和花啊草啊树啊浆果啊野菜啊,也是出自一门,只是为了填饥时,才去采摘,于是手下就小心翼翼,就充满爱意。
他们对森林怀着的是感恩,这使我想起了被称为“红人”的印地安土著,我的记忆里有一篇名叫西雅图的酋长的演说,那也可以是鄂温克人的宣言,和鄂温克一样的大自然的信徒,都是那么古老,有着金子一样对待自然的品质。
“对我们民族来说,这片土地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圣的。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树汁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载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印第安人喜欢雨后清风的气息,喜爱它拂过水面的声音,喜爱风中飘来的松脂的幽香。空气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因为一切生命都需要它。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同样,空气也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所有的生物以生命。你们要照管好它,使你们也能够品尝风经过草地后的甜美味道。”
这是美国政府要以15万美元换取印地安人200万英亩土地时,红人酋长发表的演说,这是一种忠告,也是一种深情,对离开的土地的深情。他们的爱不傲慢,他们的爱是谦卑,他们懂得躬身对待草木、溪流、虫豸,万物都是平等的,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嗓门大?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
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
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是啊,在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眼里,森林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森林的,大家都是森林的子民,有话好好说。
在森林拍照的时候,一个同伴在一个立的树桩上坐一下,就被同行的通鄂温克风俗的人叫了起来,说这是犯忌讳的,在鄂温克人眼里,那是山神爷才能坐的。
鄂温克人在森林里有很多的禁忌,我想,鄂温克人的那些禁忌是不能称为迷信的,应该是一种敬畏。人有敬畏之心是好事,这样做任何事都不会太放肆。犹太作家以撒·辛格说:“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我想,这里面是应该排除鄂温克人的。
鄂温克人猎熊也有很多讲究,打熊不能打头,剥皮时还要不停地念叨:熊大哥,冬天来了,我需要一副手套过冬啊,说完再割熊掌;割熊耳朵时要吹哨,模仿站杆林被风吹过的声音;割熊腿的皮子还要念叨:有了手套我还要一副靴子来暖脚啊,当然,还要解释一下熊皮的用途,因为寒冷还需要一床熊皮褥子来御寒;就连吃熊肉时,也有讲究,大家围坐一圈“嘎嘎”地模仿乌鸦叫,意思是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我们在吃你的肉,而是乌鸦。
多么可爱的举止啊,永远有着神秘、天真的一个族群,他们的行为像孩童,有着我们现代人消失的诗意烂漫。
这种天真在流失,这种生活成了绝响。三
在森林里,我见到了一棵树枝挂着红绿布条的树,鄂温克人称为神树,鄂温克人在树下祈祷祭拜,有心事向她倾诉。
鄂温克人相信森林里每一棵树都有灵魂,她护佑着每一个鄂温克人。在森林里,当鄂温克人在路上遇到挡道的树,要是无法绕开,就会围着树祷告,然后才敢砍伐。
这样对待树的习俗,我称之为生命敬畏的哲学。鄂温克人在森林里生死,与树终老不离不弃,鄂温克人实行树葬,也称风葬。人死后,将尸体包裹后挂于树上或放在支起的木架上,任凭风吹日晒,待皮肉烂掉后拾骨埋葬。
鄂温克人就如一棵树,老了,就和森林的树木做伴,尽快融化于这片森林!
在敖鲁古雅,我听到一个传说,有个人患了绝症,想用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不想让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为自己殉葬,害了这棵树,因为鄂温克人的习俗是凡是在树上吊死的那个人,一定要连同他吊死的那棵树一同火葬。于是在一个夜里,他找了一棵枯干的树,吊死了。我听到这个故事,落泪了,我想到里尔克在《严重的时刻》中写道: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是啊,我想,这个吊死的鄂温克人在看着大家,若世间没有了这样的爱意,这世界该多么荒寒!
这是一个敬畏树的民族,也是一个敬畏火的民族,人说,一棵树可以造出无数的火柴,一根火柴可以毁灭无数的森林,于是鄂温克人为防止烟头可能会毁掉森林,就发明了一种烟:口烟。它是用碾碎的烟丝、茶以及碳灰三样东西调和而成的,这样的烟不用火,把它们捏出一点,塞到牙床上。
在敖鲁古雅的那棵神树下,我双手合十,然后说了一句:久违的亲人!
我拍了一棵神树的照片,带回我遥远的南国,让神树时时提醒我:人,要有所敬畏,无论是遇到一棵树,还是遇到一根草。
但我忽然想到了《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所说:“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
于是感到了一阵寒颤,从这片土地的遥远处传来。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