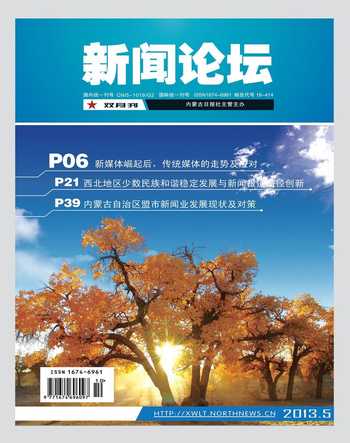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和谐稳定发展与新闻报道路径创新
摘 要: 本文从新闻传媒社会功能和政治监测的角度,探讨新闻报道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形象传播的作用。认为新闻报道应创新媒介管理规制:将西部地区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成为考量当地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检视反思: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的经验与教训,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舆论引导指向国家认同的最终目标;实行双语教育:以新闻传播使用的普通话和民语控制意识形态;赋予优先报道权:率先报道国际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提升少数民族新闻报道话语权。
关键词:西北地区 少数民族 新闻报道 社会稳定 创新路径
2008年以来,在西藏、新疆连续爆发的“3·14”、“7·5” “7·18”、“4·23”等事件,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创伤,也是我国新闻传播的痛苦记忆。这种大小不等、性质恶劣的事件从发展趋势来看,似乎呈现出阶段性轮回发生的效应。对此,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事件解决在稳定压倒一切之中,也使社会向和谐发展。从社会科学和总结学理的角度去研究,人们不仅要问,为何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所反映的“三股势力”图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及其给其他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对国家认同又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新闻宣传与国家认同未成为当时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新闻舆论如何引导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相关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大众传播的常规教育、成为负载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发展传播学原理,总结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探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国家形象传播与国家认同的创新路径,以资探讨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的正能量。正如阿特休尔所言,“确信新闻媒介具有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作用;确信新闻媒介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益于社会变化的手段;并认为新闻媒介应是作者到读者、电台到听众的双向流通的工具”[1]。“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口号标签化等落后方式,正是由于尚未找到国家传播战略、政策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之间的良好结合点所致,这正是给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责任”[2]。本文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角度,探讨新闻报道对西北地区社会发展进行舆论引导的正向作用。
如何认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国家形象和国家传播的作用,这是发展传播学的认知事理的核心,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介作为国家宣传机构和国家财政补贴的传媒事业,应运用宣传机器,经常化地传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会使公民形成对祖国的亲近感和忠诚感。而公民对国家的亲近感和忠诚感作为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最高精神境界,自然需要以传媒宣传作为物质基础。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基础并不牢固。其原因:一是我国的新闻传媒国家投入薄弱,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投入就更弱。二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紧跟临时性的宣传任务,一味地报道地方维稳,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而未注意意识形态领域为何维稳,维稳的目的何在,通过什么来维稳,因而新闻传播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究其实质,无论是汉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其实,对西北地区人民群众而言,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才是解决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基于这一点,要求媒体要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舆论引导的方向,从方法、策略上注意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而当前的新闻传播舆论引导、对少数民族地区报道,只是一种着眼于当下忙于“堵”的保守性思维,而不是一种着眼于“疏”的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认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先检视、反思政府的作为,反而认为是新闻报道惹的祸。这种思想恐怕在许多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当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对此,有学者呼吁政府改变维稳思维,建议“维稳先维权,维权即维稳”[3]。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对新闻媒体的综合功能认识不足,才使西部地区意识形态以及国家认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地、县级媒体,美其名曰让媒体走市场,实则放任其流,使媒体难以承担应有的教化功能和文化积存功能,形成广告养媒体(一些媒体无广告),媒体跟市场,市场不管导向,导向忽略国家利益等恶性循环的怪圈。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得从政治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说起。
1.创新媒介管理规制:将西部地区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成为考量当地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既然承认发展传播学所称的“新闻就是力量,或者更明确一点,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就必须控制新闻传播工具”[4]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遵循的准则,那么新闻媒介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并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天经地义。具体说来,边境或跨界民族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建设或经济指标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维稳的问题。任何边境的政治信息的波动或军事信息的变化都会牵扯国际社会动向。因此,媒介信息变化是考验当地政府官员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当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尺。这就需要创新边境地区媒介管理新规制,将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软指标评价信息波动对边境社会经济安全的影响。另外,针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而言,新闻传播不仅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检视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参照系。因此,根据西部地区社会动态的发展,拟定政府官员意识形态维稳评价体系,敦促官员将不确定因素如何创造性地消灭在平常中,而不应上报给上级如何解决,这样才能改变当地的社会发展。也许会有人对此有微义,认为小题大做,但是,对于像我国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国际新闻界从他者立场理解我国媒介的宣传功能,并指出宣传概念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传播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组织功能借鉴组织传播与制度传播的力量,来宣传并推行各种国家发展方案,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这说明对于边境媒介管理采取异于内地的政策会使边境拥有更多物质基础,促使媒介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建设。
2.检视反思: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的经验与教训,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舆论引导指向国家认同的最终目标。
检视、反思当前和长期以来不符合国际新闻传播习惯的陈规做法,创新符合国际惯例的报道少数民族新闻的新做法、新惯例,都值得我们慎思:如我们长期奉行的报喜不报忧、成就报道归于党的感恩意识的思维定势,从实际出发树立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解越宣传国际上就越不相信,国家形象就越受损的思维怪圈。如何跳出新闻传播报道少数民族成就的窠臼,回归新闻报道事实与意见两分离的新闻专业主义轨道,能否以检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适应国际惯例为标尺,来检验我国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成就,我国少数民族成就动辄都要有感恩意识。毕竟国内自我宣传的影响力偏小。如何创新新闻与宣传融为一炉,宣传讲艺术新闻讲事实。同时,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都知晓,国家认同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身份归属的重要尺度,国家越强盛,公民的幸福感就越强。新闻传播在公民教育中扮演主要角色,媒介发达,则公民教育发达。这是发达、发展中国家公民教育与社会良性发展的一条规律。
3.实行双语教育:以新闻传播使用的普通话和民语控制意识形态。
从小培养公民语言是一个民族记忆和文化的表征。阿特休尔说:“人们通过与他人相互交往而取得感受经验,这种交往的首要手段就是语言。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他们也就能够将人类或者使其成为奴隶,或者让其获得自由。言语制造者是国家,是学校,是教堂,而它的传播者是新闻工作者。因此,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进而就控制了社会。”[5]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少数民族媒介直接起着传承记忆、传承文化的作用。即使现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媒介传播有困难,也应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提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来认识。解放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汉语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今,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水平和汉族大学生相差无几,甚至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却略有倒退。笔者在伊犁、昭苏实地调查观察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说母语多,在学校大多说汉语,这样长期下去会使母语遗失,因此,国家有必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在一定的场合鼓励提倡少数民族用母语传播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让少数民族和汉族都认识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样是国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应使其永久传承下去。
4.赋予优先报道权:率先报道国际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提升少数民族新闻报道话语权。
解放以来,西部地区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建设的重镇。新时期以来,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得到极大的改善,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在物质文化建设中,以国家广电网村村通、农家书屋建设为契机,借助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之东风,新闻传播的物质基础设施大有改善,国家给西部培养的人才大有提高,加之,西部物质资源丰富、矿产储备量大,是国民经济和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新闻报道理应成为报道国际社会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的优先权。在国际传播领域,只有获得优先权,才能获得话语权,这已是国际传播的通则。当然,国家在城镇化、信息化建设中,给农村投入甚广,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广播、电视、网络村村通工程,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大为提高。近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的“农家书屋”建设,不仅给农村人提供了读好书、好读书的场所,而且还成为公民讨论公共事务、谈论国家大事的场所。这些都应成为优先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气象、新风貌的现实基础,也为优先报道权提供了机遇。如今,农村已经显露出公民利用农家书屋等场所议论国家大事、商讨村民事务及纠纷的场所,农村似乎也慢慢借助农家书屋成为公共领域的集散地。因此,报纸、广播电视和农家书屋要充分发挥媒介协调社会和传播文化之长,将国家认同利用各种故事、图片展、影像等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尤其是西北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受众,让其知晓民族是国家之根,国家是民族之本。只要国家富强,民族才能不受欺凌,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与媒介承载公民教育有机联系在一起,这里舆论引导起着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阿尔休特:《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版第174页。
[2]周德仓:《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新闻论坛》,2013年第1期第20页。
[3]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第4月总第33期。
[4][美]J.赫百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页。
[5]孙聚成:《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2页。
[30][美]J.赫百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74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0YJA860018)“西北少数民族信息需求与传媒信息供给及舆论引导研究”
作者简介:南长森,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
责任编辑:邰山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