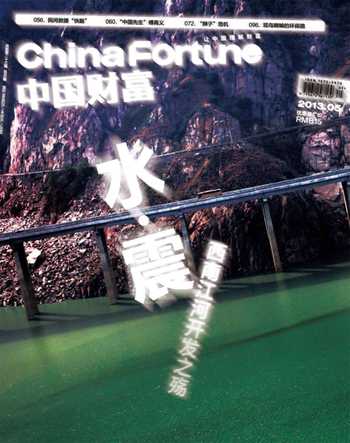艺术黑客
Jon Lackman
在法国,有一个颇富罗宾汉式侠义精神的艺术组织UX,它的目的不是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各种非正规手段潜入法国文化机构的地下,偷偷修复被法国政府忽略或者无力维护的文物。他们用这种办法修复了先贤祠的大钟,还在地下举行了无数次文化活动。
第一个报道UX的美国记者Jon Lackman,在“连线”杂志中将他们与电脑黑客相比较。“他们行动起来,铺设电线,占用网络,占用电力,为了他们的艺术事业。”
通过他们的黑夜行动中,整个巴黎都似乎充满了可能性:每个锁眼都像一个窥视孔,每个地道都成了一个入口,每栋黑暗的建筑都成了一个舞台。
30年前,在夜晚的死寂中,6名十来岁的巴黎少年聚集在艾菲尔铁塔附近一个小咖啡馆里,准备着一次冒险。他们抬起街头一个滤栅,顺着梯子下到一条地下隧道里。那是一条没有照明的水泥通道,内有一条线缆,他们顺着这条线缆,走到它的源头:法国通信部地下室。
6名少年用几个小时把这栋大楼跑了个遍,一个人也没碰着。最后他们终于在一张办公桌的抽屉底部找到了想要的东西——通信部的全市地道网络地图。
他们是从通信部的前大门离开的。街上没有警察,没有行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空荡荡的塞古大道上,于日出之际各自回到了家。这趟任务完成得如此轻松,以至于六名成员之一娜塔莎不禁自问她是否在做梦。她最终得出结论:“不,不是在做梦。如果是在梦里,事情会复杂得多。”
这次偷偷摸摸的行动不是为了抢劫或者窃密,多年后,这6位少年成立了一个名叫UX的艺术组织。UX是“Urban eXperiment”(城市实验)的简写,他们的工作是小心翼翼潜入地下,完成了令人震惊的文化保护和修复工作——“复苏祖传珍宝中那些众人看不见的、政府已经抛弃或者无力维护的部分”。
如今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精确地图要将所有城市的神秘之处抹杀殆尽,但UX似乎拥有着另外一个完整、深入、潜藏着的巴黎。它把整个城市(包括地上和地下的)都变成了自己的画布,其成员能进入每一座政府建筑,每一条狭窄的电信地道。这种自信来自UX对于巴黎地道网络的熟悉——这个地下通道网络长达数百英里,由相互连接的电信、电力、水道、下水道、地下墓穴、地铁和有几百年历史的矿道组成。像电脑黑客侵入数字网络、秘密掌控计算机一样,UX成员在巴黎各大地下通道和房间里完成他们的秘密使命。
2006年,UX的一个核心小组耗时数月,潜入先贤祠——巴黎著名胜地,葬有法国许多杰出人物的遗骨。他们在一个储藏室里建立了秘密工作室,接入了电源和网络,还摆上了扶手椅、各种工具、冰箱,以及一个轻便电炉。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勤勤恳恳地修复了先贤祠的19世纪大钟,这座大钟从1960年代起就再也沒有鸣响过。当附近居民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钟声响起——准确地报着整点、半点、一刻钟——肯定十分震惊。
目前,他们已经完成15次类似的秘密修复行动,足迹遍及整个巴黎。
修复艺术品的地下潜入者
1981年9月,巴黎中学生昂德雷吹牛说,他和朋友彼得常常通过地下通道去一些地方,他们下一步要去先贤祠。大话说到最后,昂德雷为了免于丢面子,只好带着他的新朋友到先贤祠一游。他们躲在先贤祠里,一直等到关门。事实证明,他们晚上在先贤祠活动极其容易——没有碰到保安,没有引发警报——这次经验让他们灵感爆发。
他们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很快,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潜入某个建筑物,地下道地图扩展了他们的秘潜范围,很多巴黎建筑通过地下室与这些通道相连,那些地下室的保安就和地道一样差。昆茨曼说,从表现上看,大部分官员似乎相信一个荒谬的准则:官方禁止人们到地下道去,人们就不会去。昆茨曼(Lazar Kunstmann)是昂德雷和彼得的同学,很早加入了这个团体,日后成为该团体的非正式发言人。
有人可能会想,那些成立UX的少年与如今在街上寻求刺激的孩子真的有什么区别吗?但是,当UX成员冒着被捕的危险潜入地下,他们内心对想要修复的各种艺术品怀着十分严格、几近科学的研究态度,在全城进行探索和尝试。
基于成员的不同兴趣,UX发展出了一种蜂窝状结构,不同的分支小组分别负责绘图、潜入、地道探索、砖石建筑、内部通讯、文档整理、修复和活动策划工作。其100多个成员可随意变换角色,可以使用组织拥有的所有设备。UX没有宣言,没有宪章,没有制度,只是所有成员都要保守组织的秘密。成员资格只能靠老成员邀请而获得,当组织发现有些人已经开始从事类似UX的活动时,会讨论是不是邀请对方加入。会员无须交费,奉献的只是自己的才华。
他们如何处理他们掌握的这些通道和空间?在一些地方,UX在通道里安装了伪装的连接装置,其中之一是所谓“旋转水池”。这种装置位于某条地下通道尽头,看上去像是一个下面有水的井盖,事实上,它是通向另外一条地下通道的活盖。昆茨曼说UX很喜欢做这样的发明,但他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在足够的地方进行铺设。
除了修复艺术品,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举行无数秘密的戏剧表演和电影放映活动。放映日晚上,他们通常会放映至少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相互有关联,但联系又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对这种关联不予解释,而是让观众试着去发现。
一个夏天,UX举办了一个以“都市荒漠”为主题的电影节——指的是城市里那些被人遗忘、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间。他们认为,对于这样的活动,理想的举办地点当然应该是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地方。他们选了夏乐宫(Palais de Chaillot)下面一个房间,这个地方他们已经了解一段时间,可以随便进入。而且,这栋建筑当时是巴黎著名的法国电影资料馆所在地,使得它显得加倍适合这个主题。他们建了一个酒吧,一个餐厅,一系列展厅和一个小小的放映室,可容纳20名观众,多年中他们每年夏天都在那里举行电影节。“每个社区电影院都应该是那样的。”昆茨曼说。
重新启动世界的心脏
先贤祠大钟的修复是由UX下面一个名为Untergunther的小组完成的,其成员专门负责修复。先贤祠是UX的起点,UX曾经秘密在那里放电影、展览艺术品、上演戏剧,他们对先贤祠怀有特别的感情。
2005年,一次举行活动时,UX成立人之一让-巴蒂斯特·维奥(他是少数使用真名的UX成员之一)近距离察看了先贤祠里失修已久的大钟——19世纪的工程技术奇迹。
维奥是一名职业钟表师。那年9月,维奥说服另外七名UX成员与他一起修复这口钟。因此,由于氧化,大钟受损严重,如果再不动手,恐怕就只能重做大钟每个部件,而不是进行修复了。“那样它就不再是一个修复品,而是复制品了。”昆茨曼说。
随着工程开始,这次修复对UX团队也带来了一种神秘意义。在他们看来,巴黎是法国的中心,曾经也是西方文明的中心。而拉丁区则是巴黎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先贤祠位于拉丁区,专为法国史上伟大人物而建,其中许多人的遗骨就留在这里。在先贤祠内部,有这样一座大钟,像心脏一样跳动着,直到突然停止。他们希望重新启动世界的心脏,为此,八个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这项秘密行动。
他们首先在先贤祠上建了一个工作室,就在它的穹形屋顶下面,一个从来没人(包括保安)进去过的地方。用昆茨曼的话说,那个房间就像一个“漂浮着的空间”,缀有狭窄的窗户。“我们可以在15层楼高的地方俯瞰巴黎美景。从外面看它像一个飞碟,从内部看像一个掩体。”工作室里放了八张加了厚厚软垫的扶手椅,一张桌子,书架,一个小酒吧,还有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所有东西都经过特别设计,能折起来放到木箱里,就是先贤祠里常见的那种箱子。”昆茨曼说。在寂静的夜晚,他们爬着无穷无尽的楼梯,把木材、钻机、锯子、修钟设备以及其他所有东西拖上去。他们花了4000欧元购置这些东西,全是自己掏腰包。在外面的露台上,他们还开辟了一个菜园。
就像被小偷轻松盗走珍贵艺术品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样,先贤祠的安保十分缺乏。“不管是警察还是路人,没人对我们这些从前门进进出出先贤祠的人产生过什么怀疑。”昆茨曼说。不过,这八位成员还是用看上去很正式的假证章伪装了自己。每个证章上都有照片、微芯片、先贤祠的全息图,以及“除了给人留下印象全无用处”的条形码。只有很少情况下,过往的警察会问些问题。大部分情况下,对话是这样的:“你们晚上工作?我们能看看你们的证件吗?”
“在这儿。”
“好的。谢谢。”
工作室建成,彻底打扫干净,八人投入了修复工程。第一步是了解为何大钟如此残旧,“可以说是进行某种尸体解剖。”昆茨曼说。他们发现大钟遭到了某种破坏,好像是某个人——也许是不愿再一周上一次发条的先贤祠员工——用一根铁棍打坏了大钟的擒纵轮。
他们把大钟的机械装置拿到工作室。维奥对全组人员展开了钟表培训。首先,他们要用“钟表浴液”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为此要从一楼的公共卫生间提3升水上来,再加上500克性质温和、容易溶解的肥皂,25厘升氨水,1大汤匙草酸——所有这些东西在超过华氏280度的高温里混合在一起。用这种溶液,小组成员勤奋地擦洗着每个机件。然后他们修复了机械装置的玻璃罩,换掉坏了的滑轮和线缆,重新制造了一个擒纵轮(一个锯齿状的轮子,控制着大钟的走动),以及那些丢失的部件,比如摆锤。
这一切完成之后,2006年夏末,UX把修复已经完成的消息告诉了先贤祠。他们认为管理者会高兴地把修复之功揽为己有,接管维护大钟的工作。
他们用电话通知了先贤祠馆长伯纳德·让诺,主动提出可以面对面详谈这件事。小组派了四个人前往。但他们惊异地发现,让诺拒绝相信他们的故事。当他们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工作室时,他大吃一惊。“我想我需要坐下来。”他喃喃地说。
更让他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先贤祠管理方决定起诉UX,一度甚至要求判他们一年监禁,赔偿48300欧元弥补损失。让诺当时的副手巴斯卡尔·莫奈现在是先贤祠负责人,他做得更加过分——他找了一个钟表匠,要他把大钟重新封死,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但那位钟表匠说他最多只愿意把一个部件拆下来,就是那个擒纵轮。
闻知此事后,UX成员迅速溜进先贤祠,把擒纵轮拿回来自己保管,希望在未来的某日,一位更明智的管理者能欢迎它的回归。与此同时,先贤祠管理方在这场诉讼中败北,它又起诉了一回,再次失败。因为法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约束侵入行为或者改善公共设施行为。
在法庭上,一名检察官称政府对UX的起诉是“愚蠢的”,但至今先贤祠大钟仍然没有恢复工作,它的指针停滞在10时51分。
每栋黑暗的建筑都成了一个舞台
2010年5月,巴黎的现代艺术馆发生一起艺术盗窃案,根据《世界报》报道,歹徒单枪匹马,在凌晨3时50分拧开了一扇窗,切断了一扇门上的挂锁,大摇大摆走过展厅,分别拿走了莱热、布拉克、马蒂斯、莫迪利阿尼和毕加索一幅作品。昆茨曼叹着气,他非常了解出事的博物馆不像样的保安措施。“外面挤满了涂鸦艺术家、无家可归者和吸毒人员。”他接着说,这让盗贼非常容易混在里面,整夜偷偷观察博物馆的窗户,了解保安是怎样换班的。
昆茨曼告诉记者,偷一幅毕加索的杰作一点都不困难。
UX对博物馆的安保措施研究很仔细,有一次,一名UX成员发现一家大型博物馆存在严重的安保缺陷,她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这些缺陷,在午夜时分,把它放在保安主管的办公桌上。但这位主管并没有修正安保问题,而是去了警察局,要求他们对潜入者提起控罪,警方没有这么干,不过还是告诉UX低调点。
昆茨曼对当代文明很悲观,在他眼中,这次被盗事件凸显了当代文明的诸多最糟糕的缺陷——它的无作为、自满、无知、偏狭和疏忽。他说,法国官员只关心保护和修复那些受到数百万人倾慕的珍宝——比如卢浮宫,不那么有名的地方就被忽视。如果它们正巧位于公众视线之外——比如说地下——就只能自然凋零,哪怕只需花一百美元补上裂缝。UX照看的就是这些不得宠的东西:法国文化中那些不受人关注、被人忘却的文物。
是不是UX从现代艺术博物馆偷了那些画作?这难道不是一种完美的方式,可以警告法国人政府在保护国宝方面是多么失职吗?昆茨曼说,“不是我们的风格。”
UX成员不是造反者、破坏分子、游击队员,或自由战士,更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修复大钟不是为了让国家难堪,更不会做梦去推翻政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些地方?昆茨曼用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家里有没有植物?你是不是每天给它们浇水?你为什么要浇水?因为,”他接着说,“不浇的话它们就会死,变成一堆没有生命的破烂。”这就是为什么UX觉得那些被遗忘的文化珍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接触到它们,看见了它们。”他说,他们的目标并不一定是让这些东西复活。“假设我们修复了一个防空洞,肯定不是因为希望发生新的轰炸,人们可以再次使用它。假如我们修复了一个20世纪早期的地铁站,也不会想像法国电力要求我们把20万伏电压变成2万伏。不,我们只是想要尽可能接近一个正常运行的状态。”
在经历几次和政府打交道之后,今天的UX尽量保持低调,避免官员或者其他人插手他们的行动,他们试图把自己隐藏在大批到地下空间举办派对或观光的普通巴黎人中。
为何在修复之后仍让那些文化遗产保持隐秘状态,UX有一个简单的理由:这种隐秘状态最初让它们遭遇管理者的忽视,但修复之后,这种状态也会成为保护它们的因素,使它们免受掠夺者和涂鸦的伤害。昆茨曼说,他们知道自己无法保护大批需要修复的地点。“尽管如此,因为我们的修复,一些遗迹,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不会再消失,知道这一点,那种满足感是无法言喻的。”
他们如何在众多需要修复的地点之中进行选择呢?“我们不能说得太多。”他回答,“因为哪怕只是进行一点描述,都可能泄漏它们的地点。”比如说,有一个地点“在地下,位于巴黎南部,离这儿不远。最近我们才发现这个地方,但大家对它很感兴趣。它跟位于它上面的那栋建筑的历史完全抵触。通过察看地下的东西,我们注意到它跟人们所说的历史并不吻合,从某种角度说甚至是相反的。”
昆茨曼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巴黎,那个地方是造假币的人曾经在巴黎造币厂的地下室活动吗?还是说圣叙尔比斯教堂建在了一个异教徒的地下神庙上面?突然之间,整个巴黎都似乎充满了可能性:每个锁眼都像一个窥视孔,每个地道都成了一个入口,每栋黑暗的建筑都成了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