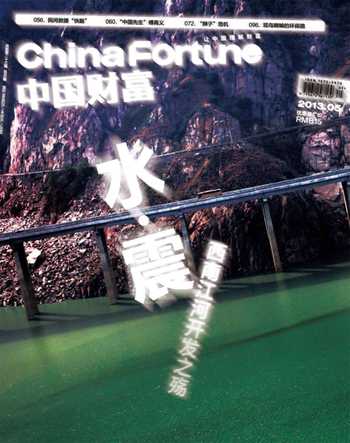电影作者·闽地行游
毛晨雨
我与柯金源、冯宇、鬼叔中所居住的新乡村示范点,几纵几横的成片规划,客家天井厅堂传统的格局,柴火灶、偏厢这样的功能需求都一律取消了。孤立冷寂的内部层级构造,难以想象到古建筑中从容舒展的天宇垂青、天地会面、天人合一的人文视野。去掉了这个视野就是去掉了居住的文化。
培田春耕节“乡土影像节”正好与两年一度的云之南影展时间重叠,云之南影展被迫改移大理且被取缔了公开放映,一场独立电影领域神往的盛会湮没不举,大理活动亦基本是电影作者的自发神游。培田的乡土影像节则在三农学术框架中存有了一丝展映的合理性,当然它也只语焉不详地放映了五部作品。
为此次乡土影像节,我临时完成了《拥有》的拼贴版本。放映的文件在出发前三小时才完成,我个人还是期待能够用新作与初次见面的朋友们交流。
鬼叔中宁化“清明计划”中的列位贤达,孔德林、杨韬、胡子等诸位;还有在培田拍摄近二年的邓伯超、邓世杰“韩汀客家电影”组合,郭熙志、冯宇、龙淼渊夫妇自驾过来,以及台湾的柯金源,以及关注大陆独立电影文化的钟永丰先生的踊跃参与,使得培田村一时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独立电影交流平台。
遇到有味的人,做别人生活中有味的人,都是让人快悦的相遇。
我在电影中使用《潇湘春雨》音律时,我是期待能遇着可知音可尽言的贤达,所谓清谈,就是这电影哪怕就为三五人所映,就为彰显你愚痴的狷狂,就为发作你心中郁积的愤懑,都让大家觉得不累不牵。
我个人对独立电影领域中隐约潜行的那种龌龊之气早已厌倦,能在没有功用的小山野中放映新作,心中不累不牵。独立电影至今天之情境,当是该舍弃掉鄙夷的诟詈了吧,谁能给我正义之音,谁能给邓伯超们继续制作的空间?
还是退回来实在,首先得存真,存真尚有格律的余地。
厦门,孔德林
4月12日凌晨,我从上海虹桥出发,八点多就到达厦门,在机场接我的是孔德林、杨韬二兄。三小时前我还在微博上与孔兄有交流,我的电影中使用了孔兄在宁化一面残垣上所作的傩神壁画。孔兄情趣纯真清雅,艺术行为自觉自律。画室中墙上地上布满了大量作品,绘画、雕塑、装置、闲置物,井然安置,慎重、闲适、自在,如其人。
待我们在机场接到台湾过来的《退潮》作者柯金源,以及台湾制茶且喜萤火虫的张伯志先生,已是下午三点。
由此,从厦门往龙岩培田的高速正好向着西下太阳而往。残阳落入了西部的群山中去,天幕暗涩下来,在黑色的村野之间,一众人早已聚集起来。邓伯超和邓世杰的旅馆成为聊天场所。古村落朦胧的景致藏匿着黎明的想象。
疲惫和睡眠严重不足是我要克服的,我提醒自己。但还是被简陋的新农村席梦思弄醒来了。因为主办方培田社区大学要端平住宿资源,我们一众人被分散到村落各个小家庭客栈。我与柯金源、冯宇、鬼叔中所居住的新乡村示范点,几纵几横的成片规划,客家天井厅堂传统的格局,柴火灶、偏厢这样的功能需求都一律取消了。
孤立冷寂的内部层级构造,难以想象到古建筑中从容舒展的天宇垂青、天地会面、天人合一的人文视野。去掉了这个视野就是去掉了居住的文化。
风物本相宜,愚人自困之。新农村建设中的区块规划、建筑空间设计、人文语境的储存,是需要心去体会的,你从外面不可能看见。
邓伯超的陷阱
2011年云之南一聚后,没想到两年后在培田客家村落再见到邓伯超。他与制片邓世杰在福建龙岩和广东梅州这个客家文化地域穿行了快两年,他们的制作恐怕难以持续进行下去。
我对邓伯超作为一个四川乐山人拍摄他不熟悉的客家文化,保持我个人的意见。之前我曾介绍给他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及《蒙塔尤》、《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等书,我想提示他“对话作为他者的异文化”需学理来保障。邓伯超的《余光之下》在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海南拍摄,若将纪录文本置于观察的主体文化语境来看,这个作品被一种外在的游离的视觉节律牵制着离开了,所谓元神并没有归位。如果置入电影——被视觉和听觉控制的自我强权的范域——这种观察的文化隔阂也不可能逃脱本体的自我申述。
培田春耕节仪式上,邓伯超单手骑着摩托车抢镜头,我跟邓世杰说或许拍摄一个镜头就足矣。“对话”怎么去建立,不光在异文化之间,就是在与自我的观照中都是个伦理问题,而且在具体文本的生产上可能存在着一种精确的算法(不是那样的被动结构和可任意地主动拣选的)。邓伯超的制作无疑会给他储备难得的文化交流经验,至于电影作品是否客家人的民族志文本,都将为他的制作视野提供难得的辨识机缘。
邓伯超是热情的,那种没有畏惧的热情,向沉寂的河流中投入一股鲜活的制剂,他并非要摧朽成木,只是要激越地告诉你他的见闻。在独立电影制作自身将因不备案而非法的政治语境下,没有畏惧的热情和集体的非理性的投入,给我们呈示的除去勇猛、坚毅、果敢的身体之外,我還想停留下来,停留下来审视我的活力,审视我能为下面的青年作者做些什么。很遗憾啊,思前顾后,我基本做不了什么,唯有警醒同勉:警惕电影地毯的陷阱,做好一场十年二十年的个人战争准备。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
郭熙志老师对青春开始有留恋。青春可以是青葱的烟草,毒害的记忆和自由的记忆,麻痹的神经和自省的行游,时代的陌路人和滚烫烙手的烧饼,既成的话语和平等的对话权利。4月13日晚放完《拥有》后我们在邓伯超拍摄对象的亚春叔家两桌连坐,各类土产泡酒包括龙淼渊的XO补充,酒精是可以享受的即时的热情。所谓盛宴,大抵是汗腺分泌的热度都可以燃烧起来。还是感谢老鬼、冯宇、小龙、德林、杨韬、胡子、小赵、柯金源、钟永丰、范立欣、蒋亦凡及女士们等等一众入酒局者,桌面上纵肆错愕的对攻是记忆深刻的。
谁是主体?
乡土影像节并没有吸取学者们的多少关注,这很正常。我曾断言“中国学者解决不了中国三农问题”。其缘由即在于中国三农学者们学术态度上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以及近亲圈子化和实践官僚政治化;中国学者的认识型基本类同政体极权认识型的同构。
在“影像与乡土”主题论坛上,有学者试图延续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文脉,建议农民们忘记党的符号、自主建设主体。这种文学化的描述甚是滑稽,怎么能将党的极权体系置若罔闻呢?甚至,温铁军告诉农民“你们已经是小资产阶级了。”如此滑稽的智识层,农民何必去期待。知识分子或者官僚知识分子能有的作为就是假装着倾听农民的声音,然后从知识“理性”的视野规制在下的农民们学着“理性”起来。学者们号召农民“要理性一点地正视乡村社会大转型!”要学着理解政府的努力、看到政府的阳光、感同身受政府的难处。
这就是目前中国三农学者精英群体。
我们能反击的是质疑中国社会学视野的常识缺失。弯腰屈膝的农民如何直身起来做自己的奴隶主?首先得摆脱被奴役的链条再说。
三农事务应该站在三农基础诉求上考虑,主体应是农民自己。
15日中午,我与钟永丰、范立欣等一行离开培田中转厦门。杨韬兄全程招待我与钟永丰。培田期间,我跟钟永丰就鬼叔中导演的电影定型进行了交流,之前与钟永丰相遇是在前年安徽黟县的碧山丰年庆上,那时没有机会单独聊天,我依然强调鬼叔中作品的风土特性及“风土电影”型塑问题,钟永丰担心如此会弱化其客家文化的内涵。
之后,我们聊侯孝贤、杨德昌,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恋恋风尘》和《风柜来的人》,渐渐算熟悉。再回厦门来,如愿感受到了海。虽居上海十几年,海的形象在厦门才真正具体化,赤足踩在绵湿的沙砾上,捡拾一地的小贝壳,逐层的浪涌动着来沉寂着去,跟我要的自由那样像:颤栗着勇猛地行游,沉寂平静而归。之后的海鲜和福建茶道则在一夜的细细体念中与海的形象榫接在一起。晚霞过后,海的不远处,就是金门了,一片灯光起来,突然浮现出一个安全的异邦。的确,那里是一个安全的异邦。
以浅显札记向云之南影展和电影作者们问候!
培田春耕节
福建连城县宣和乡的培田古村,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群,被誉为“福建民居第一村”。2013年4月13日~15日,培田村举办了第二届培田春耕节,活动包括举办乡村电影节、乡村讨论会、乡土美食集市、民间手工艺展、农具文化展,众多关心乡村命运的专家、实践者与村民一起讨论乡村的发展和未来。这些活动均由培田村民自己组织协调,社区大学志愿者协助举办。
“祭土地”
春耕节开幕式上举办了“祭土地”的仪式,人们牵着春牛,在锣鼓声、欢歌声中穿越培田古街,来到田间地头试犁,栽种自己的树苗或庄稼。
培田旧八景
一景:云霄风月
二景:苦竹烟霞
三景:松岗琴韵
四景:新福钟声
五景:崇墉秋眺
六景:总道宵评
七景:曹溪耕牧
八景:魏野渔樵
培田新八景
一景:杰阁吟风
二景:平桥望月
三景:西山树色
四景:南院书生
五景:芳泉趋汲
六景:古寨观耕
七景:蛟潭晚钓
八景:马刹晨钟
培田民居特色
由三十栋高堂华屋、二十一座古祠、六家书院、两道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构成了紧密有序、错落有致、布局科学合理的培田古民居建筑群。
外墙为清一色防火砖,内建木质构架,门楼泥塑石雕,屋脊飞檐彩陶,梁檩窗屏木刻雕花彩绘漆画。
官厅、大夫第、进士第等庄园式休闲逸乐型的建筑,结构为“九亭十八井”,每座占地近七千平方米,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厅与庭院结合,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及自然地理特征。
“爱故乡计划”
第二届培田春耕节是“爱故乡计划”中的一个项目。“爱故乡计划”在闽赣两省设有6处试验点:分别为福建连城培田客家社区大学、福建汀塘社区大学、厦门国仁工友社区大学、江西大湖社区大学、福州工友之家金山社区大学、福州故乡农园。计划缘起于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于2012年初正式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