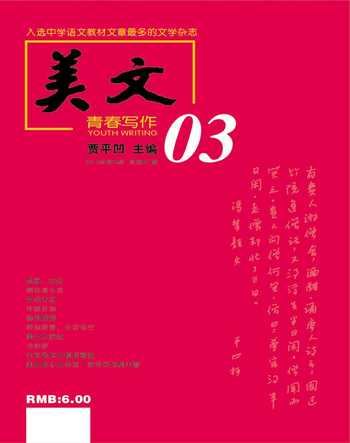花海
黎炘
关于花海这个词汇,我从不愿轻易说出。就如新采撷的花每在跌宕的时间里曝露一分,它的香气便会销蚀一分。知道吗?我曾想过属于我们的回忆都随着雨水下落在这片花海,躲过我们,在花朵与花朵的罅隙间闪着它们自己的光。
花海的北边,是一条切割了地平线的铁轨。起风的季节,洒落的花瓣就能将它掩埋,你便不会想到在或粉或白的花海下还隐藏着一条深褐色的轨迹。缓慢驶过的火车浮在花海之上,那场景,美得可以晃出眼泪来。我想若是风肯陪着它旅行,它们会去你说过的远方。
——题记
四月份的梅雨,我栖息在江南小镇某处潮湿的屋檐下。对面檐头青色的瓦菲间不住地绽开细碎的水花,在檐角缓缓笼起一层清淡的烟雾,絮语着一些难于言说的温柔。我索性光脚循着青石街走进巷弄,濡湿的发丝柔软地滑过眼帘,心中觉得连惆怅也仿佛是旅途中寻获的工艺品般精巧。
许多年后的如今,在这个被岁月反复拓写得不温不火的水乡古镇,我开始狂热地怀念记忆里一点点淡出的那片花海。
那个夏天,因为响起花开的声音而明媚。安坐在一堆草里远望着花海哼着歌。他目光闪动,灿烂得如同那些花开,而我在一旁不解地问他:“你真的就这样退学了吗?”
安把一棵草衔在嘴角,眨着眼,“不是真的还是煮的?”他有着男生少有的大眼睛和酒窝,我看着他的脸,觉得花朵让他的脸上染出纯真美好的光晕。
我坐到他身边,从一片浮花软草里随意地挑了一株野花在手中摆弄,“你的成绩很好,再考虑一下吧,我觉得你会后悔的”。
安仰面叹了一口气,接着很大声地笑,“就让以后去后悔好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些事你不马上做,那么,你就老了”。
“可是……”我本打算说话,安用手势示意我停止。他把身上的蓝白色校服外套脱下高高丢开,校服张扬地跃过落日,随风滑落那抹看不清轮廓与边际的花的海洋。消失。像一只鸟。
“我……终于……自由了!”
声音在花骨朵里碰撞,产生孱弱的共鸣,我们听见花海中疏疏落落的回音同远处流转的山岚中燃起了的浓白烟雾一样,缓慢得如同凝固。
看着安挥着双手的背影在日暮里涂上艳彩,心中倏然有了异样的情绪。那抹背影在我的眼前被慢慢推移,越来越远,在我面前追不到的地方晃成一个真切的虚点。
我开始明白,安就像一只鸟。而我缺少了洒脱的翅膀。
曾经不止一次地和我描述他的愿望:在黄昏转向傍晚时写诗,写很多的诗,直至集结成一本厚厚的诗集发表。我问这个愿望会实现吗?他笑,摇摇头:难,很难的。但是安终于还是把我一个人扔在学校里,朝着那个愿望一骑绝尘地狂奔。
没有安的教室仅仅发生空出了一个座位这样的变化,高考的逼近早已经使我们无暇顾及其他事物。唯独班主任在安退学后的那一个月里喋喋不休地用尖刻的语调说安这孩子脑袋有问题,将来有他哭的时候。他反复说着那样的话,而始终,我都皱着眉头似笑非笑。
当安不和我一起上学以后,我只好一个人过几条街去吃难以下咽的面条;一个人在老旧的借阅室写细密潦草的笔记;一个人去反复地算三百多天后必将到来的日子;一个人被迫无奈地完成誓师大会的演讲。
那场誓师大会之前,我们只花了三分钟就把被曝晒到闪着白光的空操场填满,班主任满含期待地将稿子塞给我,我胸闷气短地宣读着。而那时我突然用眼角瞥见人群中一张张涨成猪肝色的脸,在煞白燥热的日光里异常突兀。接着听见稀疏的掌声,泪水就失控地涌出眼底。我在心里想安才是对的,此刻他一定静静地坐在斑斓的花海深处,用指尖点过每一片花瓣,然后随意写下一个句子便可以轻巧地叩开心门。汗水一层一层地渗出劣质的校服衬衫,看着那些木然的脸,我想如果我停止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是大声喊出:我很累了、很无助、很迷茫。他们还有安就会讶异地回过神,然后认真地为我鼓掌。我甚至想着就这样对着把我围在升旗台上的人们大哭一场,泪水会像雨水一样浇灭这个过分响亮的夏天,让它学会安静下来。
我也知道我不会有这样的勇气。那些句子从我的嘴巴里变成无意义的咿咿呀呀,在我做完了所有的发声练习后,誓师大会宣告结束。会后,操场遗留下来杂乱不堪的垃圾,班主任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演讲感情真挚,很好。
我在几天后发现安的座位空了下来之后,我右边的视线变得非常开阔。我会长时间地透过窗子看教室外的那棵树,即使是上课也如此。那棵树的叶子总是比周围的叶子黄一点,我真担心它会枯死,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我的目光的期盼而茂盛起来。我不厌其烦地看着树冠在下午两点满是陈旧感的阳光里起伏颤抖,或许那就是那片辽阔的花海某一朵花儿对着风轻巧摇曳的样子吧。
其实窗户前还有个女孩,叫晴。当阳光款款飘进来,她逆着光的侧脸像一束栀子花般安恬。一个为微醺的下午,我透过窗子张望那棵树时发现她在看我,而后我渐渐习惯在看树的时候也去看她,或者,我只是在看她。
一次,晴突然走到我的座位边。
“哎,你怎么上课时总是看我?”
“是吗?没、没有吧”。
“没有才怪呢!”晴小声嘟囔。
接着我看见晴翘起嘴角,露出好看的微笑。然后我跟着笑,她看着我笑得更为灿烂。
我们从此在一起了,我觉得晴的笑是一株沾着雨水的茉莉花。
假日里,起风,没有云。我骑单车路过花海,安如约等在那里,像是在等某片天空里不期而遇的飞鸟。
我问:“嗨,最近还好吗?”安取出他那个灰色封面的硬皮笔记本,说:“看吧。”安的字迹清秀,连删改的圈点都做得很工整,显得尤为精致。看得出,这就是安想要的。“校园生活过得怎么样?”安问我。“你走了以后班主任一直在骂你”。
我翻看他写的诗,答非所问地说。安听后哈哈大笑。
我想到了一些似乎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他,“安,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写诗呢?必须要弃学吗?还有,什么样的句子才会被称作成诗?”
安转过脸认真地看着我,我相信这些问题安一定反复思考过了,现在完全可以对答如流。
“你有没有想过,海子为什么要自杀?而且选择了卧轨这样的方式?”
“是……是因为所谓的死亡意象吗?”这突兀的问题使我无从回答,下意识地,我看了一眼被花儿小心地隐藏起来的铁轨。
“不是,因为写诗主要是精神的一种寄托形式。而当这种形式超脱了一定范畴,也就是可以引起世人共鸣的时候,这个作者本人的精神与现实会产生隔阂”。
“你没有发现往往许多诗人的感情生活都是不幸的吗?只有海子可以听见雪吃草的声音,只有他的心中永远有一个春暖花开的地方……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不能把他留下来”。
安说,萨福是如此;茨维塔耶娃是如此;普拉斯,更是如此。
“也许诗人天生有敏感的神经,和所有人一起陷入沼泽的时候他会最先找到一片花海”。安的话使我颇有感触。
他点了一下头,“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幻想着地图上的某一个角落肯定标注着一个开遍花的岛屿,这片花海就是它的一个碎片。那里的飞絮与落花可以将你的存在给吞没,你甚至能够在天空中俯瞰到蔚蓝里的一抹缤纷的色彩,就是因为它。你可以把它以外的地方都定义为尘世,可以没有负担地在那里生活好久好久,连时间也会纯粹得如同永恒不变”。
从这一刻起,我完全地接受了安是“诗人”的身份。当他像是问我又或是问自己存在那样的岛时,火车蓦然从远处驶过,惊悸的天空将一声鸟鸣的痕迹无限的拉长。
这里是一片浮在花上的海域,它在蓝天下温柔的燃烧着,而晴在初次来这里的时候便对我说她很喜欢。我想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晴就像花一样的女孩。我用许许多多的花儿形容她,以至于想去种许许多多的花,让每种花儿的花期相接续使得一年四季都不显得寂寞。我想一定是她的名字带有神奇的魔力,仿佛和她在一起时总是晴好且闻见花香的天气。好吧,虽然后来醒悟是因为在雨天里我们的伞上会叩响滴滴答答的节律,晴的雨靴走过积满水的落叶林,轻得不留下一丝声音令我不再因下雨而不安。
晴穿着及至脚踝的连衣裙和我分别走在两条铁轨上,那些花朵这时又仿佛是开在岸边,晴弯下身花朵就会擦过她的脸颊。我们就这样走着,走过花海和木屋,走过草地和溪流。就像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如此:花都开好了,我们一直走着。
晴一边闻着花的香气一边问我:“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啊?”
“因为我收买了你的好朋友啊,她说你初中时很喜欢一个男孩子后来却迫于家长的压力而分开了。我想我也许会让你快乐起来也说不定呢”。
她用讶异的眼神看着我好一会儿。半晌她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说:“我们说好了永远在一起好吗?其实我真的很怕,很怕我们会重复我的上一次的经历。事情总是在偶然的状况下变得无序和糟糕,未来不是谁也不能预料的吗?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永远在一起……”
“相信我,好吗?”我走过去轻拍她的肩膀,嘲笑女孩子天生的多心。
天边有云朵的影子在摇晃,琥珀色的黄昏恣意流散。
但或许晴说的是对的,事情的发展从来不是我们可以意料的。高三的时候我们居住的小镇将被行政改制的消息已经传遍,远处高高低低的起吊机撑着灰雾迷蒙的天,空气变脏,夹杂着土腥味和水泥石灰的粉屑。有大批的房屋被拆迁,而原先火车轨道边的花海及周围的大片土地未来将是某大型化工厂的建设用地。安想到这些难过与愤懑就无从发泄,已有一些从我们记事起便存在的楼房陆续被清除,尘埃高高的扬起,包裹着我们住的世界摇摇欲坠。安说:“我以为我们是不会变的,我以为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是不会变的。”但也许人类已经有如此能力,抹去一处几十年的存在容易至极。而另一方面,班主任终于找到了更加值得喋喋不休的话题:他试图用行政改制后的种种好处,及将要投入建设的大型化工厂能为镇上创收的效益,阐释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我听着,已经非常厌恶去笑了。
当挖掘机肆无忌惮地开始残酷的工作时,我们以为的花海原来脆弱渺小得可怜。死去的残朵在地表升腾起巨大的香气,我知道,彼此呼吸的是那些花儿积蓄在血脉里的芬芳与悲痛。
安告诉我们他要外出旅行生活,我对他总是突然作出的决定不满。在他离开小镇的前一天,安、我还有晴开始了一次“遗失风景一日游”,我们去了彼此小时候的幼儿园、父母工作的工厂或破办公楼还有一个掉在废墟里快要找不到的公园。那座公园里生锈的秋千只有晴依然可以坐在上面,这使得我和安有些无奈。安一直用很老式的相机拍着所有建筑物,它们中大部分要被拆除,而幸得保留的另一部分只是延迟到未来的某一天了推倒重建。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听时间的话,认同那些不留痕迹的消失。
我们绕着小镇转了大半圈,安说他还要整理行李便先回去了。我和晴漫无目的的地走了一路,竟然在已成为荒地的花海停下。那是下午五点,天光晦涩。太阳的光划刻下粗糙的痕迹,像玻璃窗上慢慢淌下来的雨滴。我们在暗处看不清彼此,冰冷的空气传递给脸颊轻微疼痛的触觉。突然,晴语调极浅地说:“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我以为是自己触景伤怀的幻听,笑着问,什么?“分手”。她说完就再不愿意开口了。我问为什么?因为无法容许自己所谓的爱情这样地无疾?我用尽各种言辞去盘问,一直到晴哭出了声时我也丧失了所有力气……
我失去知觉地站在那,麻木地看着那些花已变成暗褐色枯茎,它们最终会腐烂,渗入大地。所有画面全都不对了,那个被我无比珍视无比炫耀的青春以如此荒谬的方式义无反顾地离弃我。
安在古镇的巷弄深处安静的走着,雨点如针脚织在他灰色的大衣上。我走到了天井边,四周忽而变亮,院角一株花树发出簌簌响声。安在经历了很多波折后算是真正成为了诗人,经常会在各大杂志上发表新作并且小有轰动。我在处理完工作时会同他去很多地方旅行,我们偶尔还是会聊到晴,她此时已经是两岁小女孩的妈妈,我们保持着朋友范畴的联系。
经历了太多时间的跌宕后我们开始不惧承担这种变迁。当我的嘴边的青苔更深了,我甚至欣然接受它在我的身上凿刻出年老的印迹。
因为当年过于悲愤和突兀的心绪远去了后,安和我同时找到了那座岛——它栖居在心的幽避处,只要闭上眼,花香便漫过脸颊,如一道又一道浅浅的浪淹没我们。
还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