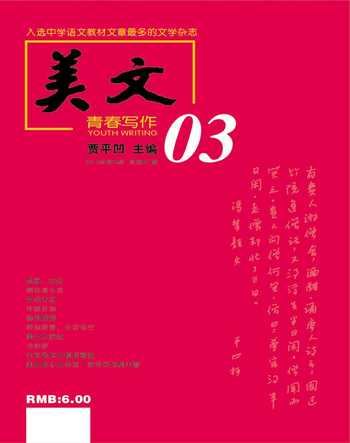别让风吹残你的青春
一
在西北的风里,我似乎只是一粒沙子,风起风住,不知道会飘向哪里。
2012年的秋天,我一个人拎着行李,告别天府之国一隅的小镇,坐上了开往兰州的火车。母亲的眼泪把沧桑的脸画满了皱纹,而远行的风吹白了母亲满头的青丝。飞驰的火车载满一个少年的梦,也载满了一个母亲的祝福与惆怅。
火车驰过月光里的村庄和秋风里的落叶,一个少年的心事正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比谁都更清楚,当火车停下的时候,一颗梦的种子就要被种下,就要努力挣扎着吸取阳光和雨露。
家越来越远,母亲的呼吸在耳边变得遥远,青春让我不得不远离家乡的味道。青春似乎总与远行捆绑在一起,一颗向往远方的心,总是那么的迫不及待。不怕寂寞,不怕伤害,青春的暗语是一把钥匙,把翅膀一打开,我就飞向了异乡的土地。
我还清楚地记得,火车定格在兰州火车站的那天,是一个有风的日子。风中的兰州没有吹出落叶飘如蝶舞的诗意,远望处,光秃秃的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把一颗梦的种子割伤。
我找不到一块能够种出绿色的土地来播种我梦的种子,我只有流泪,在没有星星的夜里。清冷的月光洒满荒凉的土地,寂寞如丝,把我的心一圈圈缠绕得严严实实。异乡的月光太容易让人寂寞,而思念也总是在月光里疯长,长成一棵参天的树,长成一朵天上的云,仿佛垫一垫脚便可以打探到故乡的模样。
这样的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的无聊与漫长。一圈圈的寂寞被我一口一口吞下,我不愿再用任何一个电话去打扰母亲刚干涸的泪水。再贫瘠的土地也不会拒绝一颗梦的种子,再寂寞的心也不会任凭绝望放肆,只要有风,青春的梦就不会断。
也是一个有风的日子,我隐忍着泪水,在兰州的黄土地上种下了我梦的种子。从此,我的青春与兰州这座城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再轻易飘摇。
二
我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孩子,在中学老师的眼里,恐怕都是这个样子。我早已习惯了老师们看我时犀利而又带点轻视与憎恨的眼神,在他们眼里,青春的叛逆似乎就是不孝,就是犯罪。
或许,我的青春真是在犯罪,我都忘记自己到底犯下过多少罪行,加起来会不会塞满一间偌大的教室?在累累的罪行里,有一条却是我无法随意从印象里挥去的,至少在青春的时光未消耗殆尽之前。
这就是几乎在所有老师与家长眼里的滔天大罪——早恋。
青春躁动的心最容易滋生出恋爱的冲动,而我任凭它的滋生,也放纵它的疯长。四溢的花香渲染着青春的时光,我只想谈一场仿佛不顾生与死的恋爱。我在世俗密集的箭雨里穿行,把爱悄悄地藏在幽深的巷子里,藏在浪花朵朵的河流边,也藏在齐腰的荒草间。我小心翼翼地爱着,把年少的张狂全部收敛在第一次恋爱的柔情与艳丽间,害怕走漏半点风声。害怕,不是懦弱,只是为她向青春的妥协,我也愿意妥协。
而在躁动的青春里,恋爱是最不容易守住的秘密。
消息不胫而走,我和她成了教师办公室里的常客。我的罪行累累,老师的旁敲侧击早已在我的耳边起了茧,竟丝毫没有作用。而她的脸薄如蝉翼,经不起三番五次的盘问,我们的爱开始动摇。不过,我们都应该庆幸,都应该佩服自己的坚强,反反复复,分分合合,竟走过了中学全部的日子。
在一个有风的日子里,我们被吹向两个不同的地方。有些话开始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距离是美的尺度,也是爱的坟墓。”青春的自大让我不太相信山一程水一程真能隔断一份纯真的恋爱。
当火车驶出成都的时候,也就载走了那份经得起雨打却经不起风吹的爱,只是我一直未知。
在深秋的风把学校里仅有的几棵梧桐吹得一丝不挂时,分开的消息终于从那个隔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地方传来。青春的自大一下子变成了苍老的自卑,眼泪如线被异乡的土地一点点侵蚀。
爱情,是青春里最难割舍,也是最让人受伤的隐喻。情爱的伤,就如同一支猛烈的催化剂,可以催人一夜长大,甚至苍老。把幻想作为尘土,埋进荒唐而无悔的岁月里,我明白,我和她在剩余的青春里,彼此都将带点遗憾,带点幽怨,带点伤痛,带点怀念,越走越远,直到风把彼此的模样吹得模糊。
风,竟成了一段爱的最后送行者,风过处,我们都飘着。
三
情爱的痛还未痊愈,又添新伤。
在雪花漫天飘飞的季节里,从我日夜思念的故乡传来一个消息:一位朋友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一刻,兰州白茫茫的雪把我的心冰冻成一颗千年寒石,就快要没了知觉。
在把梦的种子带到兰州之前,我就已知道朋友的病。骨癌,一种毫无回天之力的病。我离开故乡的时候,她还用生命的微笑和青春的坚强与病魔斗争着。而她灿烂的笑容只是粉饰着易碎的太平,她把青春的疼痛全部放在黑夜里嘶叫。
她的嘶叫,全部痛进我异乡的心里。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故乡的思念,有一半是对她的担忧。我也早已预料,她没有办法顺当地走完一个人那点本就短暂的青春,而远方的消息还是让人难以接受。青春总是经得起挫折,也经得起生离,却往往难以承受死别。
死——对青春来说,该是多么陌生的词汇!
我开始站在兰州的雪地里回忆她的模样:圆圆的脸,不高的鼻,深邃的眼,齐肩的发……回忆到最后竟是满脸的泪水,泪水很快化成雪,结成冰。我抚摸着结成冰的雪,就像摸着她冰冷的脸和手。
冰冷,是这个世界最后的诀别。诀别,定冷到心里。我怕这时会有风吹来,而越怕,风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吹来。忍不住想对风一阵破口大骂——为什么你总是把青春里最美好的东西带走,留下一地的悲伤?而无力的青春,哪还有精力再骂不知从何处来飘向何处去的风。无所畏惧的青春竟一下子变得如此的惶恐不安而又无可奈何。
我没有从被白茫茫雪覆盖的兰州飞回成都,飞回那个边远的小镇。既然,青春容不下她的模样,那么就让她安静地走吧。如此疼痛的青春,最后唯愿安静。安静地飘进孤寂的山头,飘进杂乱的荒草,飘进无向的风里。
她的青春就这样在疼痛里飘逝,我的青春就这样在风中疼痛。
只是,承受过死别的青春,一定可以承受数不清的生离,也一定可以承受天大的挫折。
四
在疼痛的青春里,我继续写着忧伤的文字。
兰州的雪早已化尽,风也不知吹过了多少个山头。2012年6月中旬,一个又一个电话铺天盖地似的打进我疼痛的青春里。电话那头,有我中学时的老师,有我久未联系的同学,也有我从未相识的某某。
一切都因为一篇我写在疼痛青春里的文字。我无意间写就的一篇文字被用作家乡中考语文卷的阅读文章。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值得自豪与开心的事情。而我在突然而来的铺天盖地的矫情里,却怎么也撑不起愉悦的磁场来。
青春里的疼痛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当一点点的愉悦到来时,却要承受那么多如刺如毡的甜言。我不得不戴上一个慈善的面具,一一回应,一一笑颜,一一鞠躬,一一言谢。
没想到,青春的尽头竟是如此无奈!
我在6月的星夜里给母亲打电话,向她报喜,也或是报忧。劳累一天的母亲言语间全是疲惫,而当我向她说出这个消息时,她的精神一下振奋起来。我知道,在一个农村母亲的眼里,这完全可以说得上是光耀门楣的事情。我那双手沾满泥土的母亲,质朴得对我永远只有鼓励与安慰。
我把心底的那点忧伤全部藏在兰州的夜里。
因为母亲,我青春的梦的种子开始在兰州的风里发芽。原来青春里的风不只是吹走一些美好,也会刮来一些美好。在我青春最后的时光里,风变得那么和顺,变得那么温暖。
无奈,只是昨夜的错觉,前夜的幻影。
暑假,我回了一趟母校,一个学妹要我写一句话给她。我在雪白的纸上诚实地写下我对青春的最后解读——
别让风吹残你的青春。
她看着我疑惑,而我对着她微笑。她迟早也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