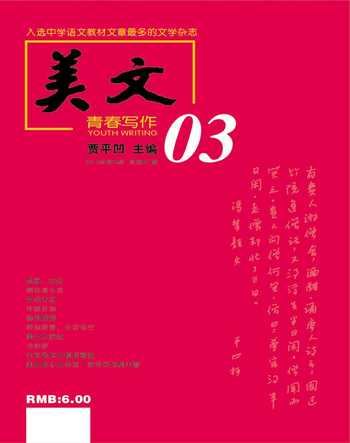冷暖自知
刘文
万圣节正好赶上香港降温又下雨,常年没有秋天的亚热带气候竟然早早进入一场秋雨一场寒,害得我踩着高跟鞋每走一步就陷在水坑里动弹不得。
兀自懊恼的时候突然听到风雨大作中有号啕的哭声传来。眼看前方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漂亮到即使修身挺括的红色洋装上已经沾满泥点,长长的头发软塌塌地堆积在肩膀上,脸上的妆容糊在雨水泪水里成了个硕大的调色盘,依然看起来眉目清秀眼波流转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女孩子。她从背后紧紧抱住一个男生,却被那个男生用了好几次力最终狠狠甩脱,带着砰的一声狠狠撞在马路牙子上。我正要过去扶起她,却看见她颤颤巍巍爬起来,痛得站不直,却依然要踉踉跄跄地去追男生,一把抱住人家的大腿,男生依然执意向前走,于是她就被拖在满地的泥泞里,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哽咽地求那个男生回头。
我追到前面去看了看那个男生的脸,惊人地帅气,高挺鼻梁瘦削下巴,单眼皮薄嘴唇,像某个红得发紫的韩国明星,搭配的却是一脸的不近人情。
走到派对里面,发现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正在舞池中间扭动腰肢的凯蒂身上,她是混血儿,既有西方人高挑的身材修长的双腿挺拔的五官,又有亚洲人细腻的皮肤柔和的脸蛋温婉的双眸。她还是某国际知名奢侈品牌的设计师,品味高贵又独特,哪怕是从热带小岛花几十块买回来一块印染花布,剪出个流苏,在身上裹上几圈,配上腰带和首饰,立刻像是能走T台的模特。她不说话就是众人目光的焦点,却偏生聪明睿智,舌灿莲花,又热情开朗,每次聚餐,只要有她在,就有听不完的段子和数不尽的笑声。凯蒂的老公却和她截然相反,身高不如她,相貌更是平平,闷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导致许多单身男士心里愤愤不平又蠢蠢欲动。
我是在不经意间才看到凯蒂的老公在舞池之外一个偏僻的角落,拿着相机拍着凯蒂舞动的样子,他眼睛里是满满的温情和自豪。等到一曲终了,他为凯蒂送上鸡尾酒和汗巾,用手指梳理她略微凌乱的头发,然后在音乐响起的时候,又默默退到观众席中。
即使我常常自诩理智有内涵,如果这两个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放在我面前,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奔向第一个的怀抱,这个世界上谁有能抵挡住赤裸裸的美色的诱惑呢?
但等到聚光灯灭了,回到生活里,过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却又真的是冷暖自知。寒风肆虐的深夜,也只有自己捏着拳头喊三声,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再说一个故事好了,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姑且称为A和B,都是在纽约大学学国际金融,当时楼市还在飙升,经济还正繁盛,金融衍生工具花样翻新,连自诩个性的美国人,都会向往进顶尖的商学院学金融,毕业后进一家投资银行,运气好的话,一不留神就能赚到几十万上百万。
A和B都是系里面的佼佼者,聪明,努力,有野心又肯实干,再加上人缘和口才都不错,是那种无论哪个大人看到都会说“这个小伙子将来一定有大出息”的类型。
他们命运的分水岭是有年夏天A来了一次香港,又背起背包周游中国,甚至在签证上做了各种手脚,最后偷偷摸摸去 了一次朝鲜。他一看,原来中国和朝鲜与美国相比差那么多,人力物力,技术资源,每一个差别都是一个商机。他干脆留在了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先是休学了半年,后来索性退了学,一门心思做起了企业家。
A再聪明睿智,也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毛孩子,开的第一家公司在谈生意的时候被人在背后阴了一招,眼看到手的合同就飞了。他毫不气馁开第二家,眼看开了个好头,却最终过不了政府那一关,在上报啊审批啊各种繁复冗长的程序中就错失了机会,穷到每天都只能吃泡面,饿到不行就在超市关门前去买打折处理的面包和就快要腐烂的廉价水果。
B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在三家投资银行实习过,毕业之后进了高盛,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有四五万,第一年就买了辆宝马车开,第二年,业绩更好了,干脆在曼哈顿租了间宽敞明亮的顶楼公寓,等到第三年,就和同样在投资银行里认识的女朋友订了婚。
当时的A和B谁能想到金融危机会如此轰轰烈烈地到来了,谁又能想到整个投资银行业谁也未能幸免全都进入了没落的开始。少年得志的B因此失了业,早上还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开了个会,午饭之后就得知自己被炒了,办公室里的物品已经安排快递送到他家中,连半点争论的余地都没有。
我遇到A,是在他第二家公司也失败最没落的时候,他请不起翻译,我就用我最业余的水平帮他翻译一些文件,再陪他去内地和那些富商和官员应酬,看着他皱紧眉头硬是把各种稀奇古怪的山珍海味咽下肚。他折腾了两次,虽然结果都是失败,倒也在创业圈子里混出了小小名气,因缘巧合认识了不少人,他年轻,聪明又肯冒险,另外一家公司拉他入伙,也不知怎么就在摩洛哥投标得了一个大项目,帮国王开发油田,每次去实地考察都成为皇宫里的座上宾。他一改当年的落魄模样,每次带给我的礼物也都很贵重。
B是A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历了9个月失魂落魄穷困潦倒的失业期,从富人区搬去贫民区住,却被猎头公司看中,给了他一个香港汇丰银行的职位。他如今在香港东山再起,之前的未婚妻因为距离关系无法维持,他也乐得回复单身,周围不乏娇小可爱的亚洲美女。
我曾经非常有目地问他们两个人,如果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来的话,还会坚持自己之前的选择么?
他们耸耸肩,像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样那样的高潮低谷,都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也总会迎来柳暗花明的那一天。要过怎样的生活,要赋予每一天怎样的意义,这样的话题看起来总是那么空洞。总是头头是道的A想了半天,终于词穷。他最后说,我没做过银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挺好了。
他们两个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一起喝酒,一起爬山,出去旅游的时候拼过房。但我们也常常一言不合争论的不可开交,无论如何引经据典也无法说服对方,与其用文化差异来搪塞,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虽然可以相携闯过一些艰难险阻,但人生里最险峻的那座山头,还是要自己一个一个脚印爬上去。我从来无法想象在他们最低谷的时候会有多么的失落和绝望,正如他们也总对我这个多愁善感文艺青年无可奈何。
语言和文字可以描述事实,却无法令我们感同身受。
曾几何时,我们都喜欢说人以类聚,比如80后就一定都是不靠谱凭一腔热血闯世界的毛头小伙,90后就是照相比V聊天用很多表情符号的黄毛丫头;开宝马车的就一定是官二代富二代含着金汤匙出生天天不劳而有美女泡;文艺青年就是鸵鸟一般躲开世俗和苦难活在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里的小清新。
这就和我们看星座,天蝎座都是野心家,水瓶座都是四次元一样。我们常常给人们分门别类,贴上标签放进橱柜装裱收藏,却忘记了每个人生命中自成一体的苦难和幸福。
最近网上正因为王石的离婚和再婚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所有中年离婚的成功男士都被打上耻辱的标记该放到火刑柱上去烧个干净。
我身边有个极为成功的朋友,哈佛大学毕业,天资过人又勤奋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早就功成名就,他的事务所交给投资银行出身的妻子打理,生意上事无巨细都打点地井井有条,一年收入几百万美金。他们在香港名流集中的中心地段成功置业,又成功把18岁的儿子送去美国名牌大学念书,等儿子到了带女朋友回家的年龄,他们却突然说对婚姻没有激情了。
他第一次在朋友聚会上讲起的时候,周围人都笑笑,哪有结婚二十多年了还激情四射的,谁家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再像干柴烈火时那样买来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再做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
可下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离了婚,事务所照样和前妻一起开,两个人还是生意上的伙伴,连财产分割都不用做。他花大价钱在阿玛尼量身定做了西装,开始重拾之前跳交谊舞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甚至还去健身俱乐部办了张卡和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一起挥汗如雨,他说他要寻找新的爱情和激情,感觉上仿佛回到了什么都没有为了未来努力向前冲的年轻时代。
我最近一次看到他,他身边已经挽了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姑娘,姑娘唇红齿白,笑意盈盈,有一种自发的天真烂漫,像挂在枝头有着金黄色绒毛汁水欲滴的蜜桃。而他站在旁边,敞开的衬衫隐隐有胸肌的线条,丝毫没有露出老态。
我之前对于老少恋一直是有偏见的,年轻美好像花朵一般绽放的酮体躺在皱纹和老人斑边上,对着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姑娘说连鬼都不信的甜言蜜语,想到是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但说到底,我们除了捕风捉影到只言片语之外,谁又能知道一段爱情背后的起承转合呢?轰轰烈烈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也好,不过是在深秋午后的暖阳里剥一瓣橘子看梧桐树的落叶也好,这些,也都是别人的故事。
我是在认识了各种各样三教九流的朋友之后,才明白世界上多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朋友里有在爱情上受过伤害的男人,订好了教堂新娘却逃跑了,于是他就每个星期强迫症一般去派对上找美女第二个星期再换一个。朋友里还有婚后却出轨的女人,因为她的丈夫是家族事业联姻的结果,背景不同,爱好不同,逼得我朋友只好把婚戒藏在口袋里重新寻找真爱。
那些让我们恨让我们爱让我们看了他们的故事要八卦上一天一夜的人,也不过是天冷的时候会咳嗽,星期日的早晨爱睡懒觉,各自藏着掖着难处和痛处的人。
但我真正明白冷暖自知这件事情,还是出了本叫《如果在巴黎,一个旅人》的书之后。
写作这本书是许多许多机缘巧合加在一起的结果。先是有机会去了一直梦想去的巴黎,在那里的6个月,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到操一口别扭的法语7点钟起床去买新鲜长棍面包和咖啡;从在派对上无所适连喝一杯鸡尾酒都会醉倒,到能够和人觥筹交错,说那些市井笑话,喝喝酒,调调情,音乐响起的时候再共舞一曲;从到巴黎的第一天走在阴雨绵绵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觉得不过如此,到之后每一天都能在街头巷尾发现新的惊喜和惊奇——我在画家小巷买了一本绘满抽象图案的日记本,带着它一个人远行,无人说话的夜晚就在青年旅社的木头小桌上奋笔疾书,哪怕楼下音乐声开得震天响也吵不到我。
我先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一些短文,然后被杂志编辑发现了,从偶尔的投稿到最后索性开一个专栏,因为杂志编辑的变动,原本的专栏开了个月就停止了,却又有出版商联系我,问我愿不愿意出一本书。
我10岁开始发表文章,出一本书已经是长久的梦想,我还记得少年时期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选手们许下愿望,说今后有一天一定要一起出书然后并排放在书架上。
但中国的出版业一直不景气,作者又是食物链底层任人宰割的羔羊,慢慢开始,为了糊口,为了生计,也不能再做作家的白日梦,出一本书的愿望,似乎是渐行渐远了。
等我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已经是被困在中环写字楼里,做到昏天黑地拿微薄薪水盼望可以凭一己之力在这个繁华都市生活下去的小白领,而不再是当年背起背包说走就走,天不怕地不怕的疯狂少女。
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放弃已经到手的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我对于人生的憧憬和激情,也在那些熬夜写作,和旧朋友通信聊天斟酌字句,挑选照片的过程中重新回来了。我是那么喜欢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大师级的作品,而是因为它那么真实地记录了我的生命中一段最重要的时光,并且让我通过写作看清了自己和自己将要走的道路。
我没有想到会突然在网上被分享几万次,也没有想到会遇到那么隆重的溢美之词。我看到有人对我说每一次看我的书都感动到涕泪交加,说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舍不得看完又回过头去看几乎能背出里面的字句,又说看我的书将会改变他们的整个人生,我总是在想,我到底有何德何能。
我也没有想到最大的非议反而是来自身边的一些旧同学,有些一起上过课,一起写过作业,一起通宵熬夜之后去考试考完试之后再去喝酒吃火锅唱KTV,有些虽然不算认识,但名字也听了无数遍。
我看到他们说我也不过如此,平凡女子一个,既不是惊才绝艳,又不是美艳无双,既没有个好爸爸,又没有一份月入10万的好工作,何德何能之有,就能出书。我看到他们“言辞确凿”说我大学时代的往事,无非是想证明我不过是行了个大运瞎猫逮到了死耗子,自以为厉害,却不过尔尔。
一时间,倒像是全世界都拿着小板凳和爆米花,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原本是想要证明给别人看,并不是功成名就之后才有出书的资格,想要写书,想要说话,想要分享,想要铭记,所有那些倾诉欲强烈的孩子,并不需要预先登记申请,反复考量。不是完美的生活才值得记录,那些做错的事,爱错的人,阴差阳错的际遇和失之交臂的机会,等岁月转了一个轮回,也会成为我们成长旅途上值得骄傲的谈资。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愈发委屈,恨不得将这些话写在自己的额头上。
可事实上,有些讨厌你的人,其实也并不需要什么合适的逻辑和理由。
我后来收到了一个读者的来信,每天好几封微博私信,我上下班的路上坐在晃荡晃荡的电车的上层,用手机慢慢看。
他也是20岁去了巴黎,在那里求学生活。他说,他看了我的书之后,去我书里面写到的那家咖啡馆,去我书里面提到的酒吧看舞者翩飞的裙裾,他就像我当年一样,看画展,看时装秀,微雨的时候从塞纳河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黄昏的时候拐进一条陌生的老巷子,好像回到了巴黎的黄金年代。
我看到他写巴黎的风景,好像自己设身处地又回到那间敞亮的宿舍里,拉开窗帘看到满地阳光。
他说,他看我的书有共鸣,他说谢谢我的书,让他发现巴黎生活不经意的美。
于是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本来就是毫不相关的。别人看到你的生活情状,有的人爱你,有的人恨你,但他们都无法真正了解你。
你最终还是一个人静静地走完来路,运气好的话,遇到几个旅人,陪你走一段路,说几句话,一别之后各奔前程。
我搬到香港岛西边的老城区去住。电梯里电车上都是踽踽独行的老人,路边是旧式的菜市场,开了三四十年卖鱼蛋粉猪手面的小店,仿佛光阴一下子慢了下来。
我和几个朋友在家里聚会,他们给我带来昂贵的香槟,香格里拉酒店的蛋糕,法国小镇的苹果酒和意大利山区的芝士,帮我庆祝我拿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我的左邻在搓麻将,稀里哗啦的,混杂着潮州方言,锅上炖着洋葱牛肉,洋葱味儿拐弯抹角地传过来。我的右舍在床上缠绵,电视机音量开得很大,却还能听到撞击床头板的声音。
10月底光景,秋高气爽,天蓝得惊人,云朵层层叠叠,知了已经不叫了,阳光却还是暖的。
我想,这就叫做,冷暖自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