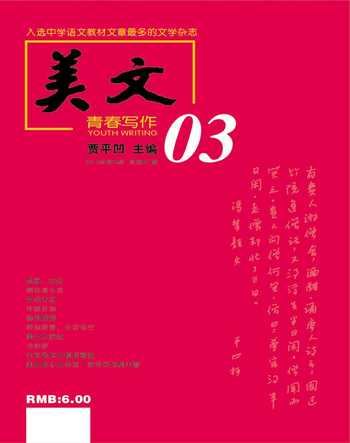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一
半年啦,在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拉脱维亚大学教学,几乎见不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人拼杀,受的可真是洋罪:自己把自己丢了,常事。闯到人家什么禁地,被人家荷枪实弹地请出来,也经历了。更糟糕的是:早晚,总有大汉不明不白地跟着你。你那心能在原来的位置上吗?我的那一半,在我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的全力帮助下,终于拿到了签证,增援来啦。
盛夏,在一片金色阳光里,我从里加城去莫斯科接我的那一半。坐火车去。一个俄族学生送我到车站。在进站口临分别,她倒像我的长辈。她特别嘱咐我,叫我一定加以小心:
“到俄罗斯会很麻烦。别挨罚,别挨偷。别又丢了您自己。”
我说,没关系。心想,我的大山来了。不怕。
现在,他风尘仆仆、伟伟岸岸站立在我眼前。身着一身纯毛的蓝色西服,一条淡蓝色的领带。那是我在家里很少看到的。老爱原来还真是仪表堂堂。
老爱棱角分明的面颊,因为长时间的飞行显得有些憔悴。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直视着我,现在那里都是温情。
“扑上去,抱着老爱,大哭一场,把所有的委屈、辛苦都哭出来”。
那是我朋友给我描绘的和我爱人相见的场面。奇怪,一点也没发生。我静静地站在他面前,不想哭,只觉得悬浮的心“喀啦”一下落进了肚。总是空空落落的感觉也一下没影了,心里涌动着一种特别踏实的幸福。高兴啊!老爱冲我微笑,像接见他的部下一样挥起胳臂和我握手。一股温暖,一股生命的力量立即注入了我的全身。
“怎么样?”
他关切地问我。是啊,一句“怎么样?”那里有多少想问的内容。出了国,他也很快知道了,为什么在国外的亲人总是说,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其实,那抵万金的家书是万万不应给家里带去担忧和无奈。
于是,我笑着说:“大山来啦!哈!更没问题啦。”
我的那一半挺一下胸膛。啊,说明一下,老爱有八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严格的训练下,他的身板永远是直直的。此刻,他有点孩子气地挺挺胸脯,冲我晃一下肩膀,一脸得意地说:
“何止大山呀!我是你的保护神!铁杆保镖!”
保镖站在阳光里,身后的太阳照在他蓝色的西服上,肩上泛着一层特别柔和的蓝光。蓝色是悠然的颜色。
然而,没悠然多久。大叫着做人家铁杆保镖的人,自己都没保了自己。

二
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词典多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
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
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等。
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时间,上午10点多。
莫斯科啊,在我们成长的五六十年代里,那真是人间天堂的代名词。要知道我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苏联的旗帜下成长的。我们看的书是《青年近卫军》《古丽亚的道路》《无脚飞将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最崇拜的英雄是奥列格,是卓亚和舒垃,是保尔·柯察金。我们唱的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列宁山》……我们最向往的是去苏联留学。那是我们的梦,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现在我们真的站在了莫斯科,心里真是有一种特别的激动。我们想看的太多。
先去莫斯科国家科学成就展览馆。出地铁,走在宽广的大街上,看着座座造型新奇的俄式建筑,心里感到无比欢畅。莫斯科的大街比我工作的拉脱维亚里加城宽广多了。又有给我提着包的铁杆保镖在身后,那感觉真是“烟火点在心坎上——心花怒放”。
那天,还因为有莫斯科大学的朋友孙琳相陪,我高兴上加高兴。孙琳是重庆大学来莫大讲学的。异国遇同行,同行加同乡,我们话桑麻,话课堂。我和孙琳在前面说得热火朝天。忽然,听见身后老爱大声呼救:
“何杰!何杰!快!快!”
我忙回身,只见一群女孩正在哄抢我们的保镖。那样子简直就像一个已经长出蒜薹的大蒜瓣:中间一个是我们那位大男人,大保镖。此刻,他举着两只手正站以待抢。他不知所措地喊着我。他的周围包围着一圈女孩儿,她们的手都伸进了那位大男人的口袋里。女孩儿们大多还背着个小孩子。
我赶过去,冲上前,伸手,围着保镖跑了一圈儿,把女孩儿们的手从保镖身上的各处扒开。孙琳也追过来帮我把她们赶走。
大蒜瓣们散开了,远远地站着,驮着她们的小蒜瓣,看着我们,不走。个个滚动着一双乌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一眨巴,一眨巴的。
我看那些女孩撑死有十三四岁,孙琳告诉我,可她们大都是妈妈了。她们专门以乞讨为生。她们就是有名的吉卜赛人,前苏联叫茨冈人。孙琳还说,她们可鬼了,专欺负刚到这儿的中国人。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有钱,又爱带现金。她们先是伸手要,接着就是抢。一蜂窝地抢。
我们那位被抢的保镖此刻一手捂着口袋,一手捂着提包,一脸迷茫地呆呆立在那儿。他完全还没醒过来。我问他你现在捂着口袋,刚才怎么胳膊还举着呢?
她们?这位老实疙瘩“吭吭哧哧”,
“哪敢碰她们。一群小闺女……”他怕人家说他是流氓。我和孙琳都哭笑不得。是啊,在国内,哪见过这阵势。孙琳忙提醒他,看丢了什么?零钱都没了,飞机票也没了。
“啊,护照还在!”
老实疙瘩保镖忽然庆幸地喊。于是我们又一块说:
“便宜!便宜!”
孙琳告诉我们,这些茨冈人只要钱。护照什么的,她们还会趁你不备给你送回来。我们真希望她们把机票给我们送回来。然而当我们找她们,她们像小耗子一样“哗”就窜没影啦。一会儿又回来,躲在树后探头探脑。我远远地看着她们:黑黑的卷发,大大的黑眼睛。她们背的小孩子更可爱:一个个都像小猫一样,毛茸茸的小圆脑袋。
唉,她们还不如掏我呢。我口袋里装着老爱从国内带的鸟结糖。尝尝我们中国的鸟结糖比他们这的酸奶糖好吃多了。多漂亮孩子呀!可是我们一想靠近她们,她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想起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中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斯米拉达。想起70年代上演的《大篷车》。吉卜赛人善良、聪慧、个性豪放。克莱斯勒优美的《吉卜赛人随想曲》好像就响在耳边。说实在的,记忆中的和眼前的都摆在一个画面上,特别看了那些孩子那么小,心里真是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味道。
三
在莫斯科驻俄大使馆,我的一个的朋友告诉了我有关俄国民族的情况。
全世界有约1200万吉卜赛人(茨冈人),前苏联有20多万,实际上可能多一倍(吉卜赛人不愿登记)。
他们大多以占卜、养马、铁、银制品的手工技艺为生。还有是专门行乞的流浪人,包括妇女和孩子。有的仍以部落散居。
前苏联时期为他们建造过居住区。但他们的民族个性桀骜不羁,最后只保留了茨冈剧院“罗曼”。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茨冈人专业剧院。茨冈人本来就能歌善舞,他们的剧目更有一种狂野的民族特色。来莫斯科前,我就希望在那儿能欣赏到纯正的茨冈风情。遗憾没有赶上上演剧目。后来我在拉脱维亚看到了他们的巡回演出。
嚯——那才叫真正的吉卜赛民族的歌;吉卜赛民族的舞。歌,可以叫你觉得天地广阔的无垠。舞,可以让你觉得世界都随他们释放,欢乐。绝不像歌舞团的表演,更不像那什么冒牌的“摇滚”乱摇,乱滚。
到什么地方一定要去欣赏当地土生土长的艺术。民族的才有独特性。
茨冈人不与外族通婚。结婚年龄在12~13岁。难怪围抢我爱人的女孩,那么小就作了妈妈。
茨冈女人有许多规矩:不能和男人一起坐在篝火旁。40岁前不能喝酒。招待客人,不能背向客人。端上食品后,要向后退着走开。妇女的衣裙要长到脚踝(抢我们的女孩也都穿长裙,颜色像新疆人穿的深色花条裙)。如果撩起裙子,哪怕是撩到膝盖,就会被丈夫痛骂。我倒真希望那些丈夫们,见见现在那些走红地毯的影视明星们。那哪是艺术?简直是在比赛——比谁裸的多。
哦,别跑题。但任何一个茨冈妇女,不管生多少孩子,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丈夫,另找别的男人,或过单身的流浪生活。
在拉脱维亚,我就认识一个茨冈孩子和她的妈妈。我的学生也有一个是茨冈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只是很有个性。
那一天,因为遭了茨冈人的抢,我和孙琳你一嘴,我一嘴地说着茨冈人。老爱有点耿耿于怀:
“你说在咱国内见了个外国人,好么,什么外宾呀,这么优待,那么优先。出了国,咱也当一次外宾吧,哈,遭抢。”
其实我们真认便宜,多亏大票缝在了老爱的内衣里。出国时,出国部礼宾司就嘱咐我们:出入俄罗斯,带美金都得报关(限数)。超出部分一经查出全部没收。老爱带来了我们一年半的吃喝费用,还有去欧洲旅游的钱啊。
真不明白,他们这是什么政策?难怪在俄国的外资少。
总之我们是便宜。说着“便宜!便宜!” 我们又玩去了。
四
可刚上路,又遇到一件“便宜”事:
坐出租,我都没看清在哪儿,有人叫停车。车前忽然冲过来几个兵,个个端着冲锋枪。大兵叫我们下车!检查!查黑户。第一次遇到端枪对着你的兵,心里一下集合了一堆小兔子。孙琳告诉我们,俄国都是武装警察,人家可是特别重视罚款。来莫大的几个中国老师,没一个不被罚过的。来莫斯科,从大使馆教育处知道,我们来莫6名留学生在机场被扣了一夜,使馆交了每人80美金才放行。问什么原因?收钱的说:“不知道,就是罚款。上一班交代的。”那时,我对这样的事还体会不深。我第三次到俄国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好好体会了体会(另文交代)。
这回,我的保镖真够意思。他不叫我们动,自己正襟危坐。
打开的车窗探进一个头来。他咕噜了一阵,我们明白了,他要护照,还要我们下车。我们的保镖仍不叫我们动。他把护照拿出,不动,等大兵拿过去。眼睛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自己直着身子,手里没枪,却像端着枪。那架势在重重地说着:
“哼,谁行(hang)唬谁呀!”
说准确点,我那感觉如同在动物园掉在虎狼之圈,我并不怎么害怕,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屈辱感。车外,我数了数,一圈7个兵,个个端着冲锋枪。他们穿着灰色军装,脚下一双半高系带大头皮鞋。顶着贝雷帽,帽子后面飞飞着个小尾巴。有点儿滑稽,可是个个一脸气势汹汹。全然没有加加林那样苏联军人的英俊,更没有电影中苏联红军的亲切。
这是苏联老大哥吗?
大兵一双棕色的眼睛在护照的扉页上滑来滑去。
我忍不住说:“这可真是锯盆锯碗的——(找碴)。”
孙琳说:“他在找美金。”
那兵把护照翻过来,又翻回去,使劲地看看保镖。保镖威威武武。那兵和凑上来的一个同伙又唧咕了好一阵。我不知道是因为那是绿皮公务护照,还夹着写有教授、校长的证明,还是因为我们保镖明显显示的威势,他们终于放行了。也许都有。
拿护照的兵,把护照很不情愿地递进车窗。给了,叫我们走,又在那儿捻手指。孙琳说:“他要感谢费。”
保镖连理他都不理他,说:
“已急(俄语音:走!)”车随之冲上了路。
我当时真不明白,从中国到俄罗斯可以免签。到了俄罗斯却遭这份优待。
俄国司机说话了。他说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我们是他这几天拉的唯一没掏“节涅给”(俄语音:钱)的中国人。他还说,俄国的公务人员索贿厉害。俄国百姓对这样的警察也不喜欢。但他也说,俄国的公务人员工资很低。
回使馆才知道,俄官方腐败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没想到……
保镖这回终于扳回了一局。他挺着腰板,冲着车窗外使劲地“哼”了一声:
“在小丫头面前,我不好动手动脚。拿枪的,别说7个,几百个我都带过。”
没被罚款。保镖又想起被抢的事:
“1比1。平了。”
我们的保镖可找回了面子。于是我们又说:“便宜!便宜!”
说便宜,心里又不知是什么味道。说真的,眼前的事与我儿时的憧憬相距那样遥远。他们要都横眉冷对,我倒佩服。想起那个捻手指的大兵,就有些反胃。保镖忙劝我:
“别!别!别吐。这可是在车上。忘啦?在人家科技馆,还羡慕得“啊啊呀呀”呢。”
保镖总是会找到开心的事。
我们在科技馆参观了加加林乘坐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看了航天飞机……”
是呀,世界真复杂!
这回不是飞出国来了吗?真得好好看看这大千世界!可说来说去,我们又都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青少年时代……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我们曾是多么激动过……
不知谁开的头,我们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总希望那美好永远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那是那个时代我们最爱唱的歌,不过那天,我们做了一点儿即兴的修改:
“长夜快过去,
天色蒙蒙亮,”
(是啊,我想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老爱唱好姑娘,我唱好小伙儿)
但愿从今后,你我快点忘,
莫斯科白天的大——街——上。”
最后我们又反复唱一句:
“但愿从今后,你我都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还是让美好的永存。
一稿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