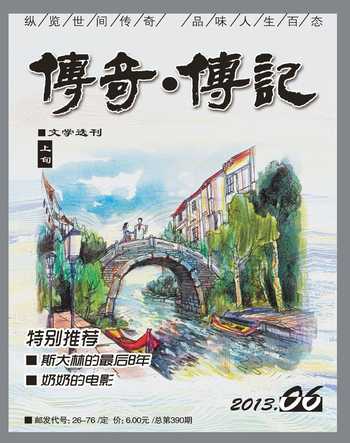谍战的变与不变
张月 高阔
香车美女、华服美景、阴谋诡计、尔虞我诈,是他的人生关键词。他总能挽狂澜于既倒,总能救国家于危难。他的阿斯顿·马丁副驾驶座上总有美女,后座却装着火箭炮。他总有各种神奇的武器,对付敌人的时候甚至不会让西服褶皱。
“邦德,詹姆斯·邦德”,成为一句经典的性感台词。
但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每个特工都能过邦德style的生活。在谍战这条隐蔽的战线上,有人一战成名,也有人囹圄终老;有人成为一国领袖,更多人终身姓名不闻。
谍战的变与不变
间谍,和妓女一样,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说,人最初都处于自然状态,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从而导致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善良与邪恶,无所谓是非曲直,唯有力量与欺诈。
间谍行走于阴谋与诡计之间,游离于忠诚与背叛两极。在国与国的博弈场上,在机构或利益群体的斗争中,间谍作为一枚枚隐形棋子,常常能够出其不意,克敌制胜。
权谋不断,谍战不止。从一战至今,随着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变,谍战的范围、谍战的方式,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军情,谍战最核心章节
2011年5月20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向媒体证实,以色列驻俄使馆武官雷德曼企图窃取俄方机密情报,已被俄方驱逐出境。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雷德曼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一名特工,作为武官被派往以驻俄使馆工作。他和一些俄公职人员交往密切,试图获取有关俄与部分阿拉伯及独联体国家军事合作等方面的情报。5月12日,当雷德曼与一名俄罗斯人进行情报交易时,被守候的俄罗斯特工逮个正着。
从古至今,这种窃取军事情报的戏码,一直是谍战最核心也是最精彩的章节。
一战和二战时期,大国更侧重于侦测军事、外交等直接关乎战争进程或是国家安全的传统情报,谍战主要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
著名的间谍王子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是英国人,毕业于英国剑桥,由于对英国政党的失望而接受苏联情报机关邀请,成为一名苏联特工。
之后他以《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开始为苏联大量搜集情报。1940年,他超群的工作能力引起了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注意,军情部门通过《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向其询问“是否愿意做些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欣然同意,自此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英国军情局。
在军情部门,他不但能窃取到欧洲国家的无线电通讯情报,还能拆看外交邮袋。他以完美的绅士形象蒙蔽了所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苏联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
令人诧异的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半点没耽误,他在英国军情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官员。
1962年,因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身份暴露后,他逃到苏联。为表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了他极高的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商场,特工无处不在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除军事外交情报外,其他领域情报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商业、文化、生态、经济、科技、社会稳定等各方面的信息都是当下情报人员关注的重点。大国之间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一国如果可以在情报工作上取得主动,则会在这场较量中抢占先机。
据统计,名列《财富》全球1000强的大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的商业间谍事件,总损失高达450亿美元。其中,位于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首当其冲。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位列《财富》500强的大公司,几乎每家都有专职的商业间谍人员。像可口可乐、3M、通用电气和英特尔等公司,都派员负责调查竞争对手的策略和动向。据称,IBM公司就有12支情报队伍,他们分工明确,盯住IBM不同的对手。摩托罗拉公司则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挖来专业情报和侦探人员,组建起公司的情报部门。
著名的商业间谍案几乎都发生在巨头之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曾派出商业间谍到通用汽车公司偷取数箱机密文件,2002年被诉后,不得不向对方支付1亿美元的庭外和解费;宝洁公司曾雇用间谍以市场分析员的名义潜入联合利华公司,从后者的“垃圾堆”中获得大量机密。
中国这方面的例子有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间谍门”。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两大巨头,交替领先,一时瑜亮。
双雄争霸,上演了一出出让人叹为观止的“无间道”。最初,双方互相指控对方派人混入客户队伍打探另一方商业情报。后来情报战不断升级,中联重科指控三一重工在2009年成立新洛普咨询公司,非法窃取商业机密。
三一重工则回击称,该公司遭到中联重科无处不在的监听。三一董事长梁稳根就公开表示,他不敢在有手机的地方开会,但凡有重要会议,只能召集高管去一个湖心亭,即便如此,依然无法保证信息安全。
无孔不入的经济间谍活动,正如法国UsineNouvelle(译为“新应用”)网站的一段描述:“在企业生活中的每一天,重要信息都有可能被精明的对手获取。在接待潜在竞争对手时要格外小心,甚至有人会在鞋底贴上不干胶,粘取地板上的碎屑进行分析。专业展会是经济间谍最喜爱的场所,有人会扮成参观者来回拍照,还有人扮成求职者轻松获得重要信息。电话、照片等都可能泄露重要信息……”
潜伏,谍战重要方式
2008年,孙红雷和姚晨主演的《潜伏》红遍了大江南北,孙红雷扮演的中共地下党特工余则成潜伏于国民党军统核心部门,惊心动魄的交锋,诙谐幽默的对白,让观众直呼过瘾。
自有谍战以来,打入敌人阵营,是获得情报最有效的途径。谍报人员所能利用的工具,不外乎经过改装的小型照相机、发报机、密码器等少数特种装备。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全凭特工个人的“业务能力”。
一战最著名的美女间谍玛塔·哈里基本代表了那个时期较为典型的人工情报搜集。
玛塔·哈里是荷兰人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的艺名,是20世纪初知名的交际花,一战期间与欧洲多国军政要人、社会名流都有关联,曾是很多盟军高级军官的情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一直是中立国,作为荷兰公民,玛塔·哈里能够自由地来往于各国之间。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英国军情五处军官的接见,并答应成为法国军队的间谍。
1917年1月,西班牙马德里的德国军队向柏林发送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承载着一个代号H-21的德国间谍所采集到的大量情报。法国情报人员截获了这份情报,并破译了全部内容,很快判定出H-21即是玛塔·哈里。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在这封电报中采用了先前已经被法国破解的编码方式,这给以后的史学家留下了很大的疑问,很多人猜测德国是否有意实行反间计。或许正如玛塔·哈里自己所言,她是在以双重间谍的身份为法国效力,而德国人仅是借刀杀人。
1917年2月13日,玛塔·哈里在其位于巴黎的酒店寓所中被捕。此时,法国在一战中正处于极度被动的地位,士气低落,几十万协约国的将士死于疆场,政府急切地需要寻找一只替罪羊。
玛塔·哈里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她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对数万名士兵的死亡负有责任。1917年10月15日玛塔·哈里被执行枪决,时年41岁。1934年《纽约客》对她被行刑前的场景做了如下描述:“她穿着一身整洁的女士西服,双手戴一副白手套,一切都是专门为这个场合精心准备的。”
时光流逝,潜伏依旧。按照一些媒体的分析,美国在俄罗斯情报与国防等重要部门都安插有大量情报人员,他们时刻观察着周围环境,并偷偷地将有价值的情报备份之后,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回美国总部。
同样,俄罗斯也毫不逊色。早前,美国一高级情报官员也曾明确指出,“近5年来,以外交官身份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人总数已达160人之多,相比于苏联解体时期上升了40%”。
以色列摩萨德更加重视人力资源,招募和培训特工不是靠重赏,而是靠信念、靠国家理想的感召。他们不要那些凭兴趣报名的志愿者,也不欢迎像007那样的冒险家,其麾下聚集的大批犹太精英,都是通过暗中考核、具有非凡经历的人。他们来自80多个国家,使用100多种语言,这使摩萨德拥有任何地区的“当地”特工。绝对的忠诚和对专业技巧的钻研,使摩萨德有着惊人的效率。摩萨德特工的最高准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
高科技,让谍战更超乎想象
2005年2月16日,时任伊朗情报部长阿里·尤尼西说,美国一直在利用无人驾驶侦察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侦察。尤尼西说:“我们民众在伊朗领空看到的大多数闪光物体都是美国用来侦察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的间谍装备……美国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伊朗领空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信息。”
这些无人驾驶侦察机最先被发现的时候,不明真相的当地报纸还曾怀疑是否遇到了“飞碟”。后来,根据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伊朗民众的描述,伊朗军方才确定这些飞行物是无人驾驶侦察机。
美国政府虽然否认派遣无人驾驶飞机对伊朗进行侦察,但3名知晓这一行动的美国官员透露,这些无人驾驶侦察机使用雷达、摄影摄像仪器和空气过滤器获取有关核活动的“蛛丝马迹”,以完成间谍卫星不能完成的侦察任务。
可以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情报工作对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美国等国的情报收集体系,除了出色的特工队伍外,往往综合有间谍卫星的大范围侦测,战略侦察机、无人侦察机和各种微型侦察机的抵近侦察。
2012年6月20日,美国空军在佛罗里达州发射了一颗绝密间谍卫星。卫星代号NROL—38,为美国国家侦察局所有,美方没有公布其任务等信息,甚至没有公开它是否安全抵达轨道。但显然,这颗卫星的目的不单纯。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广泛,网络也日益成为谍战的重要手段。通过黑客手段破坏对方的网络防火墙,潜进目标网络系统窃取重要信息或者植入病毒,已成为大国间进行谍战的惯常手法。
俄罗斯互联网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最近宣布,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间谍软件,这个软件被秘密安装到东欧、中亚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瑞士、比利时、巴西、西班牙、南非、日本和阿联酋)的一些主要军事将领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中。
因为似乎是由讲俄语的程序员设计,所以卡巴斯基将这个间谍软件称为“红色十月”。据透露,“红色十月”互联网行动已经持续了至少5年,一直在谋求获得军事和外交机密。它似乎不是出自某个政府情报机构,而更像是一些隐秘的私人黑客组织的“杰作”。他们攫取军事机密,然后再将其转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买家承诺对获取途径保密。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情报人员的装备也开始更新换代,间谍工具五花八门,趋向于精巧化、微型化、科技化。螺丝钉大小的窃照器、手表式摄像机、钢笔式手枪、香烟式引爆器、藏有致命氰化物的眼镜……花样繁多,无奇不有,令人防不胜防,几乎已经成为谍报人员的“标配”。
2005年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称挫败了英国情报机构在莫斯科实施的一起间谍活动。这起间谍案的奇特之处在于:英国间谍传输情报的方式极其隐蔽,他们使用了一块路边不起眼的石头作为发报机。
这不是普通的石头,高超的伪装下面,实则是一个装有无线电的发报机。俄方调查发现,多名英国间谍很自然地出没于“石头”附近,从“石头”发报机上下载资料。
挑战人们想像力的高科技,让谍战的江湖更加精彩。谍报工作已经告别特工单枪匹马搞情报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比拼综合实力的时代。其中,总有让人叹为观止的比拼案例,也不乏命丧黄泉的落寞故事。这是间谍最好的年代,也何尝不是他们最坏的年代。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环球》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