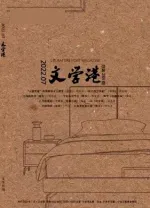赌徒
梵求
我常抱怨母亲对阿梅的溺爱。我抱怨时母亲心里很难受。倒是父亲,说:“这样的人不如死了干净!”母亲说:“你们没有做过女人,不会明白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她二十八岁那年,我还扇过她两个耳光,想起来真为她可怜。”
我与阿梅相差九岁,理应呵护她,但小时候也没少吃我的拳头。有一回,阿梅拿着木梳追赶小妹,然后一只臂膀挽住小妹的头,另只手使劲地耙小妹的头。小妹“哇哇”大哭。我跑过去看,小妹头皮呈一道道白色的齿痕,有几处像要渗血啦。我揍了阿梅一顿。阿梅上小学时,把我藏着的几本邮集翻了出来。我发现时邮票粘在她床边的墙上,还充着我笑:“哥,你觉得怎样?”我望着文革时期的纪念邮票,粘在粗糙不平的水泥墙上,痛苦地咬着牙,我就揍了她一顿。我问她还有几本邮集在哪儿?她说送人了。我说送谁了?她说送同学了。我说哪个同学?她说阿娟。为了挽回我的损失,我到她班上把阿娟找了出来。我希望阿娟把几本邮集还给我。阿娟一头雾水,睁大眼睛问啥样子的邮集,她压根儿没见过。我被骗了,怒不可遏追问阿梅。阿梅斜着眼睛像在回忆它们,但结论是她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只好又揍了她一顿。她被打得有点惨,跑到母亲那儿告状。母亲骂我:“你不爱护妹妹也就罢了,还动不动打她,这邮票值几分钱?!”气得我快要掉泪了,倒是父亲帮我骂阿梅:“败家子!”
我时刻提醒母亲注意,阿梅是个“骗子”,母亲却不以为然。
阿梅初中毕业不想读书了。母亲提前退休让她顶替了工作,希望她诚实,割断与城里不良朋友的联系,尤其是她的同学阿娟。但阿梅朋友多,讲江湖义气,就喜欢跟他们粘在一块。阿梅顶替工作不到两年,因赌博被单位辞退了。阿梅丢了铁饭碗,母亲伤心痛哭,可阿梅说:“打麻将照样过日子。”
但打麻将的日子终究是过不下去的。
阿梅待业在家,身体越长越高,皮肤越长越白。但父亲越看越不顺眼,骂她是寄生虫。她白天睡觉,晚上欺骗母亲说去会朋友,实则是打麻将。我总担心阿梅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钱。她养了一条小狗,闲了就打扮它。天冷给狗穿红背心,天热为狗剪染毛发。一天,她绑住狗,用针在狗的耳朵上扎了两个孔,给狗戴上了两个银色的大耳环。我说:“你这是虐待。”阿梅眯起眼睛斜视着我,说:“你不觉它漂亮吗?”我说:“比你漂亮。”她生气地撅起嘴,继续斜视着我。她细眼,塌鼻,厚嘴唇,这是她要改造自己的理由。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割了双眼皮,过后又隆了高鼻梁。除了她的厚嘴唇没办法削薄,脸上该调整的部位都调整了。阿梅喜欢穿黄色黑点豹纹衣服,还喜欢穿红衣绿裤,或绿裙子。有时绿长裙,有时超短裙。隔了一段时间她爱上了紧身裤,屁股包得像要绽出肉来一样。
父亲见状唉声叹气,说:“你觉得很美是吗?”阿梅笑嘻嘻,打量着自己,转过背对我说:“有代沟。”我说:“爸没有错,是你审美有问题。”阿梅说:“你跟爸一样老古董。”我说:“再漂亮的衣服,不洗也会发臭。”她瞪着眼睛,没话可说了。她换下衣服就扔在卫生间里,母亲看不下去只好洗。母亲病了,阿梅换下的衣服堆积如山。后来堆积的衣服竟奇怪地少了起来。阿梅想换衣服时,发现衣服少了这一件,又缺了那一件。阿梅问母亲,母亲说:“你没看见我这些日子躺在床上吗?”阿梅问父亲,父亲说:“你是说你的脏衣服吗?我把它扔进垃圾筒里啦。”阿梅吼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啊?!”父亲说:“不洗不如扔了干净。”
县城里因赌博逃跑的人多了起来。
一天,阿梅对母亲说:“我要去南方开服装店。”
我对阿梅说:“这可是大事情,你得慎重考虑。”
阿梅说:“哥,我欠了一屁股债。我年轻,想出去拼搏。”我终于明白她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钱了。我看到了她的决心,不再劝她。母亲望着阿梅妖艳的样子很不放心,但也无可奈何。那年,阿梅二十一岁。母亲给了她一笔钱,煮了一袋子茶叶鸡蛋,把她和那只戴大耳环的狗一同送上了南去的列车。
阿梅在南方创业,半夜都会打电话给母亲商量服装店的事情。后来突然又变得母亲打电话给她也不接了。阿梅像失踪了,母亲整夜失眠。后来,让母亲伤心的是母亲不如她的小狗。她的小狗丢了反复打电话给母亲,说她有多想念那只狗,甚至说没有这只狗,她也不想活了这样的话。约过了半年,阿梅告诉母亲,说她不开服装店了。母亲问:“你消费那么大,你靠什么过?”阿梅说:“我承包了商场,我当老板啦。我住公寓房、开小车。我嫌停车麻烦,出去吃饭还打出租车呢。”
母亲心存疑惑,但又鞭长莫及。没过多久,阿梅从南方寄来一包衣服,有母亲的,有父亲的,还有我的和小妹的。看着这一大堆衣服,母亲放心了。我们感到荣耀,阿梅在南方当老板啦。阿梅春节也没回家,说她生意太忙。阿梅给母亲寄来大笔的钱,积存在母亲那儿。母亲看到钱,说,当时决定让阿梅到南方去创业是对的,她总算走上正道啦。母亲的心踏实了。
两年后的一天,阿梅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她的手又抱又提像不够用似的。母亲喜出望外,但见她一脸忧伤,很快发现了她的异样。她给父母亲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个没有父亲的外孙女儿。父亲非要把阿梅赶出家门。阿梅说:“我有能力也不找你们了。她是多余的,我也是多余的,可你们不也把我生了出来?”气得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除了接受,无法拒绝她带来的“礼物”。
父亲送了钱,为外孙女儿报了户口,取名四季。四季长得很可爱,长睫毛,大眼睛,娃娃脸。阿梅除了爱打扮自己,也肯花钱给四季买衣服、买玩具,尤其是四季生日,阿梅总要买一大堆礼物,阿梅的消费惊人,都让我有些害怕。
四季上小学后,有一天,她态度严肃地问阿梅:“我爸爸呢?”阿梅斜着眼望着四季,不知如何回答。阿梅沉思后,说:“他在南方开厂。”
四季说:“你骗人,我没有爸爸!”
阿梅说:“不信我告诉你电话,你打电话过去问好了。”
四季说:“他叫什么名字?”
阿梅说:“他叫盛祖国。”
四季给盛祖国打了电话。盛祖国像知道四季要给他打电话。他满口广东话,四季听不懂。但有一句四季听懂了,他说他是她的爸爸。四季感到温暖,她总算有爸爸了。但四季打电话的次数多了,盛祖国烦了,盛祖国把电话挂了,后来盛祖国干脆不接电话了。四季受到欺骗,泪流满面,终于明白南方根本不存在一个叫盛祖国的爸爸。当她追问阿梅时,阿梅要么痛骂四季,要么斜着眼睛伤心地流泪。四季懂事了,她觉得这是妈妈的痛,四季不再问,但对妈妈的赌博又感到心碎。
有天夜里,阿梅出门时被四季盯上了。阿梅走进一栋声音嘈杂、乱哄哄的小楼不见了。四季没有放弃,等在小楼的过道上。房间里传出响亮的叫牌和洗牌声。隔了很久,阿梅从其中的一个房间出来。阿梅输了钱,看到四季皱着眉头说:“你来干什么?”四季说:“外婆叫你回去!”阿梅火红的眼睛斜视着,训斥四季,回去!但四季缠住阿梅。阿梅眼睛一绿,火苗窜上来,骂道:“当我心揍你!”
“你不是我妈妈!”四季叫道。阿梅像受到刺激,拧住四季的耳朵,拉着耳朵把四季拖到屋外。四季头一甩,耳朵“沙”的一声像挂在了脸上,鲜血顺着她的耳根流了下来。四季拉住阿梅的手咬了一口。阿梅尖叫后,给了四季一耳光。四季捂着耳朵边跑边哭,边哭边叫:“赌鬼,赌鬼!”
半小时后,母亲走进小楼,将阿梅从牌室中叫了出来。阿梅回家后跟母亲吵起来,声音传遍了整个街道。母亲扇了阿梅两个耳光。那年阿梅二十八岁。
我和父亲总担心阿梅的日子。一天,餐桌上父亲又骂阿梅了。阿梅怒气冲冲,说:“我有什么错?都是X县的错,这里的人除了赌博,还能干什么?我输钱都是因为被你们骂,骂晕了脑子。这日子我呆不下去了,我要去南方!”
父亲粗糙的指头捏着细白的牙签,说:“没拦你,你走得越远越好。”母亲却慌了,南方让她害怕。但阿梅在家除了跟她吵架,就是赌博。母亲试探着说:
“好,你走,把四季也带走!”
父亲说:“对对,你把孩子带走!”
阿梅撅起厚厚的嘴唇,说:“带走就带走!”
阿梅真要把四季带走,母亲又改口说:“把她带走,她的一生跟你一样,毁啦!”
父亲听罢老泪纵横:“孩子是无辜的。留下她,你滚!”
阿梅眼眶突然涌出泪水,像一串珠子滚进饭碗里。
阿梅丢下四季走了。
阿梅走后,家安静了下来。母亲怜惜四季,她没爹没娘。母亲开始吃第二遍苦,把四季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送进N大学。
母亲老了,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有精力想阿梅了。她想阿梅,想她有四十几岁的人了。她没有家庭,也没有职业。她没有医保,也没有社保,像一条流浪狗。她的后半生不知怎么过,想必要吃苦头了。母亲有点儿想叫阿梅回家的意思。父亲反对说:“你这是自讨苦吃。”母亲说:“人总会改的,况且她有一把年纪了。”母亲打电话给阿梅,说:“妈老了,你回来吧。可以帮我做点家务,或叫你兄弟找份工作。”
阿梅在电话那头呜咽起来,“嗯嗯”地答应了。她回过几次家,不是父亲拒绝,就是她不想呆下来。
阿梅又回来了。真如母亲说的她变了,变得稳定成熟,不再个性张扬。我帮阿梅介绍了一份工作。凭阿梅的学历和年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她做了几个月,没再做下去。她说她要推销安利产品,钱赚得更多。她还介绍朋友到小妹的世通汽车销售公司购买分期付款的汽车。阿梅说:“妹妹,我帮你介绍客户,价钱用不着优惠。”见小妹疑惑的样子,阿梅说:“妹妹,你放心,他们老板都很大,一次性付款有困难,到期他们一定会付清的。”一笔笔生意就这样促成了,这让小妹和母亲很高兴。
阿梅变了。她在家里帮着母亲洗衣做饭。她推销安利产品没日没夜。她将赚来的钱交给母亲,要用时又从母亲那儿取。母亲成了阿梅的银行。母亲说:“阿梅,钱够用就差不多啦。”我和小妹望着日益憔悴的阿梅,也劝她:“阿梅,身体要紧,钱可以慢慢赚的。”阿梅苦笑着说:“没钱怎么活啊。”想想也对,阿梅出手大方,花钱如流水,没钱怎么撑得下去呢。她给父亲买补品,给母亲买昂贵的玉镯。阿梅拿着玉镯对着阳光照,它晶莹剔透,绿色翡翠纹路清晰,她把玉镯套进母亲满是皱褶的手腕上。母亲对我和小妹说:“你们看看,她多孝顺,你们俩还常常对她说三道四。”我和小妹在阿梅面前都感到汗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不清楚阿梅变化为什么那么大。
一天,阿梅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给母亲打电话,说她在推销安利产品时从楼梯上摔下来,跌断了腰椎骨,必须做手术,否则下半身就要瘫痪了。母亲气喘吁吁赶到医院,望着阿梅尖叫起来。阿梅这一跤跌得太残忍了。她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她不能大小便,插着导尿管。她的厚嘴唇破了,变得更厚,像翻出来的肠子。她隆起的鼻梁又被撞进去了,而且歪了。她的脸有点惨不忍睹。母亲安慰她,说:“不要紧,慢慢会好的。”
阿梅做腰椎手术,花去她推销安利产品赚来的钱,还要母亲掏钱。
要不是后来阿娟,我们根本不会怀疑阿梅是推销安利产品从楼梯上摔下来跌断腰椎的。阿娟向我们讨债时,说阿梅是在水库边上聚众赌博被警察追赶从山崖上滚下来跌断腰椎的。我们当时还不敢相信。母亲说:“阿娟,你不要血口喷人,不要诬陷阿梅!”但当我们责问阿梅,看到她斜视的眼睛一片白茫茫的样子,我们都清楚了。我们个个都气得目瞪口呆,彻底崩溃了。
阿梅从医院出来,在家康复了一段时间,她的事情就暴露了出来。
小妹对阿梅介绍的几个朋友催讨车款,他们拿出了阿梅出具的代收世通汽车销售公司车款的收条。他们说:“钱早已付给你姐姐啦。”小妹哭泣着找阿梅算账。阿梅红着脸说:“妹妹,我也是被逼无奈,有钱了我会还你的。”小妹说:“钱都被你赌了,你拿什么还,我怎么向老公交代,你要把我们的家庭拆散了!”
父亲骂阿梅:“像你这样的人死上一百次也不够!”
隔了几天,一帮赌徒上门来了。他们将母亲家团团围住,要绑架阿梅。母亲问阿梅到底欠了多少钱?阿梅说:“也就他们一百万吧。”这已吓倒了母亲。隔了两天,又有一帮人上门来,催讨八十万元的债,母亲瞪着阿梅问:“你说不是没有了吗?”阿梅斜着潮红的眼睛,振振有词地答道:“真的没有啦!”可过了两天,遥远的债主听到风声也找上门来了。他们说,阿梅进服装时急需用钱,暂时借一借,共一百十万,一年多了还没有还。阿梅斜着眼睛望着母亲,发誓再也没有了。但谁还会相信呢,她永远没有真话。
母亲对阿梅说:“你还是走吧。”
阿梅走后,赌徒和债主们逼父母亲替阿梅还债。讨债的人三五成群,今天一伙,明天一帮,像身上的泡疹冒得浑身都是,不可收拾。母亲一算阿梅举债总额终于晕倒在地。赌徒们开始停电停水,缠住父母亲不放。父母亲商量不卖掉房子也住不下去了。他们压根儿不会想到,七八十岁的年纪还要回老家山村住破房子。
接着,赌徒们找到了我。到我家,到我单位。一天,他们把我围住,说:“阿梅向我们借钱时说,钱是到你这里来投资的,她跑了,你得替她把钱还给我们。”我不想跟他们争辩,可他们还是动起手来,把我的眼镜打碎,鼻子打歪了。他们离开时威胁说:“要么把阿梅找出来,要么把钱还给我们,否则你什么时候缺一只胳膊,断一条腿都难说。”
阿梅把我们都卷了进去。一帮人到N大学去找四季,吓得四季害怕上学了。母亲知道我被揍和有人找四季,在寒冷的山村中病倒了,不得不住进县人民医院。
那天,风雪弥漫,阿梅身穿黄色黑点豹纹皮衣,围着黑围巾,拎着LV包,手和脸冻得紫僵,人消瘦得不成样子。她突然出现在病房中,母亲哭了。母亲说:
“你哥,你妹被你害惨了。”
“妈,我……”
“还有四季,她……”母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阿梅听说他们在找四季麻烦,斜视着眼睛,脸部出现了痉挛。她愣了一会儿,然后抱住母亲呜咽起来。母亲不让阿梅久留,催促她快离开。
阿梅走了。我送阿梅到医院门口。阿梅有些依恋不舍。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塞进她的包里。阿梅斜视着我,说:“哥,事实我没欠那么多钱,我的钱帮了朋友……”我没听她说话,反而问她:“你得为四季的安全考虑,她总不能躲起来不读书吧?”阿梅垂下头去,像永远抬不起来一样。她抬起头时,满眶都是泪水。突然,她跪在我的面前,说:“哥,我想不出办法,求你帮帮四季。”我望着阿梅,真想像小时候一样揍她一顿,但她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一把拉起阿梅,骂她:“都是你害了她。你为什么不敢做敢为。你对女儿承担过责任吗?!”
阿梅泪水落进了雪地里。她伤心地别过头去,跑了。我想拉住她,但她像只受伤的豹子在风雪中飘去。我望着她,心一酸,泪水模糊了视钱。但对阿梅的记忆反倒清晰了起来。阿梅得不到四季的爱,有一段时间四季干脆不叫她妈妈了。四季把命运的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阿梅想见四季,四季却把她拒之门外。四季考上N大学那一年,四季过二十岁的生日。外婆告诉她,她妈妈想来,四季说:“谁让她来了?!”生日蛋糕上的烛光在灭了灯的房间里闪烁,我还是看出了四季藏起来的痛苦。她眼睛潮红,她的内心在等一个人,但她的内心又恨这个人。四季含着泪花吹灭了蜡烛。外婆叫她许一个愿,她也不许愿。晚餐快结束时,阿梅带着礼物走了进来。阿梅坐下,四季愤怒地瞥了她一眼,然后站起来要走。我按住了四季,四季坐了下来。阿梅红着脸,拿起酒杯伸向四季:“宝贝,妈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考上N大学。”四季像野兔失控,眼睛血红。我担心她发作。果然,四季站起来,一把打翻阿梅的酒杯。杯子的碎裂声和四季的吼声交织在一起:“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批评四季:“不能这样对你妈妈!”四季愤怒了,扭头冲出房间。我转向发呆的阿梅,说:“快去追回来。”阿梅跑了出去。房间里我们都没话说,静得出奇,等阿梅和四季回来。没隔多久,窗外传来阿梅和四季的吵架声。母亲说:“母女俩又较劲了,你快去看看。”我跑出门外,四季蹲在地上,耸着肩膀哭泣。阿梅被四季气跑了,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望着阿梅在街角拐弯处消失的背影,真为她可怜。现在,我站在医院门口,望着阿梅的身影,可怜她,又恨她不顾四季一走了之。
阿梅离开医院后的一天晚上,四季从教室走回宿舍。路上灯光昏暗,四季很害怕,因为赌徒们随时可能来找她。果然,她听到身背后有“啪哒啪哒”的声音。这声音迅速接近了她。她意识到有人要绑架她了。但她回头看时什么也没有。四季打着寒噤,没想到绑架的人不在她身后,而在她前面。他们从一辆小车上跳下来,两男两女。四季虽有准备,但准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围住了她。四季认出其中的一个女人叫阿娟。他们迅速控制住四季,把四季塞进一辆小车内。他们对四季说:“不用害怕,只想找你聊聊。”他们把四季带到学校附近一家设施陈旧的破旅馆。旅馆没有电梯,铝合金窗像一推就倒。四季被押在五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们用四季的手机给阿梅打电话,叫阿梅赶快显身,不显身就对她女儿下手了。阿梅没有耽搁,显身了。四季回忆说,妈妈就像伺机在她身边一样,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四季看到妈妈身穿黄色黑点豹纹皮衣,肩上还有雪花。阿梅一进门四季像憋了很久的哭泣一下子“哇”放了出来。阿梅嘴唇发抖,说话时嘴唇上全是白沫。她失控地吼道:
“你们敢威胁我的女儿?!”
“他娘的,你还有理?!”男人凶巴巴地说。
“阿娟,你放了我女儿,我跟你走。”阿梅克制了自己。
“你东避西藏,谁还信你。”阿娟说。
阿梅情绪又上来了。她额头上、脖子上的青筋像小青蛇一样绽了出来。她咬了咬厚嘴唇,走近阿娟。她的脸像突然失血,苍白如尸体。她举起一只手指头,那只手指头像失去控制,在风中抖动。她的另只手从袋里摸出一把雪亮的小刀。阿娟吓得退了两步。阿梅用小刀像削橡皮一样一刀削掉自己举着的指头。鲜血顺着她的指头流了下来,流在她的手腕和袖口中。四季抖着身子,闭上了眼睛。四季睁开眼睛,看到妈妈在报纸上用血手指写“保证”两字。
他们看得发呆了。他们放了四季。
阿梅嘱咐四季:“安心读书,有事找舅舅。”
四季走了出来。走到三楼,四季听到楼上有辱骂声,后来是厮打和尖叫声。四季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下楼来。四季刚到旅馆门口,准备给我打电话,突然听到头顶上方有玻璃窗的破裂声。玻璃碎末飞向了她。她的眼睛被左侧一个巨大的黑影遮盖了一下。四季眨了一下眼睛,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一股气浪从左侧扑过来。四季的心立刻收紧了,她看见了妈妈。在幽暗的灯光下,她躺在水泥地上,脑壳碎了,还有白糊糊的脑浆……四季吓得魂飞魄散,呼地逃开了……然后,又呼地返回,扑到阿梅身上。
责任编辑 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