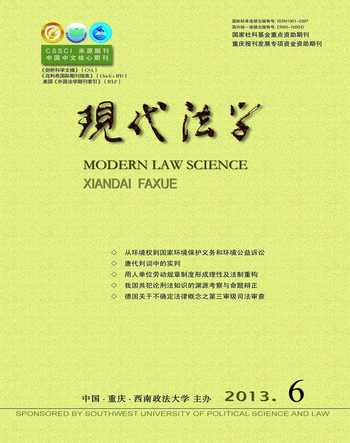汉代简牍文献刑事证据材料考析
张琮军



摘 要:通过研究汉代简牍文献发现,汉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已趋向规范化、制度化,在司法活动中表现为重事实与证据,初步创立了客观主义的刑事证据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包括据证起诉制度、庭审质证制度、据证决断制度以及俱证乞鞫与验证复狱制度等。汉代刑事证据制度的确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传统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价值。
关键词:汉简;刑事证据;据证定罪;俱证乞鞫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6.04
经过对《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及《居延新简》等简牍文献的细致研究,不难发现,汉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客观性倾向,其司法审判强调据证断罪、依律量刑。《奏谳书》中记载的诸多汉代案例,都能够对此进行印证。司法官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注重各项证据的收集、检验,并将之相互印证。以求案件事实清楚、明白,最后依据相应的律条作出判决。证据居于主导地位,它的运用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从而为诉讼审判活动提供了重要保障。笔者总结出证据运用于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即起诉是依据证据提起控诉的过程;官府的庭审活动是鉴别证据,由原被告双方进行质证的过程;审案官吏的判决是据证定案的过程;乞鞫是司法机关验证复审,平复冤狱的过程。
一、起诉证据材料的研究
汉代提起诉讼,主要有自诉、告发、举劾三种方式。其中,前两者统称为告劾。提起诉讼是“据证起诉”的过程,也是刑事证据形成与运用的首要环节,经由此开始收集各类证据,对案件事实予以调查和认定。
以下分别对汉代刑事案件的四种起诉方式加以论述,并作总结概括:
(一)自诉与证据
汉代的自诉既可以书面形式提起,又可以口头形式提起。
1.自言
以口头形式提起的自诉在简牍资料中称为“自言”。汉简中关于“自言”的记载数量也比较多,以《居延汉简》为例:
字初卿,在部中者,敢言之,尉史临,白故第五燧卒司马谊自言,除沙殄北,未得去年九月家属食,谊言部以移籍廪,令史田忠不肯与谊食……(居延汉简89·1—2)陈兵指出,我国古代特别重视口供的作用,持“断罪必取输服供词”与“无供不录案”的断罪原则,所以将口供称为“证据之王”,直至清朝仍是如此。(参见:陈兵.解读现代“刑讯逼供”现象的根本原因——从我国古代拷讯制度合法化层面人手[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4).)刘显鹏也指明,中国传统诉讼的特殊之处在于极为重视被告人口供的“口供主义”,在中国传统的诉讼当中,被告人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供认,一般不能定罪。其他证据的证明力都比不上口供高,人证、物证、书证只是辅助证据,而且必须在具有口供的情况下方能发挥作用,如无口供,仅凭其他证据不能定案。相反,如果有口供,即使没有其他证据,也可定案。(参见:刘显鹏.中国古代口供制度粗探[J].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2004,(3).)
即尉史临说:“第五烽燧的卒司马谊自行投诉,其除沙于殄北,去年九月没有获得应配送给家属的粮食,他将领取粮食的凭证交与配送部门,而令史不肯向其配送粮食……
□此处“□”为原间残缺,间文不可释。下同。
寿自言,候长宪伤燧长忠,忠自伤,宪不伤忠,言府一事一封。(居延汉简143·27,143·32,143·33)
寿自行投诉说,候长宪伤害燧长忠,(查悉)忠系自伤,并非被宪所伤……
以自言的方式提起诉讼,形式简单、操作便利,因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尤其适合于不识文墨的广大乡民就简易的刑事案件向官府自行投诉。
2.书告
书告,是指控告者以书面形式向地方或中央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这种形式一般用于各种重大案件的诉讼与直诉。因上书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可分为普通上书与越诉。
普通上书是指案件受害方以书面材料提出诉讼,此类诉讼主要由当地司法机关受理。《奏谳书》中记载了多则书告案例,试例如下: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戌,“三月己巳大夫祿辞曰:六年二月中买婢媚士五点所,价钱万六千,迺三月丁巳亡。”(简8—9)[2]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八月初三日,“三月己巳日,大夫椽状辞:六年二月中,在士伍点住处买婢女媚,身价一万六千钱。三月丁巳日逃跑了。”
十二月壬申大夫詣女子符,告亡。(简28)
(汉高祖十年)十二月壬申日,大夫送来一位名叫符的女子,告她逃亡。
(二)告发与证据
即当事人以外的同居、同伍、同里的普通百姓知悉犯罪后进行控告或揭发的行为。汉代的告发是由秦代继承而来,是由行为人主动地或者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而引发的。《居延新简》中记载了一则告发案例:
内郡荡阴邑焦里田亥告曰:所与同郡县□□□□死亭东内中,……(居延新简E·P·T58·46)[3]
即名为田亥的人报告说,同郡县的人死于亭东内中东首。
汉代为了纠举犯罪,对于告发属实者,法律规定给予奖励,如《二年律令·捕律》记载:
诇告罪人,吏捕得之,半购诇者。(简139)
即给予告发者一半的奖励,如同秦一样,应该是黄金一两。同时,汉律也明确作出规定,诸同居、同伍、同里及职务相关(包括相邻商贩)者均负有相互监督、举报罪行的义务。如《二年律令·盗律》规定:
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简68—69)
这是关于同居者相告的法律规定。劫人、谋劫人案的亲属如不及时告发将以连坐论处,只有告发才能免除其连坐的罪责。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了汉律关于同伍者相互伺察,有罪相告的规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这项义务在《二年律令·户律》中有具体的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不从律,罚金二两。(简305—306)《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爵级共分为二十等级,五大夫为第九爵,属于大夫之列。《周礼·地官·司徒》曰:“五家为邻,四邻为里。”
即凡是爵位在五大夫以下者,相邻五家为一联保单位,相互监督,发现为盗贼及逃亡者,立即报官,违背者受处罚。《二年律令·钱律》中也规定了同居、同伍者有罪相互告发的法律义务: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
四两。(简201)
如果同居者对“盗铸钱”罪行不告发的,以“赎耐”论处。正典、田典、伍人不告发的,罚金四两。
不仅同居与同伍者有相互告发罪行的法律义务,而且,因店铺相连的商贩之间,也有相互监督告发罪行的义务。《二年律令·市律》中规定:
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简260)
即商贩藏匿商物而不据实纳税的,对其本身进行处罚之外,与之同列的列长、同伍者也要受到处罚。
由上可见,汉代统治者为了打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继承了秦代的做法,在法律上作出了较为周密的规定。不仅鼓励告发犯罪行为,而且设置了诸多主体之间的举告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护和抑制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
(三)举劾“劾”的字义,旧律尽管皆围绕治罪立义,但具体解释却颇有不同。《说文·力部》云:“劾,法有罪也。”段注云:“法者,谓以法施之。《广韵》曰:‘推穷罪人也。”《急就篇》“诸罚诈伪劾罪人”,颜师古注曰:“劾,举案之也,有罪则举案。”《尚书正义·吕刑》云:“汉世问罪谓之鞫,断狱谓之劾。”相较而言,四种释义以颜师古注为允当,颜注也是前有所承。《文选·通幽赋》“妣聆呱而劾石兮”,注引项岱云:“举罪曰劾”。 与证据
上述两种诉讼的提起方式均可称为告,是“下告上”诉讼行为的总称,而劾是“上告下”诉讼行为的总称,诚如沈家本所云:“告、劾是二事,告属下,劾属上。”[4]汉代继承了秦代的举劾制度,即各级司法官吏代表官府举告犯罪行为。汉代在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劾奏是必备程序,否则将视为违法,并追究相关者的法律责任。根据被举劾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对普通人犯罪的举劾和对官吏犯罪的举劾两种。
1.对普通人犯罪的举劾
汉代负责纠察罪犯的基层组织机构称为“亭”,“求盗”是亭中专门负责捕“盗”的官吏。《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语:“求盗者,亭卒。”这是由秦代承继而来的。
《奏谳书》中记载了有关基层官吏举劾普通人犯罪的案例,如:
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毋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简1—2)
六月戊子日,发弩卒九解送到男子毋忧,告发该犯接到都尉征发屯卒的文书后逃跑,不去指定地点报到。
如果官吏未能积极行使其应尽的举劾职责,将受到处罚,轻为失职,重则坐罪。即使对于犯罪行为不知情,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二年律令》中有关于官吏失职的法律惩处规定:
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令、丞、尉能先觉智(知),求捕其盗贼,及自劾,论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罚。一岁中盗贼发而令、丞、尉所(?)不觉智(知)三发以上,皆为不胜任,免之。(简144—145)
意为发生贼盗案件,士吏、求盗所管辖的地区及令、丞、尉未发觉,士吏、求盗以卒身份戍守边防两年,令、丞、尉各处罚金四两。如果令、丞及尉能够事先觉察将其捕获或者径行举劾,由直接负责的官吏承担责任,对令、丞及尉不予处罚。如果一年中发生三次以上未发觉贼盗犯罪的行为,令、丞及尉均免职。
这条律文在史籍中多印证,如《汉书·酷吏传》载:“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即发生众盗贼作乱的案件未能觉察,或者虽觉察而未捕满一定人数盗贼的,郡守官以下直至小吏主管人一律处死。
2.对官吏犯罪的举劾
秦汉时期,已形成了一套对官吏较为严密的监察制度。监察发现官吏的犯罪行为,进行举劾,启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汉代出土简牍法律文献中记载了大量举劾官吏的案例,如《奏谳书》中的案例三是江陵丞等人对临菑(淄)狱史阑的劾;案例十四是安陆丞忠对狱史平舍匿无明数大男子种的劾。这些案例均是县级专管司法的丞对县级一般官吏的举劾。《合校》中记载了一桩关于两名戍卒相互斗伤的案件,因双方皆致伤,故对两人分别进行举劾,并行拘捕。两份劾文如下:
戍卒东郡畔戍里靳龜,坐乃四月中不审日,行道到屋蘭界中与戍卒函何
阳争言,斗,以剑击伤右手指二所。地节三年八月已酉械击。(简13·6)
戍卒东郡□里,函何阳,坐斗以剑击伤戍卒同郡县戍里靳龜,右脾一所,地节三年八月辛卯械击。(合校简118·18)
即东郡畔戍里靳龜的两名戍卒相互械击,两人皆致伤,一位伤右手指,一位伤右脾。
在汉代,举劾官吏犯罪要求有书面的劾状。《居延新简》中的“不侵守候长业劾亭长等盗官兵逃亡”的劾状较为典型,原文如下:
建武六年三月庚子朔甲辰,不侵守候长业敢言之:谨移劾状一编,敢言之。
迺今月三日壬寅,居延长安亭长王闳、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常及客民
赵闳、笵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盗官兵,臧千钱以上,带大刀、剑及铍各一,
又持锥、小尺白刀、箴各一,蘭越甲渠当曲隧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案:常
等持禁物蘭越塞,于边关傲逐捕未得,它案验未竟。蘭越塞天田出入□状辞曰:公乘居延中宿里,年五十一岁,姓陈氏,今年正月中府补业守
候长,署不侵部,主领吏迹候备虏盗贼为职。迺今月三日壬寅,居延常安亭
长王闳、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常及客民赵闳、笵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盗官
兵,臧千钱以上,带大刀、剑及铍各一,又各持锥、小尺白刀、箴各一,蘭
越甲渠当曲隧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案:常等持禁物蘭越塞,于边关傲逐捕
未得,它案验未竟,以此知而劾无长吏使,劾者状具此。
三月己酉甲渠守候 移居延写移如律令。掾谭、令史嘉。(新简E·P·T68:54-76)居延,汉代县名,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常安、攻虏均为居延县所属亭名。不侵部,甲渠候官属部。
这篇递送劾状的文书,简文较为完整。劾状通常是逐级上报的,本案公诉人不侵守候长陈业将劾状报送甲渠候官,然后由候官转呈有关部门。劾状主要由呈文、劾文及状辞三部分合成。第一段为呈文,清楚地说明了起诉时间、起诉人、文件名称及数量;第二段为“劾文”,说明被告的犯罪事实及对其调查情况;第三段为“状辞”,包括原告身份的说明、被告的犯罪事实及调查情况;最后一段为上级机构甲渠候的转呈文。
在《汉书》中也记载了多则举劾官吏的案件,如《盖宽饶传》载:“(盖宽饶)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回避,小大辄举,所劾奏众多。”这是负有监察职责的司隶校尉举劾官吏的记载。
如果官吏“劾人不审”以及“轻罪重劾”则要承担“失”罪与“不直”罪的后果。《二年律令·具律》载:
劾人不审为失,其轻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为不直。(简112)
意为官府举劾嫌犯不当是过失行为,将轻罪故意举告成重罪为不直。
经过论证可知,举劾是官府对刑事案件主动进行纠举,类似于今天的公诉。汉律对于举劾制度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规制了明确的执行主体、具体的运行程序及严格的劾状形式。
通过对汉代诉讼提起方式的分析与论证,可以得出结论:同秦代一样,汉代刑事诉讼的提起是“据证起诉”的过程。告劾是启动诉讼必不可少的程序,通过告劾形成劾状,当中涵盖了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所要求的基本证据。以自诉、自首及告发三种方式提起的刑事诉讼,至少具备了供辞证据。如前所述,供辞证据包括被告的口供、原告的陈述及案外人的证人证言。而且,由以上所提供的材料可知,多数情况下起诉人还会同时提供一定的物证。举劾则更是一种据证起诉的方式,因为官吏之所以会举劾,要么是发现了杀伤、贼盗等犯罪事实,要么是接到了发生犯罪的举报。
可见,提起诉讼是整个刑事诉讼审判环节证据运用的首要步骤,也是获取刑事证据的最初环节。正因为如此,汉律中对刑事诉讼的提起作了严密的法律规制。强调了告劾的重要性,没有告劾而系人,则被视为违法,要受到法律制裁。西汉“治淮南王狱”,列举其罪行时,便有“擅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以上十四人。” [5]的记述。《二年律令·具律》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治狱者,各以其告劾治之。敢放讯杜雅,求其它罪,及人毋告劾而擅覆治之,皆以鞫狱故不直论。(简113)
司法官吏应根据告劾内容审断案件。如敢制造障碍不法审讯,审断告劾以外的罪或者无告劾而擅自审断的,均以故意不如实断案论罪。
[HS(3] [HTH]二、审判证据材料的研究
[HTSS][HS)]
审判程序首先要进行质证,包括听取被害人的陈述、讯诘被告及询问证人。通过这些环节收集和审查刑事证据,以便确定案件事实。对审讯过程中原告、被告和证人的言辞及其他证据的收集、审查情况,要制做详细的书面记录,称为“爰书”。这是法官最后进行量刑与断决的依据。《史记·酷吏列传》中便有“传爰书”的记载:“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史记·酷吏列传》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爰,易也。”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爰,换也。古者重刑,嫌有爱恶,故移换狱书,使他官考实之,故曰‘传爰书也。”《汉书·张汤传》引师古注:“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籾山明也提出,“毋庸赘言,这些文书是为了给县官做判决提供依据。因为这些文书就是爰书,所以才称其为‘传爰书”。(参见:籾山明.爰书新探——兼论汉代诉讼[G]//简帛研究译丛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178.) 以下详细论述刑事证据在整个案件鞫断环节中的具体运用。
(一)庭审中的质证
汉代承袭秦代的质证制度,将原告的陈述、证人证言与被告的口供进行质对,以便澄清案件事实。在审讯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或其代理人必须到庭接受法官的讯问,进行质对。同时,由于证人提供的证言是重要的证据,对澄清案件事实意义重大。因此,证人也必须出庭作证,并参与质对。《奏谳书》中的第二则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庭审质证的情形:
大夫祿辞曰:六年二月中买婢媚士五点所,价钱万六千,迺三月丁巳亡,求得媚,媚曰:不当为婢。
媚曰:故点婢,楚时去亡,降为汉,不书名数,点得媚,占数复婢媚,卖祿所,自当不当复受婢,即去亡,它如祿。
点曰:媚故点婢,楚时亡,六年二月中得媚,媚未有名数,即占数,卖祿所,它如祿、媚。
诘媚:媚故点婢,虽楚时去亡,降为汉,不书名数,点得,占数媚,媚复为婢,卖媚当也。去亡,何解?.
媚曰:楚时亡,点乃以为汉,复婢,卖媚,自当不当复为婢,即去亡,无它解。(简8—12)
这是原告禄、被告媚及证人点三者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质证的情形。禄控诉说,自己以万六千钱从点处买得媚,三月丁巳日逃跑了,抓获她后,她说:自己不应当是奴婢;媚辩解道,她以前是点的婢女,楚时期就逃脱了。到了汉朝,没有上户籍。点逮住她后,仍将她作为奴婢,报了户口,卖给祿。她认为自己不应该还是奴婢,就逃跑了。其他情况,和祿所说的相同;证人点提供证言,媚以前是他的婢女,楚时期逃跑了。六年二月中找到她,她没有户口,给她报了户口,卖给了祿。其他情节,和祿、媚所说相同;法官诘问媚,你以前是点的奴婢。虽然楚时逃跑了,可是到汉朝后,并没有申报户籍。点逮住你后,仍将你作为奴婢报了户口,将你卖与他人,符合法律。逃跑掉了,怎么解释?媚回答道,楚时候她已经逃跑,点认为到了汉朝后她仍是他的奴婢,卖了。她认为自己不应当还是奴婢,就逃跑了。没有其他要辩解的。
这则案例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汉代庭审过程中的质证情形,首先是原告的控诉,其次是被告对原告控诉的回应,接着证人提供证言。然后法官进行讯问,当事人都必须如实回答。《奏谳书》的第四则案例也对法庭的质证过程进行了详细地记录:
大夫所诣女子符,告亡。
符曰:诚亡,诈自以为未有名数,以令自占书名数,为大夫明隶,明嫁符隐官解妻,弗告亡,它如所。
解曰:符有名数明所,解以为无恢人也,娶以为妻,不知前亡,乃疑为明隶,它如符。
诘解:符虽有名数明所,而实亡人也。律: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弗知,非有减也。解虽弗知,当以娶亡人为妻论。何解?
解曰:罪,无解。(简28—31)
即大夫控告女子符逃亡;女子符辩称,她是逃跑,并谎称自己户籍,依照法令的规定去报了户口,成为大夫明的奴隶。被嫁给隐官解为妻,但没有告诉他自己逃跑的事。其他情况和控告的相同;解说,符在明家有户口。他认为符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知她从前曾逃跑过,以为她是明的奴婢,其他情节与符所说相同;法官诘问解,虽然符在明家有户籍,而实际上是一个逃亡的人。法律规定:“娶亡人为妻,黥以为城旦,弗知,非有减也”。你虽然不知道,仍应该按照娶逃亡者为妻论处。你有什么可以辩解的?解答道,自己认罪,没有要辩解的了。
通过展示案例可知,普通身份的原、被告双方在质证过程中进行控诉与供述,证人提供证言,法官随之反复讯问,直至澄清案件事实为止。如果原、被告对法官的讯问不如实回答,或者所答与法官了解到的案情不符,法官则可以用刑逼取。
汉代的质证程序已趋于规范化。汉律对原、被告及证人的质证行为作出了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如实举证,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前文已叙述了《二年律令·具律》中关于“证不言情”的法律规定,此外,汉代法律中还有一条未署律名的规定:
证财物故不以实,臧(赃)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情)者,以辞所出入罪入罪。
意为在陈述案件事实时故意不如实提供财物数目,案件赃值达到五百钱以上者,如果供述后满三日不更正并说出实情,则以其供述所出入之罪反及其身。这是汉代的一项审讯制度,按其性质应当属于汉代《囚》律。在汉简中,凡记录审问案件的简牍几乎都有这条法律规定。现将所掌握简牍中的这类律文抄录一部分如下:
《居延新简》:
“□辞已定,满三日□。”(E·P·T5:111)
“□故不以实,臧(赃)五百十以上令辨告。”(E·P·T51:290)
“贾而买卖而不言证财物故不以实臧(赃)二五百□。”(E·P·T54:9)
“□三日而不更言请(情)书律辨告。乃验问……”(E·P·T51:228)
“□市券一。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E·P·T51:509)
“□先以证财物不以实律辩……”(E·P·T53:181)
“而不更言请(情)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恭辞曰上造居延临仁里年二十八岁……”(E·P·F22:330)
“□□案,不□更言,以辞所出内(纳)罪人。”(E·P·W13)
“建武四年三月壬午朔丁酉,万岁候长宪□□燧·谨召诣治所。先以证县官城楼守衙□而不更言请(情),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E·P·F22:328)以上所录简文,有的是该律文的节录,如“证财物故不以实”;有的是该律文的残篇,如“□辞已定,满三日□。”
以上简文中的“赃五百以上”、“赃二百五十以上”、“县官城楼守衙”等语,不是这条律文的组成部分,而是审判官问案时,根据审问案情的需要引用的有关令文[6]。
经由上述论证可知,质证是整个刑事案件审判的核心环节。原、被告及证人三方之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进行质辩,法官则对案件疑点及不明之处反复查问,必要时不惜用刑逼供,直至主观性证据与客观性证据印证吻合,使得是非分明、事实大白,为案件最终的决断提供充足的理由。
(二)据证鞫、判
1.鞫鞫,亦作鞠,史籍对其多有注释。如《尚书·吕刑》:“输而孚。”传:“谓上其鞫劾文辞。”疏:“汉世问罪谓之鞫,断狱谓之劾。”《周礼·秋官·小司寇》:“读书则用法。”注引:“郑司农云:‘读书则用法,如今时读鞫已乃论之。”疏:“鞫谓劾囚之要辞,行刑之时,读已乃论其罪也。”《汉书·刑法志》:“今遣廷史与郡鞫。”如淳注:“以囚辞决狱事为鞫。”李奇注:“鞫,穷也,狱事竟穷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赵弟,坐为太常鞫狱不实。”如淳注:“鞫者以其辞决罪也。”以上所释“鞫”,核心含义为“穷”,即“穷竟其事”。
质证结束之后,法官就需要对案件事实作出归纳总结,这一环节在汉代被称为鞫。如张建国先生所言:“鞫是审判人员对案件调查的结果,也就是对审理得出的犯罪的过程与事实加以简单的归纳总结”[7]其在程序中处于质证结束之后,判决作出之前的阶段。《尚书》卷十九《吕刑》正义:“汉世问罪谓之‘鞫,断狱谓之‘劾,谓上其鞫劾文辞也。”
《奏谳书》所记载的秦汉审判案例,印证了“鞫”的存在及其性质。试例如下:
鞫之:媚故点婢,楚时亡,降为汉,不书名数,点得,占数,复婢,卖禄所,媚去亡,年四十岁,得,皆审。(简14—15)
意为媚原是点的奴婢,楚时逃亡,到了汉朝后没有申报户籍。点逮住她,仍以奴婢上了户籍,并将她卖给禄,后又逃跑被抓获。现年四十岁。经审讯,均属实。
鞫:阑送南,娶以为妻,与偕归临淄,未出关,得,审。(简22—23)
意为阑负责遣送女子南去长安,其间娶南为妻。非法携带南返回临淄。尚未出关即被查获。经审讯属实。
鞫之:武不当复为军奴,弩告池,池以告与视捕武,武格斗,以剑击伤视,视亦以剑刺伤捕武,审。(简45—47)
意为被告武不应当再做军的奴隶。军以亡向校长池告发,根据控告,池带领求盗视去逮捕武。武拒捕,用剑击伤视,视回击,用剑刺伤,并逮捕武。一切经审讯属实。
鞫之:苍贼杀人,信与谋,丙、赘捕苍而纵之,审。(简91)
意为苍故意杀人,信主谋,丙、赘抓获苍后,又将其释放,一切经审讯属实。
通过上述案例不难发现,“鞫”的内容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非法律的认定,是事实判断的过程。法官经由它作出法律认定,即依法作出最终的判决。其类似于当代刑事判决书中的“经法庭审理查明”部分。该程序内容也不包含原、被告行为的定性、法律条文的适用等内容。其中,结尾处的“审”或“皆审”,意味案件已调查清楚属实,审判官吏对之确认。其类似于当代刑事判决书中的“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判决
判决是法官依据案件事实,对当事人的行为从法律上加以认定,是价值判断的过程。在汉代,判决多以“论”的形式表现。张建国先生曾言:“‘论实际才相当于判决。”[7]陶安先生提出:“断狱无疑是以‘论断终结,但是更具体地说,‘论与‘断是指怎么样的程序呢?这一点恐怕还不太清楚。‘断似乎不是文书用语,它仅作为描写用语在法律条文以及相关注释等出现。”[8]更确切地讲,“论”是根据鞫之后的犯罪事实,寻找相适应的法律条文,对案件作出决断。例如《兴律》中所见“论”字:
县道官所治死罪及过失、戏而杀人,狱已具,勿庸论,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吏复案,问(闻)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丞谨录,当论,乃告县道官以从事。彻侯邑上在所郡守。(简397)
简文中“勿庸论”、“当论”之“论”即为“处置”、“定罪”之意。
《后汉书》李贤注说“决罪曰论”,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某罪应当给予何种处罚。《奏谳书》中的案例能够印证此观点。例如第四则案例,经过质证之后,确定了案件事实,并上报廷尉,廷尉据证依律判决为“娶亡人为妻论之”。简文中的“论”显然具有“定罪”或“以……定罪”之意。
分析《奏谳书》和其他文献中记载的断罪案例,发现汉代在案件事实认定后,则会据证依律令作出判决或者据证比附作出判决,以下对此两种判罚方式进行分析:
第一,据证依律判决
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案审官吏则需依律进行判决。汉代最基本的成文法是律与令,并且已对两者作了初步的区分,《汉书·宣帝纪》言“令甲”,文颖注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盐铁论》记载:“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9]在案件事实,即鞫部分认定确凿,法律对其规定清楚时,法官必须依律令作出论断。如《汉书·匡张孔马传》曰:“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讫也。”即按照法令,犯法者都要依照犯法时的法律论处,在时间上有明确的界限。
《奏谳书》中记载的大多数案件都明示依据律令而作出论断,试例如下:
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三十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以此当平。(简65—67)
即按照“令”的处罚规定论处平。
律:盗赃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无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简72—73)
即依照“律”的处罚规定论处恢。
律:贼杀人,弃市。.以此当苍。律:谋贼杀人,与贼同法。.以此当信。律:纵囚,与同罪。.以此当丙、赘。(简93—95)
即分别于律的不同规定对苍、信及丙与赘进行处罚。
可见,汉代法官在断决案件时,如果法律对之有明确规定,则直接援引律或令作出判决。
第二,据证比附判决
在有法律明文规定时,法官应当据律断罪。但是,如果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案件又较为复杂、颇有争议时,法官就要比照近似的法律条文或者依照判例作出决断。
《奏谳书》中的案例记载:
蜀守谳:佐启、主徒令史冰私使城旦环,为家作,告启,启诈簿曰治官府,疑罪。廷报:启为伪书也。(简54—55)
即左启与令史冰役使服城旦刑的刑徒环为其做家务活,有人告发了启。在刑徒劳役记录簿中,启谎称该城旦环在修理官署。此案件中启的行为在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地方官吏不知如何定罪,于是上谳,廷尉依照比附作出“为伪书”的判决。
另一种比附形式是依照判例进行决断。依据成例作为依据断案,这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否则人们将无所是从,这导致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滞后性。为了克服法律的这一缺陷,使法官在断决案件时能够有据可依,中国古代形成了判例法的传统,以此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与僵硬。这在秦汉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汉代则称为“决事比”。
判例即判案成例,汉代较为普遍地适用判例断绝案件。比的数量也较多,张汤上奏章治罪于颜异曰:“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 [10]自此便形成了“腹诽”之法的先例。《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达“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师古注“比,以例相比况也。”
作为判决“标本”的判例,是已经生效的案件中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典型性判例。该类案件一般较为复杂,或者颇有争议。判例形成之后,法官在日后遇到类似的案件时,即可将其作为判决依据。《奏谳书》就是一部案例集,它所载的二十多则判例,大多数都具有典型的示范性功能。它当中本身也有引用判例作为定罪依据的案件。最为典型的是案例三,当中引用了先例:
人婢清助赵邯郸城,已即亡,从兄赵地,以亡之诸侯论。今阑来送徙者,即诱南。.吏议:阑与清同类,当以从诸侯来诱论。(简23—25)
因为对于本案被告行为的认定,缺乏法律的明文规定,审讯官便在案件的判决部分引入了这则决事比,认为对被告御史阑的定罪量刑可以参照此则判例适用。
甘肃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中也记录了决事比的案例,如:
……高年受王杖……有敢妄譬、殴之者,比逆不道。
年七十受王杖者……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这是两则关于侵犯长者的法律规定,参照“逆不道”或“大逆不道”处罚。
在汉代,判例的条目繁多、体系庞杂,有些甚至彼此矛盾,很难掌度。对于轻重的比附,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制,这就使得司法官吏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以致“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5]这种随意比附的流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
引《奏谳书》中记载的第五则案例“江陵余、丞骜敢谳案”为例,以图表的形式归纳汉代刑事证据在起诉与审判环节的具体运用:
《奏谳书》江陵余、丞骜敢谳案中
述武曰:故军奴。楚时去亡,降汉,书名数为民,不当为军奴。视捕武,诚格斗,以剑击伤视,它如池。(简37—39)
视曰:以军告,与池追捕武,武以剑格斗,击伤视,视恐弗胜,诚以剑刺伤武而捕之,它如武。(简39—40)
证人证言
军曰:武故军奴,楚时亡,见池亭西。以武当復为军奴,即告池所,曰武军奴,亡。告诚不审,它如池、武。(简40—41)
诘问诘武:武虽不当受军奴,视以告捕武,武宜听视而后与吏辩是不当状,乃格斗,以剑击伤视,是贼伤人也。何解?(简41—42)
武曰:自以非军亡奴,毋罪,视捕武,心恚,诚以剑击伤视,吏以为即贼伤人,存吏当罪,毋解。(简43—44)
诘视:武非罪人也,视捕,以剑伤武,何解?(简44)
视曰:军告武亡奴,亡奴罪当捕,以告捕武,武格斗伤视,视恐弗胜,诚以剑刺伤捕武,毋它解。(简45)[]质证
验问
问武:士伍,年卅七岁,诊如辞。(简45)[]确认证据
据证鞫案[]鞫之:武不当復为军奴,军以亡弩告池,池以告与视捕武,武格斗,以剑击伤视,视亦以剑刺伤捕武,审。(简45—
汉代承继了秦代的乞鞫制度,在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允许当事人及其亲属在遵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提出复审要求。经过乞鞫,启动复审程序,上级司法官吏通过核实各项相关证据,重新审视案情,并作出复审处理决定。如果相关证据证明案件确属冤、错,法官会据证重新判决,并追究原判法官“审判不实”的责任。如果原判决准确,乞鞫者理由不成立,则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汉代乞鞫制度较之秦代,进一步趋于规范化。《二年律令·具律》中对乞鞫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罪人狱已决,自以罪不当,欲乞鞫者,许之。乞鞠不审,加罪一等;其欲复乞鞫,当刑者,刑乃听之。死罪不得自乞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为乞鞫,许之。其不审,黥为城旦舂。年未盈十岁为乞鞫,勿听。狱已决盈一岁,不得乞鞫。乞鞫者各辞在所县道,县道官令、长、丞谨听,书其乞鞫,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简114—117)
这一规定就明确了乞鞫成立的前提条件、主体、提起的期限等。下面将此项法律规定展开分析,以便透彻了解汉代的乞鞫制度:
(一)乞鞫前提
“自以罪不当”,即已被判刑的罪犯自认为判决不当。这是古今通在的引发上诉制度的主观心理状态。它是行为人提起乞鞫的前提条件。
(二)乞鞫主体
即有资格向上级审判机关提出乞鞫的行为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有两类:一为被判处刑罚的罪犯,其可以“自乞”,但被判死刑者除外;二为罪犯的亲属,包括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等人。同时,排除了未满十岁儿童的乞鞫权。从以上《具律》的规定可以解读到,被告人若被判死罪,其乞鞫权被剥夺,该权利可以由其亲属代替行使。《汉书·赵广汉传》记载了一则由亲属提出复审请求的案件:“广汉使长安丞案贤,尉史禹故劾贤为骑士屯霸上,不诣屯所,乏军兴。贤父上书讼罪,告广汉,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斩,请逮捕广汉。有诏即讯,辞服,会赦,贬秩一等。”此案即是由苏贤的父亲提出复审请求,上级官吏下达重新审理案件,赵广汉获罪,后获赦,被降一级俸禄。
《晋书·刑法志》记载了三国时魏国对该律文作出了修改,进一步限制了亲属的乞鞫权,“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为了减轻断狱程序上的琐累,缩减了亲属的乞鞫权,被告人若被判处两年以上刑的,就不许亲属为之乞鞫了。
(三)乞鞫期限
根据《具律》的规定,被告人或其亲属必须在判决结果作出一年之内提出乞鞫请求,超过此期限,则不得提出乞鞫请求。在《周礼·秋官·朝士》中已有关于听审期限的记载:“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十三经注疏》注引郑司农云:“谓在期内者听,期外者不听,若今时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鞫。”乞鞫期限的设定,一则在于督促行为人即时行使乞鞫权利,时间长久会导致相关证据的流失或难以确认,妨碍清楚认定案情;再则乞鞫拖沓时间过长,会造成案件的过度积压,增加司法审判机关的压力,耗费司法成本。
(四)对乞鞫“不审”所谓“审”,即“正确、确实”之意。如《法律答问》中载:“甲杀人,不觉。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后告甲。甲杀人审。”(简68)所以,“不审”即意为“不正确、不确实”。《二年律令·贼律》规定:“诸上书及有言也而谩,完为城旦舂。其误不审,罚金四两。”(简12)又如《史记》所载“赵高案治李斯”,秦二世“恐其不审”,就派遣使者前往案验。那么,“告不审”就指不正确的告诉、告发。《法律答问》中对此有定义:“甲告乙盗牛。今乙盗羊,不盗牛。问可(何)论?为告不审。”(简47)此外,由官吏所为的虚假告发,称为“劾人不审”。如《悬泉汉简》中的囚律佚文:“囚律。劾人不审为失,以其赎半论之。”(简Ⅰ0112:1)若官吏故意进行虚假告发,则构成“不直”之罪。如《二年律令·具律》规定:“劾人不审为失,其轻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为不直。”(简112) 的处罚
如果是被告人请求复审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则对其“驾(加)罪一等”;如果是亲属提出复审的理由不成立,则会被“黥为城旦舂”。汉代通过此法律规定,以防止乞鞫的随意性,减少诉讼的耗费与拖累。
(五)乞鞫的管辖
汉律对乞鞫的管辖主体及处理程序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乞鞫者应当各到其居住地所在的县、道提交上诉状。县道之令、长、丞应谨慎受理,将乞鞫的内容记录下来,并将狱案上呈其所辖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将案件交给都吏负责再审。都吏对案件进行复审之后,廷尉和郡以文书的形式将审判结果送到附近的郡;御史、丞相复审的案件,其结果应以文书的形式送达廷尉。
经过对汉代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在承继秦代乞鞫制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在法律上对之进行规制。从制度上而言,乞鞫之制确实能够对司法审判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减少冤滞案件的发生,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汉代国祚长久,一度兴盛,与此有益的司法监督制度关联甚大。但是,到东汉末期,国事混乱,动荡不安,乞鞫制度名存实亡。正如《潜夫论·述赦》所言:
奸猾之党,……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徒,下乃论免,而被冤之家,乃甫当乞鞫告故以信直,亦无益于死亡矣。
王符对当时妄行刑辟、滥施赦行的做法进行抨击:往往被冤之家刚刚“乞鞫”,而害人者即被“论免”,这对于蒙冤死去之人而言,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从中反映了,当时的司法活动已遭到严重破坏,乞鞫制度存在的现实价值已甚微。
现将该案例归纳为图表的形式,以便更加详细、透彻地对乞鞫案件进行分析,具体了解汉代刑事证据在再审案件各环节中的运用情况:
四、研究新见
通过对大量汉代简牍资料的分析考查,不难发现,汉代在诉讼程序中已经确立了较为完善的证据运用制度。汉代刑事证据的运用制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客观性的方面,也有主观性的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证据运用制度。所谓证据的客观性,是指通常在判断案情过程中,重制度、重勘验、重原始证据的客观效力,主张据证定案的倾向;所谓的证据主观性,主要指先入为主或因政治权力之争,或因经济利益之争,或因案情复杂、证据不足时偏离证据的客观方面,主观认定,甚至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动用刑讯手段陷人于罪的倾向;其综合性即是指将证据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结合,来判断现有证据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在案情认定上所具有的证明力的大小等。
以往对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研究,偏重其一个方面,即“口供至上”,强调传统刑事证据的主观性特征。陈兵指出,我国古代特别重视口供的作用,持“断罪必取输服供词”与“无供不录案”的断罪原则,所以将口供称为“证据之王”,直至清朝仍是如此。(参见:陈兵.解读现代“刑讯逼供”现象的根本原因——从我国古代拷讯制度合法化层面人手[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4).)刘显鹏也指明,中国传统诉讼的特殊之处在于极为重视被告人口供的“口供主义”,在中国传统的诉讼当中,被告人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没有被告人供认,一般不能定罪。其他证据的证明力都比不上口供高,人证、物证、书证只是辅助证据,而且必须在具有口供的情况下方能发挥作用,如无口供,仅凭其他证据不能定案。相反,如果有口供,即使没有其他证据,也可定案。(参见:刘显鹏.中国古代口供制度粗探[J].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2004,(3).) 这样的认识,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值得商榷。不可否认,“口供”是汉代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称其为“证据之王”也实不为过。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汉代的法制文明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运用于诉讼之中的证据制度,尤其是刑事证据制度获得了突出发展,在刑事证据理论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客观性倾向。在案件调查中注意对物证、书证及证人证言的采集,而且还注重录制勘验报告;在审判的质证环节,也强调使用客观性证据来印证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实性。最终达到确定性定案的追求。正如滋贺秀三所指出的,“总而言之,把本人的供述,与证据以及一切情况都加以对照并进行总和的考虑,供述似乎有不充足不正确的地方时又得重新进行反复的诘问,这种程序就是那样充满苦涩的调查过程。” [11]在这里,他虽未专指汉代的证据应用规则,但却是在阐释中国古代证据应用的普遍规则,即重视使用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验证。这是经过对汉简刑事证据材料的全面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新见。
五、结语
综括上述,汉简较为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汉代刑事证据在诉讼程序中的运用制度。使我们了解到,汉代刑事证据规则已趋于规范化与制度化。在提起诉讼环节注意对物证、书证及证人证言的采集,而且还注重录制勘验报告;在审判的质证环节,强调使用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来印证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实性;在上诉复审环节重视重新审核证据,查验案件事实。从提起诉讼,到勘验取证,再到庭审判决,直至乞鞫复审,证据的运用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支配与主导作用。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汉代尚处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早期,其法律制度的粗糙与落后是显而易见的,诉讼审判制度有待健全。“口供至上”依然是核心的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审讯方式的随意性也较大,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辞,往往使用酷刑。而且,对原告和证人动用刑具也甚为常见,且为制度所容。血肉横飞、哀嚎不尽之中导致冤狱丛生。这有奴隶制残余思想影响的因素,但更主要是缘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取证观念。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笔者认为,研究汉代刑事证据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本土优秀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历史传承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当前国情民俗的适应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汉代刑事证据的研究,可以达到追本溯源的功效。因而,考察汉代刑事证据的制度化、系统化的尝试与成败得失,对当代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意义深远。诚如博登海默所言,“作为使松散的社会结构紧紧裹在一起的粘和物,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连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 [12]汉代的证据制度作为法学或法律的积累成果,不失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ML
参考文献:
[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55.
[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92.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52.
[4]沈家本.汉律摭遗[G]//邓经元,骈宇骞,点校.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137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2.
[6]高恒.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51.
[7]张建国.汉简《奏谳书》和秦汉刑事诉讼程序初探[J].中外法学,1997,(2):55-56.
[8]陶安.试探“断狱、“听讼”与“诉讼”之别[G]//张中秋.社理性与智慧:中国法律传统再探讨.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8:70.
[9]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2731.
[11]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J].比较法研究,1988,(3):22.
[1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