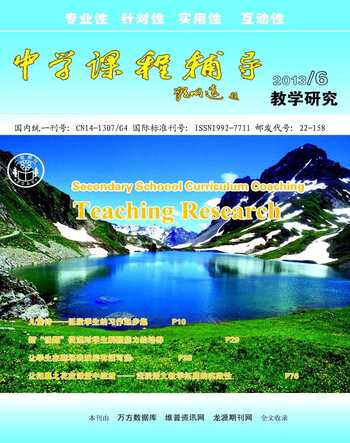由《孔乙己》中的“笑”说开去
王恩波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整体氛围本来极为压抑,有了笑声便特别刺耳,甚或让人愤恨至绝望。这些贯穿全文的“笑声”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颇值得研究。
在小说里,都有哪些人在“笑”孔乙己,又为什么要“笑”他呢?
首先要说的是咸亨酒店的掌柜。这掌柜本是一副“凶脸孔”,可是见了孔乙己,就每每故意问他的丑事,引人发笑,即使在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后也不放过。这样,在酒店掌柜的周围就是一群笑脸了。然而掌柜缘何要取笑孔乙己呢?文中交代,取笑他是为了“引人发笑”。孔乙己同其他短衣帮一样,是花钱买酒的顾客,为什么待遇就不同呢?对于掌柜来说,除了小市民的庸俗、刻薄之外,欺视孔乙己罢了。穿长衫的主顾是不敢取笑的;短衣帮呢,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收入,而且恐怕还很有一些力气。得罪短衣帮除了生意上受损失外,还有潜在的引发冲突的危险。相比较而言,孔乙己就很可欺了。他只是有了钱才来买酒喝,不能算常客,有时还要欠账,况且十九文铜钱于经济无损。最重要的是孔乙己软弱可欺,软弱到连为自己狡辩都不会,所以只能受“欺视”了。掌柜尽管不是地位很高,但也算的上是中间阶层了(至少在小说中是),欺负弱小或许是彼时这类市民的本性吧。
“我”也会跟着笑几声。但都是为了排解无聊,“附和”着笑的。这“附和”便有些讲究。首先是附和谁,当然是要看掌柜的脸色。《红楼梦》里贾母一哭,媳妇丫鬟都必须要哭的,察言观色,顺遂主人心意的做法驻在每个中国人的根里。“我”自然要讨好掌柜,保住自己的职务,至少也要做到“识脸色”吧。当然也附和众人,聊以轻松。
尤为刺耳的是短衣帮的笑。这是一群做工的人,繁重的劳动,贫困的生活和低贱的地位使他们一旦“散了工”,闲暇下来,就会极度的空虚无聊。这类人的特性是喜好聚伙找乐子。习以为常之后,就会麻木。这种情形下,出风头挑事的有之,围观“打酱油”的有之。何况孔乙己在他们眼中是不伦不类的人,取笑他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有一点,因为孔乙己“读过书”,他们绝不会视孔乙己为几类,所以他们对孔乙己是发自内心的排斥。对孔乙己的遭难,只是漠然而已。
至于那些长衫客,自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随众人哄笑,但是在心里对孔乙己的鄙视和冷笑是可以想见的。
孔乙己一出现,总是引来阵阵哄笑。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可笑之处,该不该笑呢?
仅从小说中看,孔乙己确有可笑之处:
笑他偷窃挨打,笑他说话迂腐,笑他虽然读书却无以进学,笑他无谋生手段却又好喝懒做,笑他性情软弱、遭人欺负而无力反抗,更笑他身为下贱却自命清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然孔乙己身上笑点多多,想让人不去笑他都是难事。而孔乙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却是出奇的好,众人的讥笑固然使他难堪,但是要说他是被“笑死”的,却也言过其实。
其实,究其根源,还应该是性格决定命运。
先来看看“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唯一”,说明是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在今天读书无用考试误人的论调也时而有之,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事件也时而有之,无论多么优越的社会制度也救不了孔乙己这样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土壤可以引导群体意识,却不能决定个体的命运走向。孔乙己在当时也只是个特例而已。在那时也有积极追求个人进步的人和寻求社会变革的人。所以不能把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归罪于制度和社会的弊端。现代科学还认为人的性格跟其血型有关呢。但是人的命运发展和性格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孔乙己是一个特殊的人,就会有独特的性格。不妨设问,孔乙己自己认为应该是“站着喝酒”的人,还是“穿长衫”的人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说:那些“站着喝酒”与“穿长衫”的人,谁对孔乙己的认同感更多一些?
前一种问法较易回答,孔乙己“站着喝酒”是为经济条件所迫,他放不下的是“穿长衫”的书生装,因为这装束意味着他是文化人——和做工的粗人不同,至少接近上流社会。即使不具实在的地位,也要摆摆身份架子。这是他的虚荣心在作怪。
对于第二种问法,我认为“穿长衫”的人对孔乙己的认同感更多一些。短衣帮对孔乙己只有无情的嘲笑,连对他的被打折腿和不知死活都表现得异常的漠不关心,可见短衣帮对孔乙己是绝对的排斥,绝无可能把孔乙己归在他们的阵营中。而“穿长衫”的对孔乙己则表现出一定的认同感。他们肯定孔乙己“读过书”的身份,赏识他的“一笔好字”,为他提供生活来源。只是因为孔乙己自己太不争气,不仅不求上进,还不顾圣人之道,偷窃他的雇主,免不了要受到责罚。今天路人见到小偷尚且切齿,何况丁举人之流也算照顾了孔乙己的生计,可是孔乙己把仁、义、礼、智、信的圣人之训全都违背了,这一番责打便不会留情。是否可以说,短衣帮嘲弄的是孔乙己的落魄,而丁举人之打,却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呢。孔乙己是读书人的败类,做不通学问,连诚实守信的基本准则都丢了。统而言之,孔乙己的悲剧源于他个人的不争气,众人所笑,也大都是笑他的性格和为人而已。
孔乙己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受人嘲笑是免不了的。然而作者对他所塑造的这个形象又是什么态度呢?
首先,我认为作者绝没有嘲笑之意,而是在冷峻的雕刻着一尊塑像,背景是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科举制度土壤下的长衫客和短衣帮。他们齐聚咸亨酒店,而柜台外面就是孔乙己的雕像。那是一尊没有血肉的木塑,线条深刻而又生硬。这尊像的形是孔乙己,灵却是作者自己。鲁迅是最善于解剖自己的作家,孔乙己的身上,总会有鲁迅自己的影子。
鲁迅是那个时期比较早觉醒的人之一,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深深的忧虑着。在写作《孔乙己》的一九一八年,社会动荡不堪,那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手握重兵、有实际权力和能力的人都在抢地盘、营私利,国外势力也在不断加深对中国的蚕食。这时的鲁迅不过一介书生,徒怀济世救民的理想,可是面对残酷的现实,个人微弱之力实在难有作为。所以他写《孔乙己》,除了与病态的社会战斗以拯救世人的灵魂外,也反映出文人报国的无奈与艰辛。“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是鲁迅在《新生》杂志夭折之后的感受。鲁迅还说“此后,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期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沉沦了一段时间后,鲁迅感到“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于是开始写文章,但“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而悲哀的原因是“一间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悲哀,而有人大嚷起来,惊起几个较为清醒的人,这些不幸的少数者就要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鲁迅正是少数遭受苦楚的人之一,内心有着深深的忧虑与悲哀。如孔乙己这般的不可救药,还有什么改变的希望可言?只有将求索路上深深的挫折感借由孔乙己表现出来而已。所以我说,《孔乙己》的主题,也要从作者身上发掘,对孔乙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毫无意义,要反映的正是作者心中责任愈大愈觉艰难的感慨,以及文人救国力所不逮的艰辛与无奈。
孔乙己式的人物于人无争,于社会却是大害。今天的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当像鲁迅一样警醒,不重实践,纸上谈兵,弄虚作假……种种不良风气都该改一改了。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南侨中学 36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