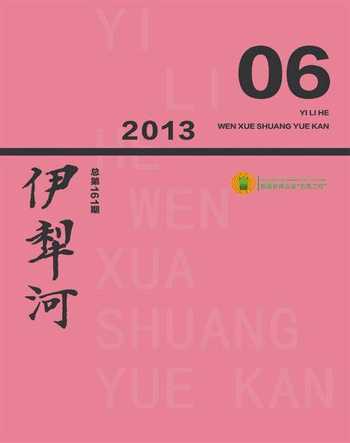人间正道是沧桑
吴孝成
父亲如果健在,今年就是他的100周年诞辰,遗憾的是他刚满61岁,便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一位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没有喋血沙场,没有埋骨荒原,却殒命于极左路线的魔掌之中,因而他死不瞑目,饮恨终身。
回顾父亲命运多舛的一生,其中充满了传奇色彩,也沉潜着太多的沉痛教训,值得梳理,值得回味。
枪林弹雨中的青春年华
父亲吴南山原名王政坤(1938年为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时改为现名),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南溪区麻河乡陈湾村一个贫农的家庭。从9岁起读了四年私塾,然后在丁家埠毛豫昌商店当了两年学徒。
自1927年起,他就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少年先锋队(根据地的青年武装组织),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正式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四军教导第二师政治部保卫连任班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调随营干部学校学习。1931年调红四军第十师手枪队任排长,后代理该队队长。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他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战争年代,受伤是常有的事,他身上的伤疤就有七八处之多。直到临终,他的左臂手腕上方的骨头中一直嵌着一颗子弹头。1932年,父亲调任该师二十九团六连指导员,第二年又调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任参谋。
红军长征开始后,父亲因为读过几年私塾,当学徒时又学会了记账、打算盘,在部队上被称为“小知识分子”,所以又被调到军部给政委曾传六当秘书兼参谋(曾传六解放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后来又随曾政委调红九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秘书、参谋和机要科长。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大搞分裂中央的活动,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过了三次草地。据父亲讲,1935年秋,在第二次过草地时,部队断了粮,野菜也挖不到了。一天他在打水时偶然发现,草滩上的小河沟里有鱼。因为当地藏民不吃鱼,所以河沟里的鱼很多,他们就徒手捉鱼,解决了口粮问题。过雪山前,红军将士都穿着单衣。他们在打土豪时收缴了一批棉布,但是没有棉花,做不成棉衣。裁缝出身的曾政委便亲自动手,给部下每人做了一件“千层衣”。衣服的层数虽多(六层),但御寒效果并不好,而且穿在身上很重。后来父亲来到新疆,看到老百姓将驼毛絮在棉衣里,比棉花还保暖,才想起当年在藏区就有不少驼毛,却不知道用它做棉花的代用品。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广元出发进入甘肃,和红一、二方面军在会宁县会师。为“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和五军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与强敌胡宗南、马步芳等部13个旅以及大批地主武装作战。历经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无数次浴血奋战,到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的绝大部分将士都英勇牺牲或被俘、失散了。剩余的部队继续在祁连山打游击。从倪家营子突围时,马家军的骑兵在戈壁滩上如入无人之境,许多红军战士蹲在地上向敌人射击,目标太大,惨遭飞驰而来的骑兵的劈杀。我父亲当时机智地平躺在地上,待敌人骑兵冲过来时,举起手枪将其击毙,然后翻身跃上马背,才摆脱了敌人的追杀。
4月初,西路军左支队接到中央军委发出的向新疆进军的指示,于是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左支队跨出祁连山,又经过安西、白墩子、红柳园等激战,剩余的400余人终于在4月底到达新疆的星星峡。当时我父亲的右臂已经负伤、化脓。刚负伤时,由于弹片切开了动脉血管,血流如注,危在旦夕。是曾传六拿出了他保存自用的最后一瓶云南白药,才算止住了血。连日的戈壁行军,大家都干渴难忍,先是喝马尿、人尿,后来又杀了马喝马血。由于马血是热性的,不少人因此流鼻血不止。晚上行军时,就从路边捡拾冰冷的石子,放在口中给冒烟的嗓子降降温。一粒石子含热了,再换一粒新的。父亲由于伤口发炎而高烧,路都走不稳了。他便对战友们说:我可能坚持不到新疆了。等革命胜利了,你们想办法给我老家的父母捎个话,就说我在去新疆的征途上“光荣”了。这一年,他才24岁。凭着青春的活力,凭着顽强的意志,他终于吊着胳膊踏进了星星峡。5月1日,见到了代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来迎接西路军指战员的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一行。四百余条铁汉就像失散多年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一样,父亲和战友们都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大批衣物、食品和武器弹药,红军将士们换装后乘汽车抵达迪化(乌鲁木齐),又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矗立在哈密市“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园”内的纪念碑文准确地概括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段悲壮的历程:“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黑云压城时的艰难经历
父亲和西路军左支队的战友们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来到乌鲁木齐后,驻扎在西大桥阜民纱厂内(现新华印刷厂),改编为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内形成的和平局面及新疆的有利条件,陈云同志及时建议党中央将左支队余部留在新疆学习文化知识和现代军事技术。陈云同志亲自编选教材,邓发、陈潭秋等同志亲自上政治课。学员们分别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兽医、情报等专业技术。1938年3月,父亲与刘庆南(万友林)、杨文先(卓锋泰)、杨天云(贾诗评)、张明敬(韶清)、谭政文(赵俞)等战友受西路军总支队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情报业务。据父亲回忆,当组织上准备抽调他出国时,老首长曾传六同志舍不得让他离开,陈云同志还批评了曾传六同志,指出:这些同志都是经受了血火考验的红军骨干,他们正年轻,又有文化,应该让他们出去学习本领,将来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过八个多月的谍报业务学习,他们回到新疆,父亲被分配到边务处驻哈密办事处任少校副主任,驻星星峡分处任主任。其他人也分别在蒲犁、和田、哈密等办事处任职。边务处是1936年盛世才在边防督办公署内设立的一个情报机构,在全疆各边防重镇下设7个办事处,在外省还设有一个参谋办事处和两个直属情报组。父亲他们公开的职业是为盛世才督办公署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税务、社情等方面的情报,暗中的身份却是共产国际在新疆的情报人员。为此他们定期将一些重要的情报传送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据我母亲回忆,1943年上半年的一天,父亲曾在迪化西公园的一个公共厕所内,给苏联总领事馆的武官传送过情报。当时母亲抱着两岁的我,坐在附近林间的椅子上为他们望风。
父亲在哈密和星星峡边务处工作的五年间,收集了大量关于马步芳、马鸿逵和蒋介石敌视盛世才,觊觎新疆的活动信息,以及日寇侵华的情报。重大的情报有驻敦煌的马步芳部队编制、人马枪支及装备数;驻敦煌蒋军四十五师的编制、装备;四十五混成旅的编制与军事计划等。在星星峡还指挥边卡队布置防务,严巡边卡,侦察逮捕乔装潜入的马家军和蒋军的特务分子、越境犯、走私大烟犯等。
1942年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抛弃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公开投靠国民党,大肆进行反苏、反共活动。边务处于1943年春正式撤销,原在该处任职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先后被捕入狱。我父亲也于1944年5月与其他战友一起以“共党嫌疑犯”罪名在迪化被捕。当时我母亲带着我被送往七道湾的一座织袜厂内,那里实际是集中营。两个月后,我舅舅赶到迪化,将我们母子接回了巴里坤。父亲直到1945年11月才被取保释放。出狱后他们请示总领事馆要求工作,上级说:你们刚刚出狱,还没有摆脱监视,待半年后局势稳定了再安排工作。他们几个狱友便各自投亲靠友,转移到各地。父亲于1946年8月回到了巴里坤,由于国际、国内的局势急剧变化,从此便中断了与组织的联系。
这一年10月,当时的镇西县县长王东阳(中共地下党员)委托何生琦与我父亲筹建镇西县中学,何任教务主任,我父亲任总务主任。1947年4月,原边务处职员王立民到巴里坤与我父亲研究成立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的事宜。我父亲就地在哈密地区发展成员,成立了“镇西情报组”。当年11月,先锋社(原名“中国共产党新疆省支部”)在迪化正式成立,镇西情报组也改组为先锋社镇西县支部,我父亲任支部书记。1948年春他又在哈密成立了哈密县支部,当年秋进而成立了哈密区支部(工作由镇西县支部兼任)。
“先锋社”是由中共派往苏联学习后又由共产国际派到新疆边务处工作的几个情报人员组织起来的。从组织成立一直到新疆和平解放,该组织做了大量的搜集情报、调查社情、渗透国民党军队、宣传群众、迎接和平解放等方面的工作。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审查,认定“先锋社”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进步的地下革命团体”,指出组织的成立并未受到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委托,所以不是正式的党的组织机构,根据其所出版的油印刊物《先锋》称之为“先锋社”。
由我父亲负责的镇西县支部和哈密县支部根据上级指示,两年多期间,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地的胜利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搜集驻地国民党军队、自卫队和警察局的编制、装备、部署情况,策反部分敌军骨干,派员打入国民党的党政机构,解放前夕组织力量维护镇西县社会秩序,派员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协助解放军剿灭乌斯满叛匪等等,做了大量有益有效的工作。1949年9月27日,哈密发生了抢劫案。事后叛军逃往镇西县达子沟。我父亲协同县长王东阳等人亲临达子沟劝降,说服他们弃暗投明,归顺人民。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兵力威慑下,在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感召下,这一营官兵迅速分化瓦解。在带领解放军剿匪的日子里,父亲常常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有时数日都不回家。
解放前夕镇西县的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尖锐复杂,军队中有派系,地方上有会道,国民党有公开的党部、警署机构,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也有潜伏的地下工作者,牧区和深山还有美国领事馆煽动支持的蠢蠢欲动的乌斯满匪帮。甚至亲属中也多有中归属于不同政治集团的情况。父亲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绷紧全身的神经,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哈密抢劫案发生后,镇西县驻军中也有少数人连夜叛逃,枪声响了一夜。当时我看到父亲镇定自若,不是外出侦察情况,就是在家听取汇报,井井有条地部署对城中要害部门的保护和对叛军动向的监视。正是由于先锋社镇西县支部的努力工作,才使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镇西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为人民解放军的进驻和此后的剿匪、镇反等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司法战线上的激情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我父亲被任命为巴里坤县人民法院副院长,1951年8月调任哈密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当年冬天被派往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53年春结业返回原职。1956年秋调任新疆自治区律师协会筹备处副主任兼乌鲁木齐市法律顾问处主任。
我父亲在司法战线上整整工作了十年。他担任巴里坤县法院副院长时已经37岁了,司法工作对他而言是个全新的领域,他不会就学,不懂就问,边学边干,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面对大量的案件,他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取证,一件件审理、结案,付出了许多心血。尤其让人纠结的是,审判对象中有的是自己的亲属,有的是熟人,他都做到了公正执法,不徇私情。
自他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回来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开始兢兢业业地抓法制建设,抓地区中级法院和各县法院的规范管理,抓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设,凡是重要的案件,都有各机关、团体、企业职工推选产生的人民陪审员参加。这一时期,他搞调研,办培训,抓建设,忙得不亦乐乎,仍然不忘学习,我家的书架上摆满了当时能够买到的所有法律、法规汇编。
他调任乌鲁木齐市法律顾问处主任时,正值我国开始律师制度建设的时期,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成熟。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自治区律师协会的筹建工作,致力于法律顾问处的机构完善。为此他四处选调合格的律师,向社会宣传律师工作的重要性,并亲自担任律师,介入诉讼事务。就是这一段律师实践活动,让他引火烧身,为后来的噩梦种下了祸根。
1957年我父亲在市法律顾问处先后接待了新疆军区的四名干部,他们有的是师级干部,有的是副团级或营级干部,他们控告的对象都是新疆军区的有关领导干部,控告的内容或是被告贪污腐化,或是被告破坏婚姻,或是被告利用职权打击报复。顾问处和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他们也缴纳了手续费。父亲给他们提供了法律意见,有的人文化水平不高,还帮其修改了诉状。就是这样几件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几个人都是先在军事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胜诉,所以转而到地方上的法律顾问处寻求法律帮助。他们担心这次诉讼如果被军内有关方面获悉,必将前功尽弃,因此提出要求,希望保密。后来,以上四人均由军区军事法院处理,有的定为坏分子,判刑劳改;有的被开除军籍、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我父亲因为这件事的牵连,1958年被停职反省,参加修渠、筑路、大炼钢铁等劳动。直到1960年,被以“支持坏人无理取闹”的罪名定为右派分子。我曾就此事咨询过上海法学会的同志们,他们回信称:“律师办案赋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律师在职权范围内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为当事人修改诉状,提供法律意见,在政治上法律上应当得到保证。当事人判了刑不应受到连坐。”
为了达到将我父亲开除公职的目的,有关部门觉得光靠一顶“右派”帽子分量不够,于是从档案材料中搜寻出一件历史积案:1956年总审干时,有人曾检举我父亲解放前担任过镇西县中学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职。解放后我父亲曾向组织交代过,1943年在边务处为了掩护地下工作,经上级批准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至于担任区分部书记则是没有影子的事。
事实真相是:1948年镇西县中学校长、区分部书记何生琦当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决定另选区分部书记。当时有人曾建议我父亲担任,父亲当面就拒绝了。此人又向何生琦推荐,何一口回绝,说:吴南山是“八”字号(意谓与共产党有关)的人物。后来何生琦直接指定学生聂隽魁担任书记,何生玉(何生琦之弟)等人担任委员。谁知十二年后,有关部门便据此诬告将我父亲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巴里坤县被监督改造期间,我父亲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希望趁当事人俱在之时,就地查清这一冤案,但是一直无人理睬。据当年曾参与整理敌伪档案的王平同志说,见过一张据说从纸篓里捡来的表格,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制表人是王平。而王平说那根本不是他的签字。这样明显的疑点被人轻轻放过,是何居心不是一目了然了吗?须知,我父亲当时正在镇西和哈密两地组建地下进步组织“先锋社”,怎么可能去担任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呢?何生琦已经认定我父亲是“八”字号的人物,怎么可能放心地让他代理区分部书记呢?
专政铁拳下的屈辱生涯
就这样,1961年初春,冒着料峭的寒风,我父亲拖儿带女,戴着两顶“帽子”,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巴里坤县大河公社三大队三小队接受监督劳动。
蹊跷的是,我父亲当时下乡时带的是自治区民政厅写给巴里坤县民政科的介绍信。巴里坤县也把他看做机构精简后的下放干部对待。下到生产队后,队里还安排他担任水利工地食堂会计。直到当年冬天,我父亲进县城参加积肥劳动时,县里正在集中全县右派分子学习,但没有通知他。他便主动去县委统战部询问,对方回答:我们不知道你是右派分子,待我们请示上级后再通知你。过了些日子,统战部通知他去学习。就这样,父亲为了能够尽早地摘掉右派“帽子”,从而自己主动地戴牢了这顶“帽子”。
十三年被专政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他便成了首批打击对象。1967年1月间,我的父亲、母亲(家庭妇女)都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将两个人的手、脚、耳朵全部冻坏。生产队抄了我们的家(此前城里的红卫兵已抄去不少东西),将家属子女们穿的衣物和家庭用具没收一空,如同水洗。大至皮箱、大衣,小到纽扣、调料,全被查抄,做为“胜利果实”分给众人。
从1968年4月到1970年10月,国务院商业部的造反派组织一共来了六个工作组,专门找我父亲调查所谓曾传六在长征途中杀害林彪部下胡抵烈士一案。因为我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情,便将他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天天审讯。前后关押一年零两个月。特别是1969年5月底来的第四个工作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经过两个月的刑讯逼供没有拿到口供,又押回公社,组织干部群众施行群殴,连续斗争四天,打得父亲遍体鳞伤。公社武装干事的一拳,就打落了父亲的三颗门牙。父亲实在无法忍受,只好自缢。虽经抢救未死,但又被打断几根肋骨,直到拿上逼供编出的材料才罢手。后面又来了两个工作组,一个让实话实说,不许捏造;一个叫老实交代,证明曾传六有罪。估计这些工作组分属两派,各有所求。第六个工作组走时还留下了话:还要来。所幸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自我爆炸,所以第七个工作组才没有来成。
但是1970年2月开始的军宣队斗批改,又使我父亲大难临头。这次有些人一心想把我父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历史反革命”是死老虎,已无油水可榨)。经过多次大小会批斗、毒打、捆绑,又放在雪地和水泥地面的仓库内挨冻,反复抄家,查封住房,妄图找出父亲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电台和照相机,为此连土炕都被拆了。最后翻出了几节年幼的弟弟捡来玩的废弃五号电池当做“罪证”。我母亲也被捆绑、罚跪、毒打,进行逼供,至今手腕上还留有绳索捆绑勒出的筋疙瘩。一次被人从暗处朝头上砸了一砖头,砖头都碎了,母亲当场昏死过去,至今留有后遗症,长年头疼。
除了对我父亲、母亲进行摧残,我的弟弟妹妹也连带遭殃。他们被打得不敢上学,不敢出家门。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绕远路,溜墙根,钻渠沟。每天给在押挨斗的父亲送饭,也是他们的一大难关。一路上总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一个人被打得受不住了,只好兄弟姐妹几个人轮流出去挨打。他们参加农业劳动,不能与别人同工同酬;父亲的义务工特别多(除了扫雪、补路,还要长年包掏三个厕所),病重不能劳动时,就从子女的工分中扣除。大弟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参加劳动,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三个妹妹都只读了小学,不准升中学。全家人都被当做四类分子对待,出外、进城均须请假。通信也没有自由,在外两个子女的来信经常被拆封审查,直至扣押没收。
刚下乡那几年,因为弟妹们都小,吃饭的人多,劳力少,仅吃粮和烧炭两项就欠了生产队两千多元的账。一年辛辛苦苦养大一头猪,也被拉去抵了债,十二年没有分到一分钱。直到1973年冬全家人拼死拼活,才算还清了债务,分到了一百多元钱,可是父亲已经生命垂危,医治无效了。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贫病交加,父亲临终前已经精神失常。他不时地会抱着写好的申诉材料往外跑,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接我来了”。一直熬到1974年4月13日,终于饮恨辞世。咽气后一直不合眼,真是死不瞑目啊!父亲死后,正在山上劳动的子女不准回家奔丧,向队里请求派几个人帮忙挖个墓坑都不同意。大弟只好一个人在北戈壁上挖了一天,第二天就草草埋葬了。
二十年沉冤莫白,一直株连全家老少三代人。母亲被当做四类分子遭受迫害自不待言,八个子女无一幸免:有的影响了升学,有的影响了毕业分配,有的影响了接受义务教育,有的影响了恋爱婚姻,有的影响了入党入团,有的影响了招工参军。就连孙女患了小儿麻痹症,因为爷爷是右派、反革命,父亲是臭老九,又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工宣队、军宣队就是不给她的父亲准假。因为不能及时出外治疗,造成双腿瘫痪,遗恨终身。一位心理治疗师说得好:“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对于这一切,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春风骀荡里的绵绵思绪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直到1979年,经过我与大妹半年多的上访、寄送材料,给自治区党委、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写报告,给陈云、李先念、江华、曾传六等领导同志写信汇报情况,终于盼来了一纸略说革命经历(26个字),突出错误与问题(91个字)的“复查结论”。就连1937年随西路红军进疆一事,还要加上一个含义深奥的定语:“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影响来到新疆”。西路军进疆明明是党中央的决策,他们偏要说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影响”,意思是我父亲早在红军时代就自觉地追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这和党中央关于建国前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等来了一个“决定”:“对吴南山同志右派分子予以改正,原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予以撤销。恢复其干部待遇,做好善后工作。”
平反后,我父亲的追悼会终于在1979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三周年的日子)召开了,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地点选在巴里坤县,主要是为了消除十八年的恶劣影响。追悼会前我草拟了一份发言稿,事前送给主持追悼会的自治区高级法院和哈密中级法院的领导同志过目,可能其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恭的言辞,也有为什么把追悼会选在这一天的深层考虑,他们临时取消了我的发言。想来在那个“两个凡是”泛滥的时期,他们的小心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前往北戈壁扫墓。远远就可看到一座矮矮的孤坟默立在秋风中,周围几百米内再没有坟茔,可见在另一个世界也无人愿与落难者为伍。我们给父亲的墓塚培土后,补立了一块木制的墓碑,上书“红军老战士吴南山之墓”。二十多年后我们换立水泥墓碑时发现,这块木制墓碑虽经日晒雨淋,已经陈旧斑驳,却完好无损。而附近的木制墓碑早被放羊的人烧火取暖,化为乌有了。看来是“红军老战士”几个字发挥了作用,公道自在人心啊!
我们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手稿时,发现除了自传、交代材料、申诉材料、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书信底稿外,还有一份《今后十大计划》的提纲。其中有重新撰写简历,追记“文革”中国务院商业部六个工作组的刑讯逼供经过,分专题撰写解放前后的回忆录,以及今后改善生活、教育子女的打算等内容。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一部分属于对农村工作的思考,诸如“教育农民的长期性”,“改善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农、牧、渔、副全面发展”,“发展手工业和繁荣市场”,“开办小型加工厂(家庭分散经营,集体管理)”,“农村远景规划”等。没想到父亲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以戴“罪”之身、贫病之躯,受尽了凌辱与摧残,但他老人家依然在考虑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生计,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啊!这需要具备何等顽强的毅力啊!正因为如此,他才急切地盼望尽快解除禁锢他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枷锁,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继续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不畏浮云遮望眼”,“人间正道是沧桑”。
父亲去世已经40个年头了。四十年来家国,八万里地山河,现在我们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你青年时代出生入死为之献身的理想正在实现,你中年时代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在达到,你晚年时代梦寐以求“还我清白”的愿望已经变成现实,你当年思考与憧憬的新农村建设的蓝图已经绘就,并在实施之中。
回顾父亲一生的坎坷遭遇,我们更加怀念无数流血牺牲的先烈志士,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更加坚定了继往开来,实现美好中国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