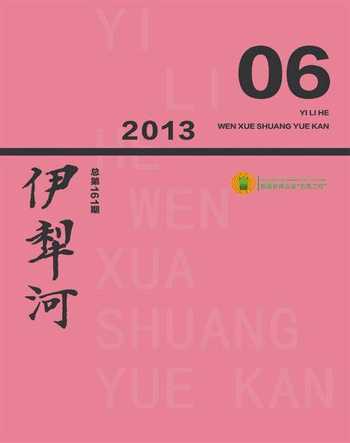木垒三题
远人
木垒县位于天山东段北麓,因木垒河得名。县城虽小,却东与哈密地区巴里坤县接壤,南隔天山与鄯善县相望,西与奇台县毗邻,北与蒙古交界。来新疆前,我从未听说过它,但此刻我站在它的眼前。
——题记
旱 地
听到这个名字时,我以为是“汉地”。我问当地陪同的李健,“是大汉的汉吗?”李健点头说是,只一个瞬间,他反应过来,“是干旱的旱。”我颇为奇怪,对名称的想当然使我觉得,我们要去的地方大概是一片干旱之地——有必要去这么一个地方吗?
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的路程,李健的越野车早已离开县城的柏油路。似乎无穷尽的沙石路弯弯曲曲地在车轮下扬起灰尘。我们像是进入一个无人区,窗外空气新鲜,但没有一丝一毫的生命迹象,旷野倒是开阔。新疆的最大特色就是开阔。现在看不到太阳,但天已大亮,不再是出发时灰蒙蒙的感觉。车子七弯八拐,慢慢地像是走上一条入村之路,灰尘少了,因为路旁有房屋。有房屋就有人烟,有人烟就有灰尘的逐渐消失。但我们一路看不到人烟,似乎那些房屋千百年来就已成空室——破败、凋敝。但还是能够肯定,不论多么凋敝的房屋,只要门前有狗、有马,就一定有人居住。我们动身得太早了,房屋里的人都还沉睡未起。我开始体会难以言说的奇特宁静。
再过一会,车子像是终于进入某个村庄。路边忽然看见有男人面对荒壁撒尿。听到车来,只漫不经心地扭头看上一眼。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间房中。他对车漫不经心,也对他每日看到的一切漫不经心。但他漫不经心的却不一定就让我们也漫不经心。
眼前的一切突然出现变化,不再是刚才路上所见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麦地在眼前忽然展开。一块四四方方的麦地旁边,是同样一块四四方方的空地。麦地是黄色,空地是泥土的褐色。我无法计算这片麦地的面积,方圆大概有好几十公里吧?李健将越野车停在麦地间的一条小路上,我走下车,便在麦地的腹部站住了。围绕麦地的,是绝对不高,但却连绵不尽的远山。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我平素以为要经过电脑制作的画面在我面前真实地铺开。太阳绝不将它的光线一下子笼罩全部,一层血一样的颜色整整齐齐地将远山涂成一半血红一半山峦本色。在这里,太阳升起的速度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它移动一毫米,山峦的本色就被血色覆盖一毫米。这才是大自然本身的奇伟。整个麦地却始终是麦地的本来颜色。时值八月,麦子黄了,我们看见的就是黄色。多年以来,我不无遗憾的便是我缺少我渴望能拥有的农事经验——也正是这一缺少,我才会如此惊奇,才会如此出乎我自己意料地忽然感动。
李健说,麦子熟了便有重量,因此麦子全部都低头弯腰。果然如此,我伸手将几颗麦粒剥下。念头忽动之下,我捏开麦粒上的薄皮,看它在我掌心滚动。我扔进嘴里,一股无法描述的甜味在舌尖漫开。忍不住一连吃了好几颗,李健对我的行为不以为然,他看着远处,唠叨着我们没早动身一个小时,否则周围的景色会更加令人动容。片刻后他忽然说,走,我带你们去更好的地方。
这地方的确更好。在拐过麦地之后,一条似乎可以通向山顶的路出现在眼前。但我们没有开上去,半途停下。我们下车,周围的一切都更加开阔,无论朝那个方向去看,都只给人无边无际之感。特别是朝路上方看去,太阳的血色已变成全部的暖色。一层层远山耸立起它们的绵长与神秘,在蓝得耀眼的天空下面变成更令人心动的瓦蓝。我陡然间就想起美国二十世纪前期绘画领袖格兰特·伍德。格兰特的画全部是描绘他的乡村故土,让我迷恋过好长一段时间。但无论怎样迷恋,我那时都觉得他不过是在探索和完成一种风格。我为格兰特写过一篇叫《他们在凝视什么?》的短文,在文中我写下了我对他作品的感受:“……那些阳光、田垄、房屋,当然不会只属于美国,但只有格兰特,将那些对象画得开阔无边,也画得生气勃发。就画面来说,格兰特表现的景致还有个醒目特点,那就是读者在读这些画时,会感觉正和画家并肩,在一个高远的山冈上凝望大地。眼前舒缓起伏的田地犹如绿色地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苞芽破出地面,被无边无际的阳光抚摸。大树四处散开,丛丛树冠,无不像一块块在焙烤的面包,唤起收获不远的人心激动。”
我无法不惊奇的是,我对格兰特画面的感受居然就是我此刻面对的真实呈现。他画下过什么样的田垄,这里就出现什么样的田垄;他画下过什么样的房屋,这里就出现什么样的房屋,甚至,他画下过什么样的阳光,这里就出现了什么样的阳光。我忽然明白,一个人画笔下的风格难道还要去创造吗?大自然早已将它的风格展现在你面前,你只要如实地将它画下来,你就能完成你想要完成的艺术。
我走上身旁的一个小小山冈。和远山相比,这里不是制高点,但从近旁二十公里的范围来看,它已经是最高的地方了。我从来没有在如此高远的地方站过。令我最惊奇的,已经不是面前的景色之美,而是无边无际的宁静就在这里。几十公里的范围,不可思议地没有任何声音。平生第一次,我发现安静可以让人内心发抖。像是不约而同,我们一行人谁也没有再说话,好像只要一说话,我们就会辜负这无声万籁的信任。我从来没意识过,安静是有深度的。它哪里也不去,只往大地深处下沉。安静越是广阔,就越是往地下沉入得从容不迫、沉入得我行我素。我走下山冈时,再也忍不住在满山的草地上躺下来。我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地躺在地上,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如此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躺下,让整个身体都和大地发生接触。我知道,我是在和安静发生接触。我没有认识过安静。我今天认识了。我伸开四肢,眼前就只有深蓝的天空。这蓝色疯狂得无边无际,乃至没有飞翔的鸟,也没有飘过的云。
鸣沙山
鸣沙山猛然就出现了。在方圆数百公里的旷野上。旷野是黑色,石头最多。若掉开视线看别处,不可能觉得有座鸣沙山在身后。因为旷野太难变化。大地没铺上柏油之时,大地就是旷野。旷野里只有石头和尘土。偶尔会有一些草尖冒出地面,但走过的人总是漫不经心,将这点绿色踏枯。看着旷野,会觉得旷野无边无际。无论视线延伸多远,也始终觉得,旷野之外,仍然会是旷野。
但旷野上矗有一座山。
有山不奇怪。所有的山都是在旷野之中。奇怪的是,这座山全是沙子。沙子赭黄,无一颗称得上颗粒,像一片海滩突然隆起,和旷野划出十分清晰的界线。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座沙山是假的,是人工堆积在这里的。但它不是,它就是一座山。对这样的景观,我从来不想去检索它的成因和年代。就像对人对事,知道得越多,一种陌生感也会失去得越多。我喜欢陌生的感受。陌生会让我的血脉突然加快。当陌生感突然来临,陌生会变成惊奇。古罗马的奥勒留斯曾说,男人到了四十岁就无所不知。这句话颇有气势,但掩盖的实质却不无悲哀。因为一个人“无所不知”之后,便不会再有对世界的惊奇。换言之,惊奇会是对四十岁男人很鲜有的感受。我始终喜欢惊奇。譬如现在,我猛然间看见这座沙子堆成的山,就不能不感到惊奇。我不想检索它的成因,但我愿意想象它的成因。那是上帝的手想握紧它。但沙子太细,连上帝也不能将它握紧,于是它就从天空倾泻,在旷野上堆出这座沙山。
物以类聚。当无穷无尽的沙子堆到一起,它们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内在密度。它们抱成一团,风吹不散,雨冲不走。大自然比所有的事物奇妙。如果说,所有的事物构成大自然,那所有的事物就都有它的奇妙之处,只是人总习惯藐视那些渺小之物,以为渺小的便不成气候。但渺小的事物一旦积聚,它们就形成奇妙的自身。
令人奇妙的事物才是真正具有力量的事物——我在鸣沙山领教的就是这感受。
我想登上去。山不高,不到两百米。即便两百米,又能有多高?很多人在登,手里还拿个小小的红色滑床。到山顶后,就可以坐在上面滑下来。我也拿了一个。这山近在眼前,走过去才知道,它和停车处不近。到了山脚,我仰望它,它真的不高。我登过的高山不少,没把它的高度放在眼里。看看其他的登山者时,有点奇怪,不明白为什么每人都在半山腰喘气。难道两百米的高度如此之难?我一脚踏上去,细到极处的沙子居然很硬,表面的一层虽然塌陷,但稍深处就结实起来。好像深处的不是沙子,而是石头。只是不知道那石头究竟在多深的地方。似乎就在脚下,但稍一用力,脚又继续塌陷。再用力时,脚下像是到了实处,但每个人都知道,实处的不是石头,还是沙子。
登得十余步,我开始体会登山与登沙山的区别了。
沙山不让你脚踏实地。在很多时候,沙子产生摩擦,但能产生摩擦的沙子却又滑溜无比。每走一步,脚下的十分力只能被沙子接受八分,另外两分力就在沙子的滑溜中消失。想挽留那两分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每走一步,用上十二分的力。
越往上走,表面的沙子就越容易出现塌陷。塌陷导致跨出的每步都稍稍后移。不知不觉中,我听到了自己逐渐加深的喘息。这里不可能深一脚浅一脚,而是步步变深。沙子从每步覆盖到鞋帮的深度,已变成每步覆盖到了鞋面,以致每次从沙子中拔脚都变得特别费劲。更何况,沙子塌陷越深,也就滑得越猛。什么叫步步艰辛,你登一座沙山就有体会了。我回头看看,李奕和黄依然原本跟我身后,此刻却还在距地面二十步左右的距离。她们对我摇手,没力气往上走了。我停下来,朝她们喊几声,想等她们攀上,只看得一会,便知道她们不会上来,毕竟体力难支。我突然发现,我这么一停,也觉疲惫忽来,双腿无力,但此刻站在沙中,哪怕不动,也得运力于脚,否则有陡然滑下去的可能。我不由也想放弃算了。登山前没有喝水,大口喘气已久,更觉干渴难熬。再看看上面,山顶上已经有人攀上。放弃的念头不由抛下,继续攀爬。现在真得用上“爬”字了。只靠双腿,不可能走上山峰。沙子看似不动,在脚下稍稍一惊,沙面便如流水,往下只泻。恍惚间觉得自己是在陡峭的流水之中。只是这流水深黄,不起波浪,只飞快倾泻。越往上,沙面越陡,越陡越滑。我俯下身,手脚并用,但速度没办法提起。更令我忍不住有点绝望的是,我似乎爬了许久,但好像根本没上前几步,很明显地感受便是,往前一步,沙子便将我推后半步。体力消耗之快,似乎从没像今天这样体验。放弃的念头再次涌上。我目测了一下自己距山脚与山峰的距离,发现已经攀到五分之四的位置了。此刻放弃,未免可惜。一咬牙,继续往上。只觉腿如铅石。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高度,要真正地征服它,远比想象的艰难。大自然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征服的欲望,立刻就给你难度。没有哪种征服可以轻而易举。即使你要征服的不过是一堆沙子。但沙子变成沙山,就会反过来给你颜色。
我不敢抬头再看,因为近在咫尺的山峰已像是不可到达。我低着头,手脚入沙,不断向上。全力以赴的速度在这里比不上一只蜗牛。终于,我偶再抬头,居然离山顶只三步之遥了。奋力攀上去,大感意外的是,发现两边山坡撑起的山顶竟然是平的——这意外难道就是给攀上者的酬谢?我没料到过这点。但实际上,我们都应能料到。一座沙山的山顶不可能会尖峭如石。千百年的狂风也不会让任何一颗沙子独占鳌头。惟其如此,这山顶的硬实程度才让人惊愕万分。我的最后一步是翻身上去,然后坐在平整如削的沙山山顶。山的另一面,几乎是一片炫目沙海。疲累夺去了我所有的感概。我就坐在上面,我也不需要任何感概。我看见不少攀到山顶的人都立刻坐进滑床滑下去,好像他们攀到山顶,就为了享受滑下去的快感。我还拎着滑床,我也想享受那种快感。但我还是坐在山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坐上一会,我更不知道,这个坐上一会的念头,为什么让我在与天相接的沙海间感到突然不能自拔。
胡杨林
从《英雄》开始,张艺谋就热衷于给观众打造烂片。片子虽烂,里面的风景却是可取。至今我都记得《英雄》中那场红妆武斗的落叶场景。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心中不自觉存起一念,什么时候能亲眼见见那风景实地,也算不枉为烂片市场贡献数十大洋。毕竟名导愿沦为向导,没理由不破破腰包。但我没打听那落叶林究竟在哪儿,念头自也逐年淡去。
没有料到,在去胡杨林的路上,沈苇兄随口告之,即将见到的胡杨林便是张艺谋的取景之地。我不由精神一振,早随时间消失的意愿一下子涌上来。此刻天空高远、深蓝,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旅行气候了。秋天已至,此刻的胡杨林,应该是最美的时候。
从鸣沙山到胡杨林,不远不近,北行三十公里即到。进入胡杨林地界时,我心中隐隐有点失望。眼前所见,都是低矮的树木,像是到了一片灌木丛中。“这就是胡杨林吗?”我一连问了几次,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我当时不知,现在自然明白,回答我的不知道我问的是那些灌木。对他们来说,我们进入的的确是胡杨林地界,自然会给我肯定回答。
树木渐渐高大。车停了。我们走下车来,我环顾周围,到处是树,树上绿叶繁茂,和我以前见过的树林看不出什么区别。失望感陡然加强,掏出一支烟想点上,却瞥见停车处的树身上钉块“禁止吸烟”的牌子。抽烟是不成了,见旁边一棵枯树横卧。树身无皮,不知道死了多久。坐上去,再打量周围。我素来喜树,更喜树林,但因之前对胡杨林有太多设想,此刻居然没见一处与设想吻合,失望感也便自然。沈苇兄坐我身边,随意闲聊几句,然后说去胡杨林看看。
去胡杨林?难道这里不是胡杨林?我内心尴尬,平日总自诩如何如何热爱自然,却真还叫不出多少树名。我自己的解释是,知不知道一棵树的名字没什么要紧,要紧的是树林或大自然给我带来的气息。气息重要了,名字当然就不怎么重要。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树木,我还真就叫不出名字。胡杨林和许多树一样,名字是听说过的,但到了面前,却没办法辨识。张艺谋取景的树林之所以让我迷恋,是因为镜头里的落叶色彩,除了金黄还是金黄,也只在他的电影里,我才见到过那样成千上万的金黄落叶。那些叶子虽然在落下,但密集、疯狂,无法不令人眼花缭乱地感到震撼。每棵树有每棵树的名字,但每棵树的叶子到最后都只可能叫“落叶”。我喜欢的就是落叶,所以我不认识电影里的树名。我到这里才知道,那些抖下千万片金黄落叶的树,就叫胡杨。
但我没看见金黄色的落叶,所以我不愿意相信我此刻看到的就是胡杨。
树林中有条小路,路面铺着曲折走廊,走廊不是水泥,是一片片树木制作。沈苇兄带我步入走廊。越往里走,我终于渐感惊讶。胡杨林虽然叫林,却终究还不是想象中的密密树林。这里的每棵胡杨都保持住各自的距离,独自挺拔。西北地大少雨,眼中所见,每棵胡杨都站立在干裂无草的大地之上。“大树之下不长草。”这是罗马尼亚雕刻家布朗库西的名言。他说的“大树”虽指罗丹,但放在这里,却出奇地恰如其分。我没看见哪棵胡杨树下布满草叶。每棵胡杨就是每棵胡杨。但若仅仅如此,胡杨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我惊讶的,是这些胡杨不论如何千姿百态,每一棵都长得非常扭曲。我猜想,那一定是从它们发芽的那一天开始,西北的风便不断地吹刮它们。我忽然体会,很难有什么可以迎风生长,生长的却可以顺着风势,哪怕长成被风雕塑成的样子,也最终会是自己的样子。风是看不见的工匠,也当然手执看不见的工具。也可以说风的本身就是工具。这些胡杨被风塑造成型,让我最终看到的却是胡杨最内在的坚实。因为风只能塑造它,不能摧折它。不能被风摧折的,一定是最坚实的。所以这里的胡杨,没有哪棵不坚实。
这是我的感想吗?这又算什么感想!说它们坚实,也容易令没身临其境的人产生误解,以为我看见的胡杨根深叶茂、绿意缠身。事实却恰好相反,这里的无数棵胡杨周身没一片树叶,只是光秃秃的树身,树皮尽褪,四处开裂得像经过无穷岁月的刀削斧砍,展现出自己坚硬的动作,像人、像动物,尤其是伸出的枝桠,干枯、破裂,突然地小到末端。但不用多看,更不用猜测,那些枝桠一根根充满力度。越是枯瘦的,越是见出力度。它们的周身上下,都只能和语言中的“沧桑”对应。有哪种沧桑是虚弱无力的?此刻的天空高远、深蓝,那些胡杨的枝头就在深蓝下变得遒劲。我的惊讶也变成了惊骇。我走近我看见的最粗壮的那棵。在它脚下,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人给它取的名字。名字不重要,我还是这么以为。所以没必要写出来。我知道它叫胡杨,就已经够了。它浑身几乎没一块完整的树皮。甚至,在它十分之九的躯干上,我也找不到一块树皮。它是裸露的,在荒凉中,在旷古中,在无穷的时空中,它裸露出自身——苍劲、威严、犷悍、磅礴——这些词过分吗?一点也不。因为这是它活着的本质。或者说,它活着,就为了证明生命的强度。具有强度的生命不可能不磅礴。
看见它时我有过误会。我说,“它没有树皮。”沈苇兄笑了,走上来摸着一处像是灰尘落满的地方,说,“这就是树皮。树没有树皮会死的。”这一次,我没惭愧自己的无知。因为它显示的生命感对我本就是一种震骇。人无知才会震骇。我走近细看,那里果然是树皮。它只要这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让它证明自己,一点点就可以让它光秃的另外一面长出绿叶。它的另一面果然绿叶无数。沈苇兄继续告诉我,胡杨树的奇特还在于它能够同时长三种树叶,一种像柳叶、一种像枫叶、一种像杨叶。我觉得不可思议,三种形状的树叶居然可以集于一身。与其说是胡杨的奇妙,不如说是胡杨独具的奇迹。
一圈胡杨林走下来,没有哪棵胡杨不是如此。没有哪棵胡杨不值得细细描绘。一圈下来,我们重新回到车旁那棵横卧的树前。又一次坐在上面。我这次注意到了,这棵胡杨横卧于地,没有一处显得枯朽。胡杨就是如此,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我又想起电影里的千万落叶来,那些金黄令我心仪多年。我今天没看到它的金黄落叶。沈苇兄说要到十月,这里的树叶才片片变黄,再看不到一枚绿叶。只要一夜风吹,胡杨林便满地金黄了。我伸出手,像是无意地敲打这棵死去的树身。我忽然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如果今天就是满地金黄落叶,我怕我会忽略胡杨最粗粝的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