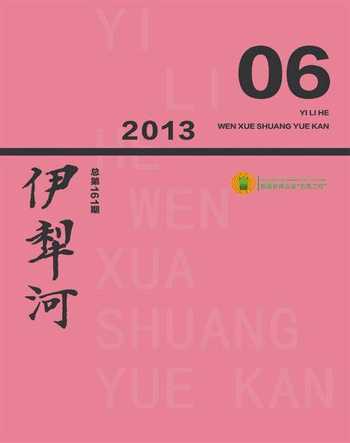看云
赵荔红
以前看过一幅漫画:一人住一大屋,床、橱柜、桌、椅子等,显得太过空荡,朝南一窗,可以看见原野、树木、天空,白云一朵朵从窗前飘过。过些天,那人将床搬进靠东墙的大橱柜,又陆续搬进桌椅什物,然后,在橱柜南壁上挂一幅画,画着原野、天空、树木、白云。他就落寞地呆在橱柜里。
当时我想:也许房间太大、他独住太孤单?将自己闭在橱柜里才安全?也许,从窗户看不见云了,他就给自己画幅云……
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看云识天气》,以科普的口吻说,看当晚的云,可预测次日是晴、多云或阴雨,其实懂了些知识,一样是判断不准。小孩子更惊讶于云的变化那样快而神奇,霞色那样富丽无法描摹,黑云闪电着实让人害怕、心中陡然升起神秘的敬畏。织女织云锦、妖怪神仙云来雾去的故事小孩子更欢喜。午休时候,不肯睡觉,巴巴盯着窗户,看云一朵朵从窗前飘过,变化出多少姿态,就想象那些云,是些什么动物、英雄、楼阁,天空正上演什么——小孩子的孤寂,多是如此打发、如此得到云的慰藉的。
稍稍长大些,就不稀罕云了。习见与知识充塞头脑,人往往熟视无睹。难得是始终对平凡的、渺小的、熟悉的东西充满敏感与好奇。世上的景象与事物皆是那样神奇,具有独特性,只是我们的心,渐渐麻木,失去了认知能力。云的遭遇也如此。
即便是这样想的,还是要抱怨,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冬春两季,的确是很少能见到小时候那样富丽的云彩。天空总是笼罩着灰色的、沉重的、可挤出水的抹布一般的云层,密匝匝将城市牢牢覆压。于是,城市的一切,楼房、街道、车辆、人的脸面,也都着上了一种灰调。一小片蓝天倏忽闪现,就闭合不见,像匆匆赶到车站的旅客,看着车门关上,火车迅速开走了。阳光极其费劲才能穿过层云,抖嚄嚄将一点点阳光意思,恩赐般撒播在城市。就是夜里强烈的灯光,也穿不破重云,只是在云层反复折射,城市便笼罩在一种奇异的蓝紫调中,远远看去,高楼大厦浮动在蓝紫雾气中,若隐若现,虚幻得很。若是一连几个月被密实的灰云笼罩,人的脸自然便带着灰气,透着阴郁神色。阴郁气质相互传递,演化成种种情绪:无聊、厌倦、愤怒、争斗……
于是有人将云画下来,挂在卧室,唤起记忆。有人,就跑到远方去看云。
我是跑到远方去的。西藏没到,看照片有那种镶了金边的大朵大朵云,心中羡慕。我最先去云南,称为“彩云之南”的地方。第一次去,坐在长途车里,一路看云,又在洱海边感受着潮湿、奇幻的云,回来后就写了《天边一朵云》,有一段是这样的:如果说往大理路上的云是姑娘清澈的眼睛鲜亮的唇,那洱海的云,就是呼风唤雨的巫师,是才情撒泼的诗人,是制造奇幻故事的戏剧大师。到洱海已是傍晚六点多,青灰湖面细细泛着波,几条小船随波起伏,浅灰的云散乱停在空中。但是起风了,苍山顶上聚拢起越来越厚的云,奶白的,渐渐转为烟灰色,灰色越深,云层越厚,终于,苍山不堪重负了,云漫溢出来了……东边天上的云如风扯下棉絮,随随便便抛掷,青灰的一小朵一小朵,小心迈步,转眼又模糊了边界,像是在薄蓝画布上随意涂抹数块淡墨,勾勒几道浅痕。西边天上的云从苍山延伸开去,越堆越厚,烟灰转深再深,浓重墨色,预示着一群精怪、一场暴雨的降临。某种可能蕴涵其中,神秘的、不可测度的,正悄悄发生。突然,在不可化解的厚重中,一道霞光刺破云层,坚强地侵蚀着黑云领地,浓重墨黑的中心,被霞光挖出一块鲜亮橘黄来,终将一整块黑云分解成无数朵。满天浮着镶金边的云朵,金色之内是白,然后才是烟灰直至中心的黑,大朵小朵,立体凸现在空中,好似泥的、雪的、大理石或重金属的雕塑。夜深下去,天空反亮起来,霞光铺满水面。八点过后,最后一点霞色消隐,天空湖水黑蓝,星星出场了……
后来又去过数次云南,每次看见的云都不一样。站在地上,看天上的云停停走走,有时心生恍惚:那天空竟是湖泊、大海,而云朵,是帆船、礁石、灯塔,我们悬在空中。我们是从云朵里出生的。死亡?死亡不过是让我们退隐到云里,自我消逝了,化作了水汽、颗粒,化作了云的一部分。
我去看云,追逐云,似乎去追寻自己。
所以,当沈苇邀我参加松拜草原诗会时,我就问:草原上的云怎么样?
从上海到松拜草原看云,要越过大别山脉、太行山脉、祁连山脉、天山山脉……从东海之滨一个蚂蚁人穿梭钢铁楼矗立的城市,飞越长江黄河,穿过伊犁河谷、特克斯河畔,到苏木拜河边看云……
车行进在伊宁时,我们就为天高云白大呼小叫,蒋晓华撇撇嘴说:到我们松拜,才知道什么叫蓝天、白云,太平常了。可是,车一过乌孙山,进入昭苏草原时,气温陡然下降。刚刚漂浮的一朵朵白云,奔涌着、聚集着,团在一起,云色转灰、变暗,瞬间,遮蔽了蓝天,左右前后,一大块厚重灰白棉垫子盖在头顶。草原延展到哪儿,棉垫子就铺展到哪儿,天空草原阔大、单一,隔着铁壳,依旧感觉云压迫得很低,透不过气来。车茫然向前,似要与云赛跑,却似乎永远无法从那种压迫、厚重中挣脱出来。三个多小时,只是这样。天越变越黑,竟下起雨来了,原野道路没入到灰白云气中,与天空相接,真个是“天苍苍、野茫茫”。我们的车在云雨中埋头挣扎,甲虫般摇摇晃晃,多么渺小啊……心生畏惧!如此厚重阔大的云被翻卷下来,将我们裹挟而去,身在何处啊?
到目的地,雨越发大了。暗暗祷告明日会是好天。晚饭设在草原上一个大毡房里。夜九点多,有人叫道:雨停了。我们就跑出毡房——
好大的风!从草原四面涌进怀,裹着雨后的潮气、青草味、香紫苏花甜中带涩的香、牛羊身上暖烘烘的膻气。那是大雨后草原平缓的吐纳。雨水顺枝桠、草坡、沟壑、根茎,潜到深处,接骨木的白色聚伞花,盛放的金黄油菜,细茎火红的野罂粟,蓝色鸢尾,所有未名的野花上、树叶上、草上,尚凝结着晶亮水滴,一只红色拖拉机缓缓进入黄泥小路,渐渐没进草原深处。辽阔的烟蓝暮色,在草原徐徐降下。收敛的,孤单的。这样神圣的静寂!我不敢迈步,怕撞破这层烟蓝之纱。风渐渐小了,花朵儿轻轻摇曳。牛羊离我们远远的,一只一只,成群而独立地站在凸起的草坡,仰头平视着我们(远方)。他们才是主人!我们突兀地闯入,如此惊异于他们的生活背景,以及这风景中未被言说的永恒:雨后的天空宁静、祥和,灰白的天幕露出一小片玉色,站在万花盛开的草坡,身后是青黛色乌孙山,几朵白云,如同刚刚吐出的蚕丝,附着在山顶,洁净地,轻柔地,一动不动地。
次日凌晨,与黄永中等人去看日出。天麻麻亮,吉普车盘旋在泥泞小路,草几乎没过车身。转过草坡,云天尚且灰蓝。突然,一道胭脂红抹在天山雪顶,如少女的绯红面颊,庄严、洁净、羞涩,两三分钟,由暗涩转透亮,灿烂的橘红是少女春情荡漾,随即变暗如同失望,渐渐褪隐,整个过程不过七八分钟。太阳藏在山后。大地蒙着瞌睡的雾霭。逆光下青黑白杨挺拔站立,如同伟岸而缄默的男子;高而黑的电线杆一根根相接着丈量草原,传达人的意愿。天放白了,草原睁开了双眼,天空呈明亮的青玉色,云从草原升起,大片烟蓝中泛出红色,青灰、玫瑰色、胭脂红、橘红、柠檬黄、金色,反复变奏着,一朵两朵逃逸出,呈粉色。南方洱海的云霞可用水墨表现,潮润、漶漫,堆垛一起时,蒸腾着浓重水汽。这里的朝霞鲜亮,云彩如聚集的万千颗粒,手一碰,就散碎了,须将油画颜料调和一起,反复涂抹,各种颜色相互叠加、渗透。
一条黯淡的黑泥小路切入草原深处,载着孤单的我们,爬上隆起的线条柔和的草坡,草坡之顶是乾隆平定准噶尔之乱的格登纪功碑,一座红亭子。太阳已从草原上、从山后、从云层深处跳出来,曙光汹涌,阳光所及,土地、草坡,草坡上的红亭子、摩托车、汽车、白色塔楼,全都发亮、泛红。碧蓝天空,云朵起伏、汹涌地变化出各样形状。云从草坡长出来,又低伏着大地,奔走、拉扯、延展到满满天空。北边的天透亮而高,云朵是轻盈的白;南边的天,厚厚云层灰白地压住天山山脉,只露出一线晶莹雪色,越低云越灰,顺着山势,连成一片,完全笼罩住山脚山腰,浅灰的云与草原尽头朦胧、灰黄的雾气相互漫漶,边界模糊。阔大、平整的松拜草原在眼前展开,在这样的七月,远处一大片收割后的土黄麦田,成片平整的哑黄油菜田,阳光一照,闪亮如金子,近处被齐齐站立如士兵的墨绿白杨分割出一块一块青绿麦田,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浮动着,如同即将散去的梦……苏木拜河静静流淌。站在格登碑边上,俯视整个大草原,中国的,哈萨克斯坦的,连成一片,被这条河流分割,苏木拜,意即平静流淌的小河,充满良好的愿望,如同这个宁静祥和的早晨。
回转路途,一再回首,来时的山道草坡斜向天空,才刚纯白的云,变成烟蓝,低低覆盖,聚成一圈如同菊花,若有所言地在花芯处透出一圈蓝天。车下到平缓处停下,一条小路曲折地切开平整麦田,香紫苏花、油菜花送来阵阵香气,远处隐隐显出房舍的红顶,路边一排白杨静默站立,云奔涌、聚集,又变得很厚,似乎一会又将下雨,太阳躲在云后,将万道银光射在草原、麦田,一个牧人骑马,赶一大群羊,拥挤在车道……
早晨十点半,我们出发去沙尔套山。天完全放晴了,阳光透亮,无遮无挡倾泻下来,晃得人睁不开眼。湛蓝天空,金灿灿的油菜,碧绿麦田,银色的雪山。明丽!鲜亮!呼吸都洁净。草原如此阔大,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似乎没走多远,白云一大朵一大朵扑向车窗,满满地向人面扑过来,又如千军万马呼啸而过,奔向不可知的未来。云天如此阔大,毡房、牛羊全都矮矮地趴在草地,只有一条赭黑泥路延展着,直通到天上,与云相接。爬到沙尔套山顶,站在敖包下,数千里祖国河山尽收眼底。起伏连绵的草坡,线条柔软,如沙丘堆积,看上去可用手捏起一小撮,上面似乎只是覆着薄薄一层青苔,青绿草皮似可随手揭去;一切都是肉肉的,在肉肉的草坡上,行走着肉肉的羊儿,蚕宝宝般卧在这里那里,毡房也肉肉地如白蘑菇生长。一切都是直接的、无遮挡的,如这正午的阳光,垂直、热烈、明亮,白云浮动,投下一大朵一大朵黑色云影,风从山谷来,云影随云转移,在草坡凹洼,在褶皱,在水流,在油菜花田里。
我多么想进入风景,化作其中的一朵云,水汽尘埃自然凝结,天然禀赋,在阔大天地间,随风漂移,自由聚散。我多么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渴望。二十四时之内,松拜的云竟有如许变化,色调与形态如此多样,充满丰富性与独特性,语言无法传达,画笔无法描摹,即便是当场摄下,也无法摄下与预测下一秒钟的改变。我只是观看、惊讶,只是感觉着流逝。昨日阴云下的惊怖,乌孙山上白云的轻灵,凌晨朝霞的鲜嫩,正午云影的转移,这一切,已然是无法弥补的流逝。世上可曾有过一模一样的树叶?我又怎能挽留、捕捉住毫无二致的云朵?“昨日之日不可留”,逝去的时日,不过是如那条黑泥小路,没进了草原深处……只有美、生命,在我心头盘旋,是永恒的忧愁。
回到上海,整理照片,写下文字,在我逼仄的蜗居,如牛反刍着干草。如同那个住在橱柜里的人,挂一幅有原野、天空、白云的画?我们都是,在不确定的事物里寻找确定性,在流逝中,试图凝固下某个瞬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回忆……车行进在法国南部,两边是柔和起伏的草坡麦田,青绿的葡萄树,金黄的向日葵,天上的云奔涌、变化,那样的云天,如同伊犁的松拜草原。我这样坐着车,一直看着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