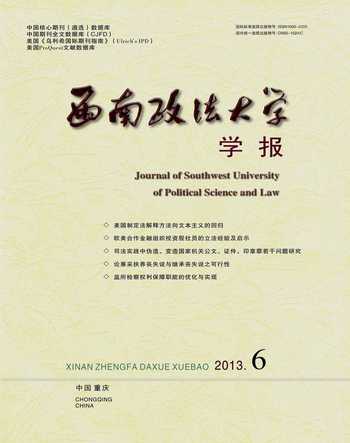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之反思与重构
摘要:认定是否成立具体的犯罪是定罪活动的核心任务。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的命题,在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悖理与纠葛。合理解决此等困扰,只有突破犯罪成立标准的传统认识,将集中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概括性情节因素置于犯罪构成之外独立评价,进而重新构建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即“犯罪构成+情节非显著轻微=犯罪成立”。
关键词:犯罪成立;法律标准;犯罪构成;情节
中图分类号:DF61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6.08
“在法学家眼中没有法律只有法理,在执法者手中没有法理只有法律。法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将法律的理性变成理性的法律交到执法者手中。”[1]就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而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定罪实践中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影响犯罪成立的一切因素最终都必须回归到法律的准绳内才是科学适用的根本保障。然而,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的命题,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悖理性。此等悖理性一方面损害了理论自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另一方面使得其在实践适用中的可遵循价值大打折扣。因此,深刻反思传统观念中的犯罪成立标准,紧扣刑法规范,合理建构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理论显得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讨论的前提: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之涵义界定科学构建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必须首先对其本身的涵义有着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里涉及两个基本概念:犯罪成立和法律标准。法律标准的涵义相对好把握一些,这里先做介绍。“标准”,即标尺和准绳的意思,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依据;而这里的标尺和准绳不是根据学界所构架的理论而确定的,而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故称“法律标准”。
认定是否成立犯罪是定罪的核心任务。我们知道,所谓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犯罪的形态和一罪与数罪的活动。具体言之,定罪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为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即罪与非罪的认定;第二个方面是确定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即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第三个方面是犯罪形态的确定,即在犯罪的性质和具体类型认定以后,进一步确定是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还是共同犯罪,等等;最后一个方面为罪数形态的确定,即认定行为所构成的罪数是一罪还是数罪[2]。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定罪的任务仅指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包括所谓“重罪”与“轻罪”的区别,后者属于量刑阶段的任务。而有学者却认为在定罪阶段“除了要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罪之外,还应当判断是属于基本构成,还是属于特别构成的犯罪。正确认定不同的构成层次,”以“准确适用不同幅度的法定刑”[2]232。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混淆了定罪和量刑的区别,详述如下:
一方面,定罪的核心任务是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该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程度,简言之,定罪是对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质的整体认定。无论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还是犯罪形态、罪数形态的确定都是围绕这一核心任务而展开的,详述如下:
其一,罪与非罪的认定是实现这一核心任务最明显的表现,此处不赘。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胡成胜: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对情节要素的独立评价其二,此罪与彼罪的选择是对行为所反映的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的相对具体的确定,它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以刑法规范存在具体的罪行规定为蓝本,而不能仅凭主观感觉擅断。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选择最能恰当说明其危害程度的罪名,此为量刑过程中最终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前提。换句话说,罪刑相适应不仅是对刑罚裁量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罪名选择的要求,只有在定罪时恰当地选择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的罪名才能在量刑中充分地做到罪刑相适应,此即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以刑定罪”理念的基本原理。
其三,犯罪形态和罪数形态的确定同样是围绕上述核心任务进行的。由于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共同犯罪以及数罪相对于单独犯一罪的既遂形态而言在反映社会危害性上具有非典型性,对于现实案件中预备、未遂、中止以及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帮助等不是十分明显或者直接反映社会危害性的具体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考察,决定着对此等具体行为究竟符不符合刑法规范所规定的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以及共同犯罪的判断,进而决定罪与非罪的认定。
其四,罪数形态的根本原理也是如此,基于上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针对错综复杂的行为事实,适用一个罪名能否将其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完全评价,决定着一罪还是数罪的判断。
实践中,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统一在罪与非罪的认定过程中。离开了此罪与彼罪的对比选择,没有犯罪形态的确定,是无法得出罪与非罪的结论的。一罪与数罪的认定同样如此,从基本原理上讲,同罪与非罪的原理一样,一罪与数罪的认定同样是对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总体考察;从具体认定来讲,行为究竟构成几个犯罪,最终还要落实到对其涉及的每一个犯罪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定罪的核心内容是罪与非罪的认定,定罪与犯罪成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定罪的标准即为犯罪成立的标准。
另一方面,量刑的核心任务是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严重程度已经整体确定并由此得出构成某犯罪的结论之前提下,具体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而判处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是对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量的具体衡量。而前述“重罪”与“轻罪”的区分,即在构成犯罪以及构成某种犯罪认定后进一步确定该犯罪的具体严重程度,显然属于量刑阶段的任务。
申言之,认为“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是定罪内容的观点往往是建立在将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分为独立的犯罪构成和派生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的。所谓独立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构成,相对于危害严重或危害较轻的犯罪构成,它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形态。”例如《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1款的规定,相对于第2款“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规定就是故意伤害罪独立的犯罪构成。所谓派生的犯罪构成,是指“以普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由于具有较重或较轻社会危害程度的情节而从普通的犯罪构成分化出来的犯罪构成。”派生的犯罪构成又可以分为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前者如《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款“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规定,后者如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后半段“情节较轻的”规定。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61)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基于此种划分,认为诸如《刑法》第233条、第234条所规定的犯罪,其罪行具有轻重层次之分,轻重层次不同的行为属于不同的罪行——基本罪行、重罪行和轻罪行[5],犯罪构成是对罪行特征的抽象描述因而也具有层次性。
然而,在笔者看来,罪行有轻重之分不假,但轻重不同的情形并非属于不同的罪行。因为罪行是此行为之所以为此行为的内在质的规定,具有独立品性,而诸如《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后半段“情节较轻的”情形,并不能独立说明什么问题,它需要依附在前半段“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上,因而不是独立的罪行。而所谓罪行的轻重层次实际上是在同一罪行质的规定性确定后进而确定其严重程度的具体量的内容,质和量是站在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考察,人为地将质和量割裂开来进而将同一事物分割为两个事物的做法是错误的。
果真如此的话,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即破坏犯罪构成的行为定型功能,犯罪构成是犯罪行为的法定类型性描述,它的内容应该具有确定性,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所谓派生的犯罪构成中诸如《刑法》第233条的“情节较轻”往往没有确定的内容,这里的“情节”泛指一切能够反映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事实,将其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势必使犯罪构成的内容变得不确定,因而破坏了犯罪构成的定型功能。
当然,上述主张在定罪阶段区分不同层次的“罪行”或者认定“派生的犯罪构成”的初衷是良好的,即为量刑阶段准确适用不同幅度的法定刑提供前提从而准确量刑。但是,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事与愿违。因为,不论是犯罪构成还是罪行都是对能够反映社会危害性的罪中行为事实各个方面的描述,但不包括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这是由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刑法规范的简约性决定的。而罪前情节和罪后情节由于同样能够说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在量刑中不得不考虑,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上述做法无形中将这两类情节排除在外,显然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定罪的内容不包括“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所谓“重罪”、“轻罪”实际上是量刑情节的内容,属于量刑的考察范畴。
澄清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涵义和内容,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的概念也就明确了,它指的是司法机关据以认定某行为罪与非罪的法定依据。
二、规范概览:犯罪成立标准之法律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对于罪与非罪的认定只能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标准而不是脱离法律规定依据理论定罪或者另寻其他依据。这里的法律特指刑事法律规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其他法律规范只能作为理解刑法规范的指导或者参考。例如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权威的地位,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母法,包括刑法规范在内的其他法律规范的理解与适用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不得与其相冲突;再比如,我国刑法分则许多条文关于罪状的规定多是采用空白罪状的描述方式,即在罪状中只规定某种犯罪行为,但其具体特征还需要参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确定,这些其他法律多是经济法规或者行政管理法规而不是刑法规范本身,如《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这里并没有写明什么是交通肇事行为,只能结合相关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才能确定。但这些相关的经济法规、行政管理法规本身并不能独立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只有与刑法规范相结合才能用于确定犯罪行为的内容。总而言之,就认定犯罪的标准而言,只能是刑法规范明文规定的内容。
我国刑法针对犯罪的认定在总则和分则中都做了规定,详述如下:
(一)总则规定的抽象与概括
刑法总则对各种犯罪均共同适用的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做了一般性规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犯罪的宏观把握而言,总则首先在第二章第1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犯罪的概念做了一般性界定,前半段(即“但书”以前的内容)从正面描述了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并归纳出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两个基本特征,后半段(即“但书”以后的内容)从反面强调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将实质上没有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程度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第二,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只有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实施的行为才是犯罪,并紧接着在第16条强调“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行为不是犯罪。
第三,就犯罪的主体方面而言,《刑法》第17条、第18条分别从刑事责任年龄和精神状况两个方面对犯罪一般主体的适格性做了界定。并在本章第四节单列一节就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范围和主体进行明确。
第四,就犯罪客观行为而言,《刑法》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行为,是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益的行为,从反面印证了犯罪行为的性质必然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又分别就犯罪行为的预备、未遂与中止等停止形态和共同犯罪等行为实施形态做了规定。这些规定是我们认定那些非典型性的具有复杂情形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依据。
(二)分则规定的增补与突出
刑法分则根据各种具体犯罪的特点又做了一些特殊规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的犯罪突出或者增补了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内容。例如,《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规定,以“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限,倘若不明知是上述赃物就不构成犯罪。又如,《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规定,强调以“故意”为限,而过失毁坏公私财物的不构成犯罪。再如,《刑法》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规定,要求构成此罪必须“以牟利为目的”,如果不是以牟利为目的实施上述行为则不构成此罪。上述立法例中前两种是为了说明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突出和强调,后一种是为了区别于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程度的一般行为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明显与之不同的类似犯罪行为而增补的主观要件内容。
第二,有的犯罪限制了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范围。例如,《刑法》第291条对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规定,将行为主体的范围限定为首要分子,从而缩小了刑法的打击面,体现了刑法的不得已性。除此之外,《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以及《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九章渎职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多数犯罪都对行为主体要件做了特殊规定,不符合该类型中某犯罪的特殊主体要求就不能构成该犯罪。
第三,有的犯罪突出了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1强调行为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引起某种严重后果的危险。比如,《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必须以“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为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构成本罪的客观要件必须具有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2强调必须使用法律规定的犯罪方法。例如,构成《刑法》第257条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必须采用暴力的方法,使用非暴力的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不构成本罪。3强调行为必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施。例如,《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第341条第2款的非法狩猎罪,构成这两种犯罪的行为必须分别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禁猎区、禁猎期实施。此外,刑法分则第十章对军人违反职责罪规定的多数罪名需以发生在战时或战场上为时空条件。
第四,有的犯罪突出了客体要件,即强调了犯罪对象的特定性或者达到一定的数额或数量。前者例如,《刑法》第365条传播淫秽物品罪等规定,其行为对象特指“具体描述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而“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以及“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淫秽物品或不视为淫秽物品,针对这些物品实施的传播行为不构成本罪。后者比如,《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的对象必须为“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刑法》第345条第1款、第2款规定的盗伐林木和滥伐林木罪都必须以“数量较大”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为客体要件的内容。
第五,有的犯罪采用概括的方式强调只有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的才能构成犯罪。例如,《刑法》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就是以“情节严重”作为罪与非罪的分界,《刑法》第255条规定的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以“情节恶劣”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等等[6]。
三、理性归纳:犯罪成立标准之规范模式说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是刑法规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种说法太过笼统,对于实践也没有任何意义,理论研究既不能脱离具体的法律规范也不能拘泥于此,其真正使命应该是从合理的角度剖析法律规范的内涵、归纳总结法律规范的内在规律,为执法者提供一套合理的具有可遵循性的正确适用法律的思维判断模式。
带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成立标准的上述规定,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特点:
(一)总体规定与具体规定相结合
我国刑法针对犯罪成立的标准既有总体规定又有具体规定,详解如下:
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是关于犯罪一般概念的规定,这一规定从正反两个角度界定了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根据《刑法》总则第101条的规定,《刑法》第13条的规定适用于分则的每一种犯罪。因此,该条关于犯罪一般概念的规定是认定罪与非罪的总标准,它对于分则所有犯罪的认定都具有指导意义。
犯罪概念是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抽象和概括,然而各种具体犯罪又是复杂多样的,具体犯罪不仅具有犯罪所共有的普遍性,而且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仅仅依据犯罪一般概念是无法区分罪与非罪的,还需要结合具体犯罪的特殊规定才能完成认定犯罪的任务。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也要求我们在认定犯罪时不能仅仅笼统地认定某行为是不是犯罪,还要具体地确定其构成什么犯罪。所以,我国刑法针对具体犯罪类型的成立条件又做了相对具体的规定。其中,出于刑法条文简约性的考虑,在立法技术上又将各种犯罪都共同适用的成立条件统一放在总则中作一般性地规定,如上文已经介绍的犯罪主观要件、主体要件、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中的一般情形或要素都在总则中规定,而具体犯罪成立所特有的条件要求则放在分则条文中描述或者强调,不同的犯罪所强调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这在上文已做归纳。
(二)定性规定与定量规定相结合
我国刑法对犯罪成立标准的规定采用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所谓定性规定,即规定行为这里的行为包括行为的主体、主观、客体和客观行为内容四个方面,而非仅指客观行为。的基本模型(类型),其目的是将此行为与彼行为相区分。所谓定量规定,是指规定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的规格,只有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达到某种规格要求才构成犯罪,没有达到该规格要求就不构成犯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规定模式在犯罪成立总标准和具体标准中都有所体现。
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一般概念的规定是对认定一切犯罪都具有指导意义的总标准。这一法定的犯罪一般概念就是采取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界定的:《刑法》第13条前半段即“但书”之前是对刑法范畴中行为模型的基本界定。其中“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对各种行为类型的抽象列举,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才可能是刑法中的犯罪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是对这些行为类型在刑法规范中的存在状态进行的概括描述,其目的是限定只有刑法分则条文做了类型性规定的行为才会是犯罪行为。《刑法》第13条后半段,“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一般规定,即只有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才认为是犯罪,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这里同时为社会危害性量的大小考量规定了可以把握的评价指标,这个指标就是“情节”,情节显著轻微就说明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不是显著轻微甚至严重的就说明社会危害性大。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成立具体标准的规定也是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详解如下:
定性规定,主要表现为《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犯罪构成四个方面要件的确定上,即一个行为要成立某种犯罪必须符合刑法关于该犯罪的主观要件、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客体要件的规定,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就不能构成该罪。因此,犯罪构成四个方面的要件是决定某行为之所以是此行为而不是彼行为的骨架,是该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本质属性,故称其为对行为的“定性”规定。
定量规定,则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罪状规定中,这里根据定量因素表述方式的不同,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数额(量)犯直接规定定量因素。所谓数额(量)犯,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要求以数额或者数量的多少作为具体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类型。例如,《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刑法》第345条第1款关于盗伐林木罪的规定;《刑法》第218条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据有学者统计,诸如此类的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共有大约130处[7]。
第二,部分结果犯与部分危险犯中间接规定定量因素。所谓结果犯,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以发生实害结果为基本形态的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类型。所谓危险犯,是指以行为具有引起发生某种实害结果的现实危险为基本形态的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类型。前者的定量规定例如,《刑法》第135条规定:“安全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除此之外,还有第114条中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第115条第1款中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第131条中的“造成严重后果”,第147条中的“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第161条中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等等。后者的定量规定比如:《刑法》第330条第1款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这些“重大”、“严重”、“较大”等字眼就是立法定量的表现,它提醒司法者在认定这类犯罪时不能仅凭是否有现实危险或者实害结果发生,还要考察这种现实危险或者实害结果是否达到了相应的量的要求。
第三,情节犯概括规定定量因素。情节犯是我国刑法分则中常见的一种犯罪类型,通常是指刑法分则明示以一定的严重程度的概括性情节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类型。例如,《刑法》第243条关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刑法》第261条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我国刑法分则具体犯罪中此种规定十分普遍,立法中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将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基本要件但其社会危害性还没有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程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因此,这些概括性情节是对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定量评价指标,其功能是从社会危害性大小方面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批判反思:犯罪成立传统标准之悖理性探明了刑法关于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规定的规律,并没有真正完成理论研究的使命,还需要据此进一步总结出一条简洁的思维路径供执法者参考。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参照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构建了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认为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惟一标准。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所谓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2]57并强调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件的简单相加式的总和,而是这些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各个要件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的犯罪构成。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不需要增加其他的条件,即可认定构成犯罪,因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被认为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2]58,表明了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只将构成要件符合性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构成要件理论不同。这种犯罪构成理论的构建反映了我国在犯罪成立标准上紧扣法律规定的整体思维模式,是对犯罪成立各个要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离开了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其他要件就无法确定或者变得毫无意义的这种不可分割的逻辑关联性的深刻认识。也即是说,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对犯罪成立的质和量的整体性统一评价,是对刑法关于犯罪进行定性加定量规定模式的理论抽象和总结。
然而,将犯罪成立的定性和定量因素全部纳入犯罪构成中考量,难免存在逻辑上的悖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区分与纠葛
传统犯罪成立理论一方面主张将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相区分,犯罪概念对罪与非罪区分只是起指导作用,具体犯罪的认定还要依靠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才是认定具体犯罪的惟一标准,即判断某具体行为是不是成立犯罪就在于看它符不符合犯罪构成,符合犯罪构成就是犯罪,不符合犯罪构成就不是犯罪;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形式上符合分则某一条款的规定,但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在判决宣告无罪时,“可在宣告无罪的法律文书中,同时引用《刑法》第13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2]54。这实际上是在犯罪构成之外另将犯罪概念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因而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标准”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
针对此种矛盾,有学者为了捍卫“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的不可动摇性,提出对犯罪构成进行实质解释从而排除犯罪概念在认定犯罪中的直接运用。例如,张明楷教授就主张“对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必须进行实质的解释,使犯罪构成的整体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6]在张明楷教授看来,使用极其轻微的暴力抢走他人1元钱的行为,原本就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构成抢劫罪,而不能认为该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然后以情节不严重(实际上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认定无罪[6]。张明楷教授所称的不符合犯罪构成实际上是指不符合抢劫罪的客观行为要件,即使用极其轻微的暴力抢走他人1元钱的行为不是抢劫行为。
然而,我认为这种对行为性质的否定是不恰当的。因为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抢劫罪的客观行为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中“暴力”、“胁迫”或者与暴力、胁迫具有相当性的其他方法是抢劫行为区别于抢夺等其它类似行为类型的关键,就抢劫行为类型而言,这里只是规定暴力方法,并没有强调暴力的程度,“极其轻微的暴力”同样具有暴力性质,不能因为暴力的程度轻微就否定其抢劫行为的性质(当然,更不能认为抢劫的数额少就不是抢劫行为)。按照这样的逻辑,使用极其严重的暴力强奸妇女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抢劫行为?抢夺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是否也可以说是抢劫行为?显然不可以,一行为之所以是此行为而不是彼行为是由其本身的内在质的规定性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其行为方式的轻重或者行为客体量的大小。
当然,张明楷教授观点的初衷是将具有刑法规范性质的抢劫行为与非刑法规范性质的“抢劫”行为纵向区分,而不是抢劫行为与其他行为类型的横向区分。但是,一方面其解决路径必然导致上述逻辑谬论,另一方面,即便是前者也已经不是抢劫行为类型与非抢劫行为类型的区分问题,而是抢劫犯罪与非罪的不同。因此,暴力的程度与数额的多少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危害性的量,可能会决定罪与非罪的性质,但决定不了行为本身的性质(即行为类型)。试问,倘若说使用极其轻微的暴力抢走他人1元钱的行为不是抢劫行为,那么使用何种程度的暴力抢走他人多少钱才算是抢劫行为?这个问题,恐怕张明楷教授自己也说不清楚。
张明楷教授主张维护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惟一标准的目的是排除司法恣意,但是同样一种行为模式时而是抢劫行为时而又不是抢劫行为,就使得刑法条文的文字丧失了其本来的含义,使刑法规范规定的行为模式变得摇摆不定、不可捉摸,进而使刑法规范的内容变得不确定,内容的不确定势必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确保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可预测性的要求,同时也留给司法人员更大的恣意空间。
(二)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的纠缠与混乱
传统犯罪成立标准的理论把所有影响犯罪成立的定性和定量因素全部放在犯罪构成框架中在逻辑上存在矛盾。通过上文对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成立条件规定的梳理我们知道,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是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式。将定性规定纳入犯罪构成中没有任何问题,具体的犯罪认定不仅是笼统地界定某行为是不是犯罪,还要更加明确地划分出是构成此罪还是构成彼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就需要有一个概括各种犯罪内在特殊本质的标准,而犯罪构成正是体现各种具体犯罪特殊本质的法律结构,是对各种犯罪内在特殊本质的法律归纳与抽象,因而犯罪构成承担着定性的功能。当然,这里的定性与定量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危害性的量,而是说犯罪构成侧重于对行为的定性考察。
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是能不能把所有的定量因素都放在犯罪构成中衡量。笔者认为不可以。
如上文所归纳,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量规定表现在总则的第13条但书部分以及分则的数额(量)犯、部分结果犯、部分危险犯和情节犯中。对于数额(量)犯、结果犯和危险犯由于其量的考量依据即“数额(量)”、“结果”、“危险”具有确定性,放在犯罪构成中很容易归位,例如数额(量)犯的数额、数量要求可以作为犯罪构成客体要件本文所讲的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指的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或者讲“犯罪行为(欲)影响或改变的犯罪对象的特征”。由于非本文研究重点,这里不加阐述,相关论述请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49-256的内容,结果犯和危险犯作为评价严重程度参考指标的结果和危险也可以视为对象状态改变的征表作为犯罪构成客体要件的内容。
但是,由于第13条但书和情节犯中作为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的评价指标的概括性情节在内容和功能上都具有不确定性,它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包含犯罪构成四个方面中反映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如果将情节放在犯罪构成中就存在一个归位的问题:由于情节内容的综合性特征,不可能将其具体作为某一个要件的内容;如果在每一个要件中都增加一个情节因素,即将犯罪构成要件都理解为开放性的因素,无疑意味着每一个犯罪构成要件都没有确定的内容,其结果一方面伤害了公民对自己行为及后果的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使犯罪构成理论丧失指导人们理解认定犯罪的刑法标准的参照性[3]。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还会不恰当地缩小处罚范围,因为情节的内容虽然来自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但最终对定罪起作用是对这些情节综合评价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单独功能,主观方面情节不严重可能其他三个方面有严重情节,如此等等,如果在每一个要件中都增加情节要素,势必导致因行为不符合某一个方面的情节要求而错误地出罪;如果将情节要件作为四要件之外独立的第五个要件,但这里的情节要件又没有自己独立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前四个方面的要件,因而在逻辑上又显得很尴尬。
对此,张明楷教授也有相关论述,张明楷教授认为:“‘情节严重不是属于犯罪构成某一个方面的要件,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件。正因为如此,可以认为,这种‘情节严重属于犯罪构成的综合性要件。”同时,张明楷教授又讲到:“‘情节严重作为构成要件,其特点是综合性,涉及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等内容,并非说它是独立于客观方面、主体与主观方面之外的某一个方面。”[8]225
然而,上述观点一方面主张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综合性的要件,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要件,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嫌,最终还是没能解决情节要求到底放在犯罪构成中的哪个位置的问题。
五、标准重构:情节要素在犯罪成立中的独立评价针对传统观点中以上两点逻辑矛盾,笔者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就是打破“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惟一标准”的传统认识,在犯罪构成之外另寻不确定的定量因素的理论归位,即将不确定的定量因素独立于犯罪构成之外单独评价。这样犯罪构成就不再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犯罪构成加上情节非显著轻微才是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借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犯罪构成+情节非显著轻微=犯罪成立”。
在这个公式中,犯罪构成和情节非显著轻微都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其中犯罪构成主要起行为定性(即行为类型)的作用,情节非显著轻微主要起社会危害性定量的作用;犯罪构成是第一位的条件,情节非显著轻微是第二位的条件,行为符合了犯罪构成才需进一步判断情节是不是显著轻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无需判断后者可直接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情节非显著轻微又具有两个层次的具体要求:第一层次的要求只是情节非显著轻微就足以认定为犯罪,这一层次适用于刑法分则罪名罪状的规定中没有进一步概括性情节要求的情形;第二个层次的要求是情节只是非显著轻微还不足以成立犯罪,还必须在此前提下进一步达到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够成立犯罪,这一层次的要求适用于刑法分则罪名罪状的规定中具有进一步概括性情节要求的情形。第二层次的要求与情节非显著轻微的总体要求并不存在冲突。因为情节的严重程度本身存在等级之分,在情节非显著轻微的前提下,至少可以将其分为轻微、较轻、一般、较重、严重五个等级,这五个等级都属于情节非显著轻微的范围。具体言之,第一个层次的情节要求是情节轻微以上(包括轻微)即可成立犯罪,第二个层次的情节要求是情节必须达到严重程度以上(包括严重)才可以成立犯罪。之所以会有这两个层次的差异,是因为行为本身的性质存在轻重程度的差别,刑法分则没有进一步情节要求的犯罪往往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比较严重或者已经通过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因素使其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因而只要是情节非显著轻微(或情节轻微以上)就可以成立犯罪;而刑法分则具有进一步情节要求的犯罪一般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较轻而又没有补强其严重程度的具体附加因素,所以概括性地强调情节必须达到严重或者恶劣的程度才可以成立犯罪。
与上述两个层次的情节要求相对应,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又可以具体分解为两种情形:对于刑法分则条文本身规定了诸如“情节严重”等概括性情节要求的,为“犯罪构成+情节严重=犯罪成立”①;对于刑法分则条文本身没有规定诸如“情节严重”等概括性情节要求的,为“犯罪构成+情节非显著轻微=犯罪成立”。这样设计犯罪成立的标准,一方面保证了犯罪构成内容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也确保了犯罪成立标准内在逻辑的融洽性[7]。JS
参考文献:
[1]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题记.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31-232.
[3]陈忠林.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共性比较[J].现代法学,2010,(1):169.
[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6.
[5]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67,277.
[6]高格.定罪与量刑(上册)[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88-91.
[7]高维俭.罪刑辩证及其知识拓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3.
[8]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6.
——与张明楷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