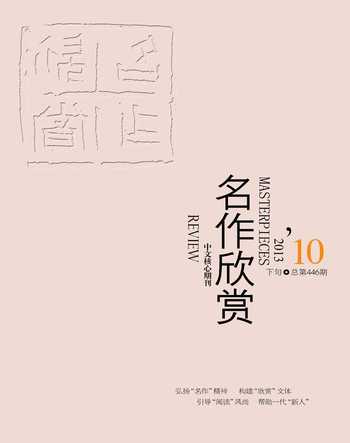推敲“位置”
摘 要:《又来了,爱情》是多丽丝·莱辛于七十六岁高龄时出版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年女主人公萨拉,讲述了她在筹措编排一场戏剧期间所经历的情感纠葛。本文将从空间研究的角度细读文本,挖掘、推敲小说中关于女主人公萨拉空间位置的有力的空间标识和位置符号,探索这些位置蕴含的隐喻之意。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空间隐喻 边缘
《又来了,爱情》(love, again, 1995)出版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 )已逾古稀之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女主人公萨拉也已经六十五岁。萨拉早年丧夫,守寡三十载,至今一双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并在他乡成家立业,经过多年的打拼,她在工作上小有成就,成为了青鸟剧团的团长。故事发生时,萨拉所在的剧团正在筹措编排一场戏剧,打算将刚刚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的法国女艺术家朱莉·韦龙的生平事迹、艺术成就和情感经历搬上舞台。在这部戏的创作过程中,萨拉沉寂了三十年的情感世界重新泛起了波澜,她先后与编剧史蒂芬、演员比尔和导演亨利发生了微妙的情感纠葛,久违的爱情给六十五岁的她带来的是焦虑、痛苦和对人生新的思索。
这部小说聚焦于六十五岁的萨拉,关注于迟暮之年老人的情感诉求。萨拉虽然是小说中的主角,却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主角。当今社会,老年人往往是被忽视的群体,已经完成生育和抚养后代责任的老年女性更是被遗忘于社会边缘的对象,展现老人的边缘地位可以说是《又来了,爱情》多重题旨中最重要的一个。作者采用了多种方式对这一主题加以呈现,最显著的就是对萨拉的心理刻画和对小说中人物之间对话的描写。上述两种方式都属于“宣言式”①的表达,可以直接向读者道出老年人的心声和想法,但“作为书写符号之集合的小说文本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②,这些因素被“自然地织入小说语言的流程”③,协助传达作者的旨意与小说的主题。
韩敏中曾撰文分析“坐在窗台上的简·爱”这一反复出现的形象在小说中的隐喻之意,笔者受其启发,对《又来了,爱情》中女主角萨拉所处的空间位置进行了分析,竟也发现了一位“窗台边的萨拉”。与简·爱相比,萨拉的空间位置更为多样化,除了窗台边,莎拉还反复出现于房间之中、床铺之上和镜子之前,于是“房间中的萨拉”“窗台边的萨拉”“床铺上的萨拉”和“镜子前的萨拉”形象便成为了有力的空间标识和隐喻符号。本文就将推敲《又来了,爱情》中萨拉的位置,探索这些位置蕴含的隐喻之意。
一、“自己的房间”中的萨拉
“自己的房间”是萨拉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位置之一,故事以萨拉出现在“自己的房间”为开端,也以她身处这一房间作结尾。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女子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才能确保在家庭社会中的独立地位,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④。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象征的是女性的独立。但在《又来了,爱情》的老年人语境下,“自己的房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丈夫的离世和子女的离家为萨拉腾出了足够的独立空间,她面临的并不是与家庭成员争夺生存和精神领地的困惑,而是一种寡居之下孤寂无依的困境。“自己的房间”特有的、可贵的“独立性”在六十五岁老人的语境下转化成了可怜、可怕的“孤立性”和“封闭性”,房间成了老年人的囚笼,将其隔绝于主流视域之外。
小说刚开始,萨拉的房间就是封闭的:“人们容易把这间寂静不通风的房间看作堆放杂物的储藏室。”⑤但随着女主角“拉开窗帘,猛地打开窗扉,走出房门”,读者的目光得以进入了这个“旧储物室”一探究竟。在屋中,笔者看到“堆放的杂物”只有两类:工作之物和回忆之物。“书桌上堆满了参考书籍和存放剪报资料的文件夹,在书桌的一边,放着几个叠起来的书架,几乎要触及天花板。”可见,工作之物不仅占据了很大的物理空间,还是帮助萨拉排遣老年孤寂、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而真正占据萨拉精神空间的则是回忆之物。“这套公寓储存着三十年来的回忆。长久居住过的房间就像布满碎石瓦砾的海滩,很难判断某个碎石来自何方。”这些回忆的碎石中,有萨拉用来回忆子女的塞尚的《狂欢节》等物件,也有用来回忆亡夫和祖父母的照片,就是没有关于她自己的部分。回忆之物帮我们勾勒出了这位六十五岁老人缺乏自我的精神境况。正是这个“封闭的”“回忆之屋”给萨拉套上了牢牢的精神枷锁。
不可忽视的是,小说的一开始,萨拉就表现出了要打扫房间,扔掉废物的冲动。笔者把这一冲动看作是囚笼中老人对自我救赎的渴望。萨拉开始“坐立不安”,她希望用行动摆脱回忆的纠缠,打破封闭性,改变自己孤寂的生活状态。这也为下文她走出房间去苦苦求索情感作了铺垫。
但萨拉并没有真正走出这间房,在小说的末尾,经历了一系列感情纠葛的她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萨拉的“越狱”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发现这间牢笼却发生了变化。“这间房间变了”,油漆匠刷白了米黄的墙,垃圾被清出,窗台、桌上、书架顶都干净了。房间的翻新使萨拉“变得轻松和自由了”,可见,时光的流逝是不可阻挡和逆转的,无论老人如何“坐立不安”地抗争,也无法返老还童,唯一的办法就是坦然地面对衰老,像萨拉一样,与自己的老年身份达成了一种和解。
小说的结尾,我们得知,萨拉的女儿带着孩子们到“萨拉的房间”过了圣诞节。整部小说都一直缺席的儿孙角色在最后出场。亲人进入“自己的房间”也就打破了老年囚笼的“封闭性”,缓和了老年生活的“孤寂性”,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老年人的精神困境提供了一剂解药。
二、萨拉的“窗”与“床”
“自己的房间”是处于小说开头与结尾的重要位置意象,小说的中间部分则是由“窗”与“床”这两个位置隐喻串联起来的。萨拉在戏剧的剧本撰写、角色选择和排练上演三个阶段,分别与接触到的三位男性角色,编剧史蒂芬、演员比尔和导演亨利发生了感情纠葛。笔者认为,这三段感情都出自于萨拉的臆想,其实是三段一厢情愿的单恋。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老年女人”一章中就曾提及老年女性的情欲诉求。“在这个紊乱时期,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比青春期还要不分明”?譾?訛,老年妇女“拥抱被爱的幻觉是正常的”?譿?訛。《又来了,爱情》中的萨拉就是一个沉溺于爱情和欲望幻想中的老年女性。而这幻想的主要场所,就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窗”与“床”。
上文提到,“房间”隐喻的就是边缘的、封闭的老年世界,房间之外才是年轻人的主流世界。萨拉渴望走出房间,在年轻人的世界中释放自己的情欲诉求。但显然,她很难迈出房间,很难打败时间,很难扭转自己的老年身份。于是满怀“越狱”渴望的萨拉只能站在窗台旁边。凭借“窗”这个唯一可以沟通外界的渠道,望向年轻人的主流世界。
当戏剧在贝尔河镇上演时,剧组成员需要在当地的旅馆落脚,作为团长,萨拉负责安排房间。当时萨拉正暗中迷恋着二十八岁的年轻演员比尔,于是她把自己的房间安排在比尔房间的阳台对面,一个绝佳的窥视角度。透过“窗”这个“隐喻的眼睛”?讀?訛,萨拉这个“可怜的老迈的幽灵”看见“有着柔滑、温暖、被阳光晒成棕色的躯体”的“比尔穿着游泳裤在阳台上晒太阳”。随着窥视的频率加大,老人的欲望也逐步升级,比尔成了她眼中“年轻的神”,“他知道自己是被大众膜拜的神”。在这一场景中,年老窥视者处在暗室之中,年轻的被窥视者处在阳光之下。老人渴望的眼睛是隐匿的,青年健美的身体是显现的。这里,老年人欲望的不可言说、与不可告人的特性被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窗”是萨拉观看欲望对象的位置,“床”则是萨拉放纵欲望想的位置。在“自己的房间”中,“床”在物理空间上紧挨着“窗”,在情感空间上紧挨着欲望。老人的睡眠稀少珍贵,但在床的位置上,萨拉却很少真正安睡,情欲熬煎下她醒则沉溺于幻想,睡则深陷于性梦。这就验证了波伏娃所说的“她在梦境里充满了性爱的幻
觉,甚至在醒的时候也受到困扰”?讁?訛。暗室中的“床”同样喻指老人欲望的不可言说,与“窗”一起构成了对老年人的边缘情欲诉求的重要隐喻。
三、镜子前的萨拉
透过“窗”和“床”我们看到了萨拉追求情欲对象时的一厢情愿,同样出自萨拉一厢情愿的幻想的还有她自己在镜子中的年轻形象。萨拉在镜前出现多次,读者不难发现镜中萨拉的形象在前几次时还十分年轻,“比实际年龄小二十岁”;但在最后一次时却十分衰老,“她已经老了十岁,她的头发现在夹杂着一些银丝,她已有了上年纪的人那种迟钝小心的表情”。究其原因,与多数评论者不同,笔者并不同意将这骤然而剧烈的衰老看作是三次爱情失败打击下的产物。
镜子本该反应萨拉的客观形象,但由于潜意识里对老年身份的排斥,她不能接受镜子的客观反映,于是发出了“我不会是镜子中的老太婆”的抗争。萨拉“完全不能从客观角度看问题”?輥?輮?訛,并产生了“奇特的双重感”?輥?輯?訛的幻觉。这面镜子其实映照出了老年人无法接受衰老事实的边缘心态。
小说结尾,我们发现经历了三段情感幻灭的萨拉不再自欺欺人,不再“恭维着自己,并删去无法恭维的部分”,而是第一次客观地直面镜子中的自己。可见,这三段感情纠葛看似是追爱而不得的失败,实则是萨拉步入老年道路上的一次洗礼,既帮助她梳理了自己的情感,又帮助她更好地平和了自己的欲望。这样看来真正照出萨拉衰老样貌的不是镜子,而是这三段感情经历。最后,在镜子这一位置前,萨拉接受了现实,终于真正“迈着优雅庄重的步子步入老年”。
至此,笔者已经逐一对《又来了,爱情》中四个萨拉反复出现的位置进行了推敲,对“自己的房间”中的萨拉、窗台边的萨拉、床铺上的萨拉和镜子前的萨拉这几个形象的隐喻意义进行了探究。可见,小说中的这些空间位置都不约而同地指涉了当今社会老年人的边缘地位。这一作品是正值晚年的人道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对当今社会关注老年人这一边缘群体的殷切呼唤。
①②③?讀?訛 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简·爱》,《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④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⑤ [英]多丽丝·莱辛:《又来了,爱情》,瞿世镜、杨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下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⑥⑦⑨⑩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舒小菲译,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第215页,第217页,第217页。
Rubenstein, Roberta. Feminism, Eros, and the Coming of Age[J].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2001(2): p19.http://muse.jhu.edu/journals/fro/summary/v022/22.2rubenstein.html.
作 者:李思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研究。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