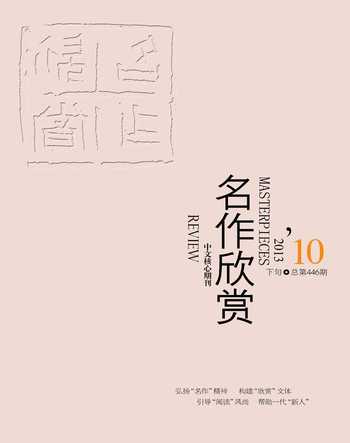《他们眼望上苍》:一曲黑人女性生存伦理演绎的赞歌
摘 要:本文对《他们眼望上苍》中美国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演绎过程进行了解读。该作品中的黑人女性生存伦理不仅包含了传统黑人女性的“隐忍式”生存,还包含了有尊严但没有自由的生存以及自由、平等但略带遗憾的生存。最出人意料且令人惊叹的是,主人公珍妮生存伦理发展的终点是当代正探讨着的生态、“天人合一”式的生存,从而从一个新视角再次证明了作家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的伟大。
关键词:《他们眼望上苍》 黑人女性 生存伦理
《他们眼望上苍》是美国黑人女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初版于1937年。出版后,受当时流行的黑人抗议文学的影响,该作品未能引起白人批评者的注意,同时还遭到了黑人批评者的冷落,它在湮没无闻中度过了数十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女性主义的迅速发展,它才被另一位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重新发掘。今天,它不仅已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更是20世纪美国文学和世界女性文学的经典,步入了所有主流大学的殿堂。该作品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并非仅是借20世纪末女性主义发展的东风(那只是诱因),或依靠爱丽丝·沃克对其的褒扬(她曾称“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为重要的书了”①),而主要是凭自身伟大的创作艺术,尤其是作家远超其生活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想。迄今,批评界已从许多视角对其展开了讨论,如从人物形象、自我、自传体、象征主义、民俗文化、宗教、黑人语言、生态女性等角度,然而如果我们借助另一个视角——文学伦理学批评来分析其人物的生存伦理,同样会产生令人惊喜的发现:该作品不仅描述了各种黑人女性的生存伦理,更是一部完美展现了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宏伟史诗。尤其是其超前地包含了生存伦理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生态生存,从而再次彰显了作家思想的伟大。下面让我们跟随作家的笔触,一步步地体验她作品中的美国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发展与演绎,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和感悟聂珍钊教授对文学所做的注解:“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②
一、隐忍式生存
隐忍式生存在美国黑人社会由来已久,它与美国南方长期的奴隶制有关。经过数百年发展,美国南方不仅形成了严格的黑人奴隶制度,还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伦理体系。这种制度与伦理体系在内战前的美国颇为盛行。内战后,它虽有所收敛,但还是以隐晦的方式又继续肆虐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影响下,林顿·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案”,黑人才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白人主流社会不仅一直坚持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政策,视黑人如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同时又视其为私家所有,对其任意剥削、虐待与蹂躏。相应地,美国黑人社会被迫适应了这样的格局,建立起了从属和隐忍的伦理规范,并形成了相应的伦理身份和意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照此生存,鲜有反抗,并将其世代相传。这是对黑人男性而言;对黑人女性,这种隐忍具有双重性质:她们既要忍受白人的歧视、虐待与糟蹋,又要忍受本族男性甚至自己丈夫的歧视与践踏。用赫斯顿小说中的话来描述,即“黑人女人在世界上是头骡子”(16)。
小说中,珍妮的祖母南妮及珍妮早期直到第一次婚姻期间的生存伦理都属这种传统的非人性的伦理,其主要特征是隐忍。“活下去”是“黑人,特别是又肩负着抚养孩子这一艰巨任务的黑人妇女的一切行动的前提”③。南妮是老一代黑奴,历经磨难,少时遭白人主人强暴,生下了珍妮的母亲(这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罪恶,许多黑人妇女都有相同的命运。珍妮的母亲也一样,珍妮是其母被学校老师强暴的结果)。南妮一生贫困,过着依附白人的生活。她带着小珍妮,祖孙相依为命地住在白人主人沃什伯恩家后院的一间小屋里。由于自己和女儿的共同遭遇,她不希望同样的灾难在珍妮身上重演。珍妮十六岁时,南妮看到穷小子泰勒吻了她一下。这让她大为震惊,勾起了悲痛的回忆。于是,她激动地宣称:“你是一个女人了,我要看到你马上结婚。”(14)她为珍妮选择的是同为黑人的中年富裕农民洛根·吉利克斯,选择的标准很简单:洛根有六十亩地,路边还有大房子,可以保证珍妮衣食无忧。对南妮而言,生活就是物质生存,其他的一切都可有可无。为了说服珍妮接受这桩年龄悬殊的婚姻,南妮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就我所知道的,白人是一切的主宰,也许在远处海洋中的什么地方黑人在掌权,但我们没看见,不知道。白人扔下担子叫黑人男人去挑,他挑了起来,因为不挑不行,可他挑不走,把担子交给了家里的女人。”(16)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妮对“黑人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的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悲惨遭遇”有深刻认识,但她又认为“生活中的等级制度和不公平是普遍的,不可逆转的”,她的“这种对自我身份根深蒂固的认同”使她没有“改变自我生存空间的可能”④。换言之,她认可传统黑人妇女的生存伦理观,其生活的目标就是“活着”,是隐忍式生存伦理的典型代表。在外祖母声泪俱下的劝说下,珍妮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场包办婚姻。然而,南妮的这种伦理意识注定不会在珍妮身上持久。十六岁时的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让她领悟到了什么是理想的婚姻:“她看见一只带着花粉的蜜蜂进入了一朵花的圣堂,成千的姊妹花萼躬身迎接这爱的拥抱,梨树从根到最细小的枝桠狂喜地战栗,凝聚在每一个花朵中,处处翻腾着喜悦。原来这就是婚姻!她是被召唤来观看一种启示的。”(13)这成为她内心未来婚姻的参考,成为支撑她未来生活前进的精神动力。在这种比照下,她对洛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我希望结婚给我甜蜜的东西,就像坐在梨树下遐想时那样”(23),然而现实却是“有的人永远不招人爱,洛根就是其中的一个”(26)。不久,婚后的不平等生活进一步加剧了她的不满:洛根开始用不好听的言语跟她说话,要她劈柴,到谷仓帮忙,接着又给她买骡子,对她说:“我要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33)随着洛根对珍妮的拥有和控制欲越来越强烈,珍妮的反抗与摆脱意识亦愈来愈强烈,这种反抗同时还伴随着一个人的出现:聪明伶俐、具有雄心壮志的乔·斯塔克斯。用小说的原话,当时的情景是“春天来到了她心头,大路上走来了乔·斯塔克斯”(31)。终于有一天,在跟洛根吵了一架,洛根说了“我要拿把斧子劈了你”(34)后,她决定离开他,“解开围裙,扔在路边矮树丛上……从现在起直到死去,她的一切将洒满花粉与春光。她的花上会有一只蜜蜂。她从前的想法又触手可及了”。(35)扔掉围裙意味着她“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实现之旅的开始”⑤,意味着她摆脱了人生的“骡子”阶段。她跟乔一起私奔了,走向了第二次婚姻。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珍妮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她抛弃了旧的、老一代黑人妇女的生存伦理,做出了新的伦理选择,开启了人生新阶段。
二、有尊严但无自由的生存
离开洛根,珍妮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与乔一起到了伊顿维尔小镇。不能不承认,乔是个有魄力而且能干的男人。他一到小镇就开始营建新生活:买地,开商店,造邮局,还号召全镇公民召开会议决定未来发展。由于他的才干,他很快就被推举为镇长,成了当地的大人物,而珍妮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镇长夫人”,过上了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但在这荣华的背后,珍妮并没有看到她理想的婚姻。
在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婚姻中,她的生存状况可以用“体面但没有自由”来概括。乔虽然不像洛根那样把珍妮当作会劳动的骡子,但在控制她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将她的活动限制在家里,不许她四处走动。乔就任镇长时,曾有人提议让珍妮发言,但当即遭到了乔的强烈否定:“感谢大家的夸奖,不过我的妻子不会演讲。我不是因为这个娶她的。她是个女人,她的位置在家庭里。”(46)碍于丈夫情面,珍妮不得不以尴尬的微笑将其敷衍过去。即便珍妮到他的店里帮忙,他也总是要求她用头巾把头发裹起来,因为她的头发散发着独特的女性魅力,流淌着性感,但这种感觉只属于他,不能与他人分享。乔的商店是镇上人们的常聚之地,附近的居民常在这里交流聊天,畅所欲言。珍妮是开朗女性,渴望融入社会,不爱把自己锁在屋里,可每每此时乔都借故将她支开,不仅不让她说话,连听的权力都加以剥夺。珍妮想去参加一头骡子的葬礼,乔听后惊讶地说:“人挨人人挤人的,这帮人还一点不懂礼貌……镇长的妻子就是不一样。你不许和这帮粗俗的人一起去。”(63)从他的表现和话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的男权伦理环境:“社会从意识形态上规范了对黑人妇女的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到了权威的程度,而人们都对此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⑥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珍妮渐渐明白了她身处的严酷的社会环境。面对这种比洛根还强烈的控制,骨子里依旧倔强的她选择了沉默,决定忍耐。她的忍耐力是惊人的,甚至超乎常人的标准,连周围的人都有时会为她鸣不平:“她可真不怎么说话,她出了点错,他那个大喊大叫劲儿真有点让人无法容忍。”(53)珍妮不仅没有自由,有时还要忍受丈夫的体罚,乔会因“某天一顿饭做得不够好而在厨房里扇她一阵嘴巴”。对这种身体的虐待,她的反应是“此情此景多了……她咬紧牙关逐渐学会了缄默”(76)。在她与乔婚姻的最后几年,她已与先前大不一样了,“岁月使争斗之心从珍妮脸上完全消失了,有一段时间她以为也从她的灵魂中消失了。不论乔做了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说”(82)。小说描述了她当时的思想状态,“三十五岁是两个十七岁了,一切都完全不同了”,妥协与屈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事,因为这使她顺从地接受一切,到了这种地步,她好像土地一样漠然地接受一切。无论是尿液还是香水,土地同样无动于衷地把它们吸收掉”(83)。但珍妮的这种向男权社会的妥协不能视为小说的失败,反而是她形象的进一步丰满,因为正是这种妥协才表明主人公是一个现实的、成熟的人,而不是一个依旧幼稚、任性,只会反抗而无法过正常生活的社会异类或精神病患者。
但是,一个天性追求自由幸福,具有固执、叛逆性格的人在第二次婚姻期间就突然变得唯唯诺诺、毫无抗拒,这可能吗?读者不免质疑。对此质疑,小说给出了最佳,也是最合乎情理的回答:珍妮只“是大路上的车辙,内心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但总被车轮死死地压着”(82)。实际上,在与乔长达二十年的婚姻中,她一直在时断时续地抗争,只是大多数场合里比较柔和。如乔瞧不起妇女,对珍妮直白地说:“得有人去替女人、孩子、鸡和牛动脑筋,老天,他们简直不动脑筋。”珍妮忍不住反驳说:“我也知道些事情,而且女人有的时候也动脑筋。”(76)对乔的大男子主义,她时常会表达不屑:上帝“对我说他没有这么造你们,可你们都变得这么聪明,这使他多么吃惊。如果你们终于发现,你们对我们的了解连你们自以为有的一半都不到时,你们会多么吃惊。当你们只有女人和小鸡要对付时,把自己装作万能的上帝是多么容易”(80)。但有时珍妮的反抗也很激烈,甚至因此要了乔的命。在他们婚姻的末期,在一次激烈的言语冲突后,一向高高在上的乔终于轰然倒下:那是在他的商店,顾客等着要烟草,珍妮正帮忙切的时候。乔嫌她切得慢,走过来故意让她当众出丑地喊道:“老天!一个女人在店里一直呆到和玛土撒拉一样的年纪,可是连切块板烟这样的小事都还做不来!别站在那儿冲我转你的突眼珠,看你屁股上的肉都快垂到膝盖弯上了。”(84)众人哄堂大笑,忍无可忍之下,珍妮终于爆发了:“我不再是个年轻姑娘了,可我也不是个老太婆……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个女人……这可比你强多了……哼!说我显老!你扯下裤子看看就知道到了更年期啦!”(85)这番话对乔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他无法承受:“她在众男人面前打掉了他空空的盔甲,他们笑了,而且还将继续笑下去。”(86)虽然他使出全身力气打了珍妮,并将其从店里赶走。但自此,乔很快就因肾衰死去。对此,盖茨认为“珍妮摧毁了乔的男性权威……用嘴巴杀死了他”⑦。从当时的男权伦理环境来看,这种观点是合乎逻辑的。
乔死后,珍妮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她把乔给她戴的“束缚”——她的头巾付之一炬,把浓密、性感的头发放了下来,展现给世人,突然她发现“年轻的自己已经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漂亮的妇人”(95)。她的容貌和成熟引来了众多追求者,但她不急于再婚。她的生存伦理已发生改变,天性正在回归。她珍惜新获得的自由,暗下决心:除非新的婚姻能带给她自由,否则宁可独身。在这种新的生存伦理意识中,她开始了悄悄的等待,开始了她新伦理规范的践行。
三、平等、自由但仍有缺憾的生存
珍妮等来的第三任丈夫是维基伯·伍兹。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珍妮就感到这位小她十二岁的男子与前两位截然不同:伍兹请她下棋。对乔和洛根而言,下棋是男人的专利。因而,珍妮虽遗憾地坦诚自己不会,但内心是十分感动的。当伍兹进一步主动提出教她时,她的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恰如吃了“甜点心”一样(这正是伍兹在小说中的绰号,此处体现出来的作家的艺术匠心令人赞叹)。接下来的事情珍妮更感动了,完全是从未经历和未曾想象的:他们一起钓鱼,一起挖蚯蚓,一起看电影,一起野炊等,这些带着童年浪漫的小事,令她心花怒放。与乔和洛根截然相反,甜点心鼓励她说话,而不愿她沉默。在他的鼓励下,珍妮的语言焕发了青春,用她自己的话说:“他重新又教会我少女的语言了。”(124)她不仅话多了起来,还学会了调侃。如一次甜点心说最近收入还行,干了四天活,工钱装在口袋了,她笑道:“那么咱们这儿来了个阔人了,这星期买旅客列车还是战舰?”甜点心道:“你要哪个?全在你了。”(109)从这里可以看出珍妮跟甜点心在一起的自由与快乐。甜点心不仅让她愉快地生活,还让她自主地生活,这正是珍妮决定嫁给他的原因,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年龄差异和身份差异:珍妮大他十二岁,是镇长遗孀,受人尊敬,还有商店、房产等经济基础,而甜点心只是季节工,朝不保夕,穷困潦倒。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结合无疑要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对种种流言蜚语。
但珍妮决定嫁给甜点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包含了婚后的各种可能。这从她与菲奥比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虽说甜点心不是个囚犯,他可是一文不名。你不怕他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吗……”“他还从来没向我开口要过一个子儿呢,而且假如他爱财,他和我们大家也没有什么不同……结婚总是使人产生变化,有的时候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存在的肮脏卑鄙的一切都显露了出来。这你是知道的,也许甜点心也会变成这样,也许不会,反正我做好了准备,愿意试他一试……我一和他结婚,大家就会做比较了,所以我们要到别的一个地方去,按甜点心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我们这不是做买卖,不追求金钱和名位,我们这是爱情的追求。我按外祖母的方式生活过了,现在我打算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了。”(122-123)
婚后,他们离开了小镇,一起到了沼泽地。这里,民风淳朴,他们过着田园式的“诗意”的生活。沼泽地美丽的自然环境是净化人心灵的灵丹妙药。在广袤的原野里,所有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压抑的社会氛围、小镇一切肮脏的习俗以及珍妮心中还留有的女性自卑,全部一扫而光、烟消云散。像其他男人一样,珍妮白天穿着粗糙的工作服和笨重的鞋与甜点心在田里愉快地摘豆;晚上,他们一起回来做饭。饭后,他们与其他季节工一道唱歌、跳舞、谈笑。这里,穿着工装裤的她“拥有了自己的声音,获得了与前两次婚姻不同的地位,也终于找到了自我”⑧。这里,他们的生活虽简单辛苦,但却情趣盎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她不再是以前那个沉默的珍妮了,她不仅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甚至自己都能够讲了”(144)。她还学会了打枪,枪法比甜点心还好。
但小说并没有就此结束,她的婚后生活还在延续。随着时间流逝,正如她早先预料的那样,婚后的甜点心可能会变,她的预想应验了。甜点心的大男子主义开始显露,尽管他知道珍妮爱他,不会做不检点的事情,但为了脸面,还是因特纳太太要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珍妮的事情打了她一顿,并让周围所有人知道:“他是一家之主,他能打她,就再度证明她属于他。”(158)他还颇无廉耻地对别人说:“我要上哪珍妮就到哪,她就是这样一个妻子,我就爱她这一点。”(159)然而,在甜点心逐渐显露出与乔和洛根并无二致的劣行之时,珍妮选择的却是妥协:她没有反抗,反而顺从地接受了。
小说的这种安排令人扼腕,但却具有合理的一面——这正是珍妮思想日臻成熟的表现。经过前两次婚姻和甜点心的逐渐变化,珍妮已经意识到了男权中心是当时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反抗并不能取得效果。与其反抗,不如以顺从的方式主动塑造出一个令她满意的统治者,从而创造出自己可以接受的婚姻局面。对这种妥协,米勒将其解读为“创造性的顺从”⑨,应该说是颇有道理的。
珍妮采取的妥协对策一方面说明了她思想的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她对甜点心的真挚的爱:她愿意为了爱情而牺牲。尽管如此,她的爱情也没有持续长久。很快,沼泽地经受了一场由飓风引起的洪水,为救珍妮,甜点心染上了狂犬病,最终精神错乱,用枪指着珍妮,准备打死她。为了自卫,珍妮不得不举枪。两人同时扣动了扳机,不幸的是甜点心的枪没打中,而珍妮的枪要了他的命。就这样,珍妮被送上了当地法庭。出人意料的是,她的故事感动了全体陪审团,法庭接受了她的陈述,最终宣布她无罪开释。尽管如此,甜点心的死还是给她带来了巨大悲痛。甜点心曾对她显示大男子主义,并用枪威胁她的生命,但她并未因此而指责他。她对他的爱是深沉的,她对朋友们说,爱人的肉体虽离开了,但她对他的思念永远不会停止,“只要她自己尚能感觉、思考,他就永远不会死”(209)。甜点心死后,珍妮决心在对甜点心的思念中继续生存,而且更好地生存,尽情地享受他为她带来的“多彩的生活”(209)。
四、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
甜点心虽然去世了,但珍妮的生存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少女时代就有的朴素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伦理,此时没有了任何外界束缚,她终于可以不再“按甜点心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而是按自己内心的要求,按自然的方式开始生活了。她这一阶段的生存伦理可以用“自然”来概括,其特征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超越了白人/黑人的区分,打破了男性/女性的界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消除了人/自然的对立,充分融入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一贯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
甜点心死后,珍妮被推上了法庭。当时参加审判的法官、陪审员、律师、警长、法警等权势人物都是白人,旁听者中有八到十人是白人妇女,其他的都是来自附近的黑人。他们都是来替甜点心抱不平的,带着恨不得把珍妮碎尸万段的气势。珍妮知道黑人决定不了她的命运,决定她命运的是白人法官和陪审团。然而,珍妮并没有因此对黑人表示怨恨,也没有对白人表示恭维:“她没有向任何人乞求,她就坐在那里讲述着,说完了就闭上了嘴。”(202)此时的珍妮已经超越了黑人/白人的概念,无论对谁,她都会说同样的话。她尊重的只有事实,她唯一想让众人明白的是她和甜点心的真挚的爱情以及当时的现场情形:“她惧怕的不是死,而是误解。”(203)当法庭宣布她无罪释放时,“法官和台上的人都和她一起笑,和她握手。白人妇女流着眼泪像保护墙似的站在她周围,而黑人则垂着头蹒跚着走了出去……在这一天剩下的那一点点时间里她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去拜访那些理解她感情的厚道的白人朋友们,向他们表示感谢”(203)。此时的珍妮,她的一切表现都是那么超然,她对人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肤色:白人中有坏人,但也有许多主持正义的人、厚道的人、通情达理的人,所以她要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而黑人中也不都是好人,他们中有许多邪恶的人。黑人所持的偏见不仅不比白人少,甚至更强烈——在
案情真相大白后,许多黑人还在她背后议论说:“黑女人可以杀死她们想杀的一切男人,不过你最好别杀她们,不然白人肯定会绞死你。”(204)对这些黑人,珍妮的做法更显示了她超脱的心态:她给他们带口信,并通过他们告诉所有人关于甜点心的葬礼。结果,“下葬那天他们带着满脸羞愧与歉意来参加葬礼,他们……都来坐珍妮租好的十辆汽车,坐不下他们还自己租了车加入葬礼的行列”(205)。借此,她成功地赢得了沼泽地人们的理解与尊敬。
在对男/女性别的超越上,甜点心死后珍妮的表现也更为抢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为甜点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上“乐队奏着哀乐,甜点心像古埃及的法老般来到了自己的墓地”,而就在这样一个极为庄严肃穆的场合,她“没有穿戴上昂贵的长连衣裙和面纱,她就穿着工作服去的”(205)。虽然珍妮以前跟甜点心在一起劳动时就穿工作服,表现了她男女平等的意识,但这次的工作服出场无疑表明她的这种意识已根植于她的内心,根植于她今后的生活了。她要借此让甜点心“看到”,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给她带来的变化是何等巨大,并且这些变化不会消失,它们将伴随她的余生,直至永恒。借助这种“可视化的声音”,珍妮“不仅成为自己生活的观众,更成了自己生活的真正参与者”⑩。
在对人/自然的理解上,珍妮也取得了比以前更为升华的认识。很早以前她就有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少女时代她曾躺在梨树下,感叹道:“能做一棵开花的梨树——或随便什么开花的树多好啊!”(13)后来她参加骡子的葬礼,再后来决定离开小镇到大沼泽地居住等。而现在,甜点心虽然离去了,但她正如甜点心的姓伍兹(Woods:树林)所预示的那样,已经成为一棵独立的、成熟的、历经风雨磨砺的大树。不仅如此,她还决心按照伍兹生前的心愿,让自己永远活在Woods中,活在他身边。这样一幅完美的生态图景,读者通过小说结尾的描述可以清晰看到:“菜籽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使她想起甜点心,因为他老是在种这种那的……现在她回家了,她打算种下种子,纪念甜点心……这时甜点心来了,在她身旁欢快地跳跃着……飞出窗口,停歇在松树尖上。甜点心身披阳光。”(207-209)由此可见,此时的她在思想上已经真正成为珍妮·伍兹(Woods),自然生存,“天人合一”是她生活的新抉择。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甜点心的死对珍妮是更大的解放,去除了她自由生存中的最后遗憾。之后,她不仅更自由了,而且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真正地践行她十六岁时在梨树下感受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虽然她又孤身一人了,但却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类生存伦理的最高境界:自然的、生态的生存。这种生存,不仅在当时社会极为难得,即便在今天,在众多的已婚男女或单身男女的生存中亦极为罕见。诚如程锡麟教授所言,“对于一位出生在19世纪、主要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黑人女作家,在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创作出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今天的我们已
经意识到了作家思想的伟大,而未来将会证明,她的伟大将不仅仅局限于现在:她为黑人女性指出的生存之路,就像茫茫大海上的灯塔,将指引着包括黑人女性在内的全人类的女性,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语言、不分年龄,继续前行。
① [美]左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内容提要。本文许多引文皆出自该书,后仅标页码,不再逐一注出。
②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第40页。
③ 修树新:《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生存伦理——以〈秀拉〉和〈宠儿〉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9页。
④ 刘珍兰:《〈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的自我实现》,《译林(学术版)》2012年第2期,第6页。
⑤ 李梅、付海艳:《艰难的自我实现之旅——评〈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女性物化现象》,《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2页。
⑥ Collins, Patricia Hill, ed.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C]. New York: Routledge, 2000:5.
⑦ Gates, Henry Louis Jr.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192.
⑧ 田蓉:《〈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的婚姻及其独立》,《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51页。
⑨ Miller, S. E. “‘Some Other Way to Try: From Defiance to Creative Submission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J].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2004 (Fall):74-95.
⑩ Clarke, Deborah. “‘The porch couldnt talk for looking: Voice and Vision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4,2001:599-613.
程锡麟:《赫斯顿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北京市教委2013年度“现代美国文学资源包”二期拓展项目资助
作 者:滕学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心成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