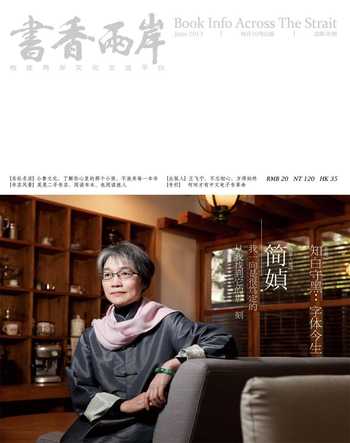书香两岸选书 · 主题阅读
人间气候
5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廈门暴雨。水漫全城,岛内多个路段严重积水。除了交通干道,地下车库成为积水的另一重灾区。有民众无奈地说:“马路由于堵车成了停车场,停车场就变成游泳池了。”
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柳中明在《台湾环境变迁解密:改变未来的12堂课》的序言中说:“气候是人为判断的。譬如有人说:一辈子没遇过这么严重的水灾,但说话的人最多也才100岁左右!或是说:仪器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豪雨,但是气象科学仪器发展还不到150年!那么如果说:有文字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灾——但是有系统的文字记录,不过五六千年。……无论地球是否将再进入另一个冰期,无论人类物种是否在万年后消失,我们所担心的都是:未来我活着的时候,以及我孩子与孙子活着的时候,气候会是如何?相对地,当然我们会想:过去我与我父亲活过的百年间,气候是否与现在不同?没错,有人说地球古气候,有人谈气候影响朝代兴亡……但是人只关心前后百年的气候,这就是‘人间气候。”《台湾环境变迁解密》整理了柳中明过去二十年的观察,多为发表于报刊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在全球各地发生气象异常现象时所提出的专业分析,并与台湾地区的情况紧扣,提出与气候相关各个层面的环境政策的建言。
与时间相对应的,人们对于天候的感受,其实也只局限于自己生活和活动的地区。从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到冰川加速融化的格陵兰岛,干旱、暴雨、飓风、物种消亡、环境难民……这些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边),就都只是电视/电脑屏幕上的他者的命运。
媒体资讯是一种很吊诡的存在,它使世人之间的“可视”距离拉近,但也让人在旁观他人之痛苦时变得麻木。但怀抱新闻理想的媒体工作者,始终相信传播地球角落的真相的重要性。为《Time》、《Fortune》、《The Atlantic Monthly》和《Salon》等杂志报导发展中国家新闻的Stephan Faris,为了撰写《大迁移》而展开调查之旅。他不远万里,走访了非洲难民营、美洲边陲小镇、地中海岛屿、欧洲城市、北极观测站、亚马逊殖民地、墨西哥湾滨海城镇、纳帕山谷葡萄园,从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到北极圈冰川融化,从佛罗里达珊瑚礁群死亡到沿海岛城深陷萧条,从卡特里娜风灾到新奥尔良保险费用激增,从意大利海龟生态恶化到发达国家移民风潮……他藉由对过去、现在、未来事件的深入探访,以及对气候灾难现场的第一手报导,揭示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超越环境与天灾,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保险业、酿酒业、航运业、甚至公共卫生、地方选举等,都和气候变化脱不了关系。
Stephan Faris形容,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有如饥饿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如果有个快饿死的人死于肺结核,或是在偷面包果腹时被打死,没有人会说这个人是饿死的,但是饥饿的确是他死因的一部分。全球变暖本身不会发动战争与叛乱,甚至是种族大屠杀;“全球变暖的效应就是降低社会的承受力,”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环境与冲突相关性长达20年的政治科学家Thomas F.Homer-Dixon说,“它使社会无力应对冲击与危难,包括大规模暴力事件。”
目前世界上关于气候变迁的“结论”都集中于“全球变暖”,而对此的研究大多以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主要着眼点,这也是上至各国政府间,下至企业、媒体、公众人物所热衷谈论的“后石油时代”、“低碳”等词语风行的背景。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系教授Richard S. Lindzen声称,科学界对地球是否变暖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他批评说,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者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显然,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对资讯的吸收本身就存在着被“主流意见”误导的潜在危险,以及在时间维度上片断式的人云亦云。
“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在《天问:谁驱使了气候变化?》开篇即指出了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存在“变暖论”、“降温论”和“怀疑论”三足鼎立的论战。在这本科普读物中,他通过“天地之美”、“四时之法”和“万物之理”,从天文、地质、海洋和大气等因素分析气候变化的驱动力,说明这个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美国气象学家Edward Norton Lorenz曾经开玩笑说:“老太太说幸而我们没有住在‘局地,否则天天有雷阵雨了。”他所提出的“蝴蝶效应”,最初就是为了说明由于初值不确定而必然产生的天气预报对发生地点和准确时间的无法确定。短期的天气预报尚且如此,可见长期的气候变化是受着多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钱维宏也指出,目前人们对大气的变化过程了解较多,而对海洋内部的变化情况了解相对少。“大气变化迅速,海洋变化缓慢。大气往往用快变掩盖慢变。对持续性气候事件,了解海洋中的慢变更为重要。”
而追本溯源,这种认识的落差的根源在于近百年的气象仪器记录的现实限制:这些记录主要来自有人居住的地区;在海洋上、高山-沙漠地区和高寒地区,观测记录则很少——空间覆盖面不足会大大影响全球气候分析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观测位置的改变也是人们会忽略的因素,例如,随着城市的发展,有些原来在郊区的气象观测仪器现在已经在城市中心区了,这会带来温度偏差。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洪致文所著的《台湾气象传奇》,以社会人文的观点切入,分析与介绍了台湾各地测候所的发展背景与缘由,从历史纵深说明了这一因素的影响。他在美国UCLA攻读大气科学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授Michio Yanai一再强调:做科学数据分析前必须谨慎理解资料来源。因为,在电脑科技进步、资料获得相对容易的情况下,现代人已经渐渐失去“真正的科学研究不能缺乏实地踏查功夫”的态度。洪致文走访全台气象站的行脚印证了:气候观测首重观测地点的相同与时间的长期接续,因此二战后台湾地区许多测候所的远距离搬迁,都让原本可以谨慎累积的气象记录被破坏。
但无论全球将升温还是降温,回到每一个人的日常,大家最关心的始终是,自己身边是否会发生极端气候事件而蒙受损失。钱维宏说:“极端气候事件确实能够掠去可观的生命和财产,但引起灾难的区域极端气候事件成因不是全球变暖,不是全球降温,也不是全球气温不变,而是区域温差。”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们在呼吁下一文明为“生态文明”。
Stephan Faris说:“我们就像一个抽烟的医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翻阅探讨肺癌的医学杂志,同时希望这种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柳中明说:“若我们无法跳脱传统思维,无法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可能,那就只好做个鸵鸟,等着某一天一切会改变成我们所期望的——而那一天,却可能永远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