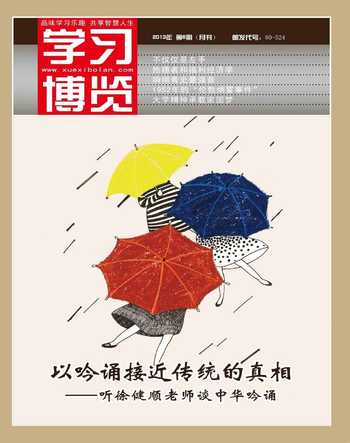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需要仪式
施琪嘉
上周,我家的狗死了,一只活了15年的京巴。它患了严重的肿瘤,自知来日不长,在主人身边发出希望洗澡的信号。洗涮干净后,它踯躅到阳台,夜晚悄悄地没了呼吸。
这只名为“胖胖”的狗,活着时喜欢和主人一起玩耍,而死的时候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因此做了一些仪式化的处理。
为什么死,哪怕是一只小狗的死,也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哀恸?为什么一些哀悼仪式会打动我们,有时我们竟会从这些仪式中获得能量和希望呢?
中国文化中强调的死之丧失其实是活人之悲: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弗洛伊德对“丧失”的定义,不仅限于那个自己所爱和爱自己的对象逝去了,也强调随着这个对象的离去,那一份爱也随风飘逝。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创伤来源于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所熟悉的环境,特别是那些构成我们安全、信任的结构的“分离”。
死亡是单程车票,有去无回!对于这样一种“绝然”的分离,大家处理的方式也显得特别。有人将亲人住过的屋子保持原样;也有的人将逝去亲人的一切痕迹都销毁掉,好像这个人从来都不存在;更多的成人,通过调动自己的哀悼机制——办理丧事、建立灵堂、与亲朋好友倾诉、写一些相关回忆文章,来平复伤痕。
很多家庭,在亲人去世时将孩子放到亲戚那儿去。其实,如果去世的亲人是孩子最熟悉的,孩子就丧失了最后与之告别的机会,而这是处理“丧失”的最重要仪式,他/她也许会竭尽终身来完成这个不能完成的仪式。
我国有清明节这个约定纪念日,通常我们用固定的仪式来怀念死者,包括时间、地点和程序的固定化,仪式的固定似乎使得我们能够将已经逝去、抓不住的亲人请回来。
仪式更有着驱除自己内心恐惧的功效。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顺的国家,害怕对亲人照顾不周,害怕死去的亲人怪罪自己。仪式将人类内心无法言传的恐惧感、无助和渺小的焦虑感通过程序化的、可操作的过程具体化,在仪式中表现出来。
哀伤不是遗忘的过程,恰好相反,它是将失去的所爱内化到自己内心的过程,是使自己和爱人最终永远在一起的过程,所以我们还需要去重复仪式,对失去的所爱的亲人需要反复去谈论,而不是回避。
在电影《活着》的结尾,福贵死了儿子和女儿,他和妻子家珍去给孩子上坟时,他们谈到女儿凤霞难产死亡时的那个临时拉来给女儿接生的被打成右派的教授。那个教授已经饿了好久,见到馒头一口气吃了五六个,最后给噎住了。家珍说,一口气吃这多馒头,这该有多饿啊!说着,这两口子在坟头笑了起来。这时天边抹起一道晚霞,镜头转到屋里福贵和凤霞的儿子苦根一起热腾腾地盛饭、吃饭的情景,生命就这样一老一少地传承延续下去,生活也依然是这样不紧不慢地沿着它固有的轨迹走下去。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