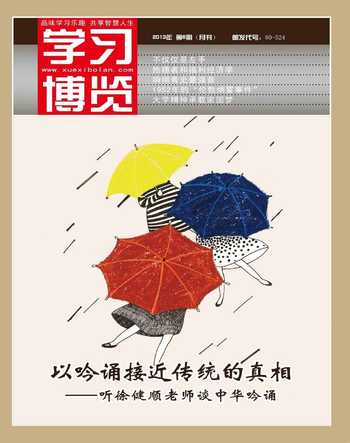我识贾平凹
阿成
走进贾平凹,无论如何是不难的,在中国普通的读书人家中,至少存有一本贾平凹的书。
贾平凹在他的一本集子里对他的作家身份作了这样的“阐述”:“即使(我)小有名气,成名岂是成功?作家充其量是个手艺人,我的‘活儿做得并不好。”他进一步解释说:“人生若认作荒原上的一群羊,哲学家是上帝派下来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如此的说明,反倒让人们觉得贾平凹是个谜了,似乎他也不再那么普通了。然而,脱俗与普通,是作家灵魂中的一柄鸳鸯剑,少了其中的哪一柄,都是不完整的。
第一次看到贾平凹对空门的敬礼,是在1990年广州的笔会上。参观一座寺院时,同行的许多文人墨客,紛纷焚香磕头,俯仰之间,亦不乏泪流满面者。贾平凹则伫立一旁,双手交叉,两拇指抵在一起,默默地仰视着。这种样子似乎已经将“问”和他不事张扬的个性含在其中了。“问禅”,说穿了,是对自家灵魂的拷问,是思索的另一种形式。遍览古今,“问”,也是文士的一个重要特质。于兹之下,他在广州送给我的条幅上,称我为“方家”,可谓心照不宣。
贾平凹似乎从不主动与人攀谈。当你主动与他聊天时,他却十分热情。同时你会发现,在无谓的应酬和轻松的闲聊中,他并不坚持什么。另外,你或许想不到,其实他早就想同你聊天了。记得在北京的“外研社”,他的属下总当众开他的玩笑,他不无甜蜜地自语道:“这哪里当我是个领导哇!”然而我们同走粤地的时候,有人看到单独走在一边的贾平凹,却悄悄地对我说:“他在想事情,不能打扰他。”这种理解与误解连在一起的事情,想来该是贾平凹的一种苦恼,但又怨不得别人。
其实,无论是身处文坛,还是走出文坛,他被提问最多的,便是《废都》,而且这样的提问常与身随。实话实说,在当下,我不仅欣赏直言的批评,更喜欢坦荡无忌的文学创作。我在想,倘若再把虚假与无聊的魔术玩下去,那真是要愧对国人、愧对历史了。
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个关于城的小说。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依我在四十岁的觉悟,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
有时候,提问的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思索的事。贾平凹说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虽则“玄之又玄”,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段真实的大白话更好。面对令人炫目的生活,作家终是不应背过脸去的。
在哈尔滨,我们聊到这个“问题”时。贾平凹说:“我的朋友不多。”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范畴的朋友。几年前,贾平凹曾有信来,说要到东北走一走,看看大白脸的女人。我不禁吃了一惊,东北的女人是大白脸的吗?于是,再上街便注意了,果然,在那些擦身而过的女人当中,真的不乏大白脸者。这种“不幸言中”,在他,大约是无意中的幽默;在我,却使得本来十分清晰的贾平凹又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了。
这就是贾平凹。
(摘自《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