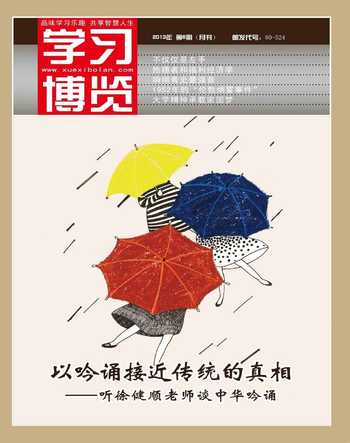以吟诵接近传统的真相
李勇刚
徐健顺,满族,1969年出生于青岛。著名吟诵专家,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曾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广泛采录、研究各地吟诵调的基础上,将吟诵规则概括为“一本九法”:声韵涵义为本,入短韵长、虚实重长、平长仄短、平低仄高、依字行腔、依义行调、模进对称、腔音唱法、文读语音为九法。2010年,发起成立中华吟诵学会。2009年和2011年,两度在北京发起举办“中华吟诵周”大型学术文化活动,邀请海内外著名吟诵专家数百人齐聚北京,共襄盛举。在全国做过几百场讲座、七十余个班次的培训,在多家电视媒体展示过吟诵。录有《徐健顺吟诵专辑》《学唱传统吟诵》《吟诵之美讲座》《吟诵理论与方法》等吟诵录音与录像。正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着力建设“中华吟诵资料库”,包括“少数民族汉诗文吟诵资料库”、“北京话/普通话吟诵数据库”、“吴语吟诵资料库”等。
2011年,在北大繁星诗社的中秋雅集上,徐健顺老师拍着桌子、端着酒杯,吟诵太白的《将进酒》,试图展现出一个“痛苦以豪放出之”的李白形象。桌子听上去险些被拍烂,桌面上盛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尚能安然。酒杯被他数度端起,却终未喝下。
今年暮春时节,去首师大拜访徐老师。对着照相机,徐老师整个人极不自然——眼睛不愿意直视镜头,即使目光斜视时,依然显得“羞涩”。他经常上电视和做讲座,经历过太多“大场面”,按理不至于此。回来看他的文章,里面说:“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表演就是假装,是娱人的”,“自己有了情感,抒发出来,才是艺术。”
徐老师每周在学校里和社会上讲课超过30小时,从无间断,每每带病上课。有学员在博客中说,徐老师是“用生命去挽救与弘扬中华吟诵”。
吟诵承载着声音的意义
《学习博览》:徐老师,你所致力推广的吟诵,是当今比较陌生的读书方式。请你开章明义地谈一谈,什么叫“吟诵”?
徐健顺:“吟诵”,应是“吟咏”和“诵读”的合称。在古人那里,“吟咏”的对象多是诗词韵文,甚至可作诗词韵文的代称;“诵读”的对象,既可以是诗词韵文,也可以是散文。“吟咏”多半有曲调,但也可以没有。“诵读”多半没有曲调,但也可以有。在推广吟诵的时候,我做了概念上的规范,用“吟咏”专指有曲调的,“诵读”专指没有曲调的。
汉诗文的“义”有三个层次:字义、音义和文化涵义。现在一般中国人都不知道“音义”了。只有吟诵,才能把长短、轻重、缓急、高低这些声音的意义展示出来。
《学习博览》:为什么非得通过吟诵才能理解“音义”?
徐健顺:因为汉诗文本身就是通过吟诵的方式作出来的。鲁迅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其中说“怒向刀丛觅小诗”,他怎么写诗呢?“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说明鲁迅作诗是先吟的,吟成后才要找支笔记录下来。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古人?李白说“吟诗作赋北窗里”,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韩愈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白居易说“终日歌吟如狂叟”。中国人“作诗”的主要方式是“先吟后录”。作诗的时候,心中流淌的是吟诵的声音,所以叫“作诗”不叫“写诗”。这与今日之上来就写、涂涂改改或者敲键盘完全不同。
“吟”的总体特征是拖长腔,即“歌永言”。有的音可拖长,有的音拖不长,那么长的就更加长,短的就愈显短。在生活口语中,语音本身的意义不大。然而一旦拖长,声音的意义就被放大了,于是承载了作品的一部分意义。同理,高低、缓急、轻重,在吟诵中都被放大了。所以,当我们说某诗好,叫做“脍炙人口”,没听说“脍炙人目”的。
诗文格律的产生,也是因为吟诵的需要。在字音都拖长的情况下,要是都是高音或低音,会让人很累,而且难听,所以要一高一低地唱。汉语是两个音节为一个节奏单位的,所以每两个字要变化声调,就形成格律的“平仄相间”原则。只有吟诵才能表达声律的意义,传达古人的心境。
吟诵不仅是诵读和创作方式,还是教育、修身、养生的方式,是汉文化的意义承载方式和传承方式,是中国式读书法,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曾国藩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曾国藩是桐城派传人,吟诵的时候声震屋瓦,每日以此为乐。这是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状态。
朗诵是从老外那舶来的
《学习博览》:相比起来,如今我们所习惯的朗读,在你说的这些方面似乎都不太“讲究”了。
徐健顺:我每次上班经过一个学校旁,老听到里面的学生齐诵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因为这种读法,从小学到大学,我们都讲这首诗的意思是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你读读它的韵:“iou”,拉长3秒试试,还能积极向上、奋发图强吗?再看这个韵有哪些字呢?秋、悠、游、囚、幽、留、忧、愁……情感都很悠长,一般很忧郁。那么大的太阳都落山了,那么长的黄河都入海了,不回了。我的生命啊,也将流逝。我多么想抓住时间啊,所以我要登楼,再登楼。可是,鹳雀楼只有三层。可见,这是一首吟咏生命苦短的诗。从典故上看,杜甫说“花近高楼伤客心”,辛弃疾说“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有王粲登楼而悲。在古代,登楼是伤心的意思。
朗诵中每个字都很短,不超过一秒钟。但当我们吟诵时,体会就完全不同。朗诵可能误解诗歌的原意。
《学习博览》:既然古代诗文都是吟诵,为什么我们今天只知道朗诵呢?
徐健顺: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小学课本使用白话文。白话文要怎么读?当时谁也不知道。教学大纲中出现“两字一顿读法”的字样,当时有很多老师、学者撰文反对,到1926年就从大纲中删掉了。此后,西方重音语言的诵读方式随着话剧和白话朗诵诗进入中国,并在抗日朗诵诗中定型。
朗诵的基本方法源于印欧语系重音语言和节奏语言,全靠轻重、节奏、速度、架势,而汉语是旋律型声调语言,讲究高低、曲折、长短、声韵,二者有根本的区别。话剧的朗诵属于表演,需要放大声量才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到。他们把“朗诵”、“朗读”这两个带“朗”字的词拿走了,我们今天被迫叫“吟诵”。
当时,北京和上海都有民间艺人说相声嘲笑过古怪的朗诵。汉语要如何朗诵,早期也是不清楚的。所以,台上朗诵,台下哄笑一片——见惯了吟诗,没见过这么念诗的,也没见过这么在台上说话的……一百年以后,台上吟诵,台下哄笑一片——人们反倒纳闷:中国的诗怎么叫他念得这么怪腔怪调的?我们的诗不是历来就是朗诵的吗?
三千年以来,作为旋律型声调语言,汉语一直是用声调来传情达意的。自从我们引进西方的模式以来,把汉语当英语教,把表情达意的方式仅当成字义式的,而不是声调式的,从而失去了汉语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朗诵强调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但很多是无根的乱解。
为什么会听错这些歌词?
《学习博览》:除了“朗诵”,唱歌跟吟诵似乎也有某些联系。
徐健顺:杨荫浏先生说,中国音乐都是从吟诵里流出来的。吟诵没有了,中国人已经不会唱歌了。
和吟诵一样,传统中国唱歌也讲究依字行腔,就是不倒字。不仅准确地发出声母和韵母,而且依声调的方向来走旋律。声调往上的就往上唱,声调往下的就往下唱,声调平的就平着唱,声调拐的就拐着唱。我教依字行腔,一般只需要10分钟,因为这是每个说汉语的人的本能。
《学习博览》:现在的歌,能做到“依字行腔”的很少,倒字反倒让我们习以为常。
徐健顺:有一个贴子叫《听错的歌词》,在网上流传十年了,大部分都是倒字问题:
“学习雷锋,好榜样……李昌坚定豆子香……”这个李昌是谁呢?为什么他坚定了,豆子也就香了呢?因为豆子也是爱国的吧……
《龙的传人》那句“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当初无论如何也听不懂,总听成“永永远远地差两年”,老是纳闷儿,为什么一定要差两年呢?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小时候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郁闷了好些年……
还记得游子费翔的《故乡的云》吗———“……鬼来吧,鬼来……(归来吧,归来)”,乍一听,真吓了一跳。
第一次在听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时,竟听成“……野驴呀,神秘野驴呀……”纳闷儿了好一阵子!
……
这年头,唱歌不讲究依字行腔,不打字幕就听不出来唱的是什么,听错歌词就在所难免了。
国学教育得更“国学”点
《学习博览》:这些年国学教育逐渐复兴。在读诵经典的过程中,大部分学校或私塾也没能采用吟诵的方式。
徐健顺:是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中西语言的对比。西方语言是轻重音,所以有非A即B的“逻辑”;中国语言有流转的声调,所以有圆融流转的“道”。汉语说起来是婉转的、连绵不断的、圆润的、柔韧的。吟诵是拖长腔的,更放大了这种语感,所以文人在气质上大多似水、如玉。
现在很多孩子像机关枪一样地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能止于至善吗?这明明是RAP,是hip-hop!这样体会不到经典中的跌宕起伏、婉转迂回,体会不到圣人之意的深微奥妙、精切细致,读经之功、背诗之意就大打折扣了。如果孩子将形成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形成刚硬的性格,而他的环境、根基又决定他成不了西方人,岂不是要矛盾一生?
现在一些地方在推行国学教育,除了课本换了,教法、模式、环境、理念好像仍是体制教育那一套。国学教育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教法不“国学”仍不算是国学。
《学习博览》:那你认为国学该怎样教才够“国学”?
徐健顺:首先要强调吟诵。我采访过的很多老先生都说,几十年过去了,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东西几乎全忘了,但先生教的吟诵调却永远记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能慢慢体会出为什么这个字高,那个字低,甚至先生的表情、动作、姿态,都清清楚楚地想起来——原来,先生把自己的理解通过“编码”融进吟诵中,一股脑地传给了学生,种下未来理解的种子。如果只是朗诵,即使小时候背过,长大后也不一定能够自然理解,因为没有把理解的种子种进孩子的心里。
其次是一对一的教学方式。中国人相信没有两个一样的学生,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所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每个学生吟诵的内容都不一样,极少出现大家齐念的情况。大家各吟各的,所以“书声琅琅”——就像不同的美玉相碰,发出美妙的叮咚之声。西方教育标榜个性,但使用一样的教材,用一对众的教学方式,成批地生产,恰恰是反个性的。
还有是早识字。反对早识字的理由是识字使用理性,对于理性未发育好的儿童是一种摧残。这是西方人的经验。西方是拼音文字,是逻辑文字,如果不会拼,就等于没学会这个字。汉语是图画文字,识字更多是用感性认识的。我们古代的教育是识字优先,就当图画来认,写字可以推后。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学习汉语主要用右脑,学习英语主要用左脑。中国的儿童恰恰要趁感性好的时候赶紧认字。有了吟诵这个工具,识字教学就变得很容易。
九十多年来不绝如缕
《学习博览》:九十多年来,吟诵逐渐式微,但不绝如缕。如何看待这段惨淡的历史?
徐健顺:1905年,清廷下令废止科举。1912年,民国成立,以新学堂为教育正宗,不承认私塾学历。吟诵是跟着私塾一起淡出教育体系的。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小学使用白话文教材。建国后,吟诵不再进入课堂,朗诵遂一统天下。
不过,吟诵仍然“不绝如缕”。1927年,赵元任为自己的《新诗歌集》作序,开始吟诵研究。一大批学术大家,如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吴世昌、王力、朱光潜、赵朴初、臧克家、周有光、卞之琳、朱东润、南怀瑾、叶嘉莹等,都曾撰文呼吁吟诵归来。唐文治先生主持上海交大和无锡国专,40多年坚持吟诵立校,大批江南才子受益。“唐调”源于桐城派,如今成为最大、最完整的吟诵调。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批会吟诵的先生们刚从牛棚出来,心境极佳,身体尚健,学术会议大家见面,总要吟诵一番。用半头砖录音机录的磁带,现在尚存不少。1988年,中华诗词学会拍摄《华夏诗声》吟诵专场录像,数十位先生纷纷吟咏唱和。1991年秦德祥先生采录常州吟诵,1992年王恩保先生采录北京吟诵,一时吟诵似乎回春有望。
但是,限于唱和的吟诵毕竟不能持久。随着先生们的年事渐高,吟诵之声又消沉下去了。
《学习博览》:这应该是你积极张罗成立吟诵学会的大背景吧!
徐健顺:近几年,为了抢救、传承和推广吟诵,我们团结了一批有识之士,赴全国各地开展了抢救、采录、整理、研究的工作。在中央精神文明办、国家语委、教育部语用司的领导和支持下,2010年1月24日,经教育部批准,民政部注册,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中华吟诵学会)。这是一个吟诵文化志愿者群众团体,也是唯一的全国性吟诵组织。
老先生的吟诵最是动人
《学习博览》:现在,全国还有多少会传统吟诵的老先生呢?
徐健顺:估计几千人吧,但每天都可能有几个人离世。最后一代会吟诵的老先生,年龄一般在80岁以上,而且没有向下传承。目前一个市(包括下属各区、县)如果有10位吟诵传人,就非常幸福了。如果一位也没有,也是正常的。
每一位吟诵传人都很珍贵,因为他传承的是那个特定地区的吟诵。在百年以前,吟诵就像民歌系统一样庞大丰富。今天,我们每失去一位吟诵传人,就可能失去一个地区的吟诵调。这个地区在将来发展自己的普通话吟诵调时,就失去了根,只能参考临近地区的吟诵调。所以,抢救、采录传统吟诵是目前最紧急的工作。历史只留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中华吟诵学会准备对全国的吟诵传人进行采录,并把信息汇总整理。目前已经采录了600多人,搜集了400多人的影音资料,总计积累上千位老先生的吟诵影音资料和采访记录,另有数百万字的吟诵文献。
《学习博览》:在采录过程中,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况?
徐健顺:我们采录老先生,经常碰到读着读着就哭了的情况。因为那个声音是真的,真的才能感动自己、感动别人。老先生的吟诵,经常颤颤巍巍的,有时还跑调。但是,最打动我们心灵的,还是老先生的吟诵。比如坐到一个老先生面前,他开口就吟“李白乘舟将欲行”,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社会的看法,他的待人接物乃至整个生活,全在这里头了。
我们采录的那些老先生,个顶个的,全都很有特点。每个人都能讲一堆故事。他们表面上看没什么,但身上有一种和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至少要有所了解。
普通话吟诵的“矿泉水调”
《学习博览》:吟诵学会还开展了很多普通话吟诵的推广工作,情况如何?
徐健顺:吟诵自古是用雅言来文读的,雅言可以说是古代的“普通话”。所以,我主张并致力于推广普通话吟诵。普通话与古音虽然不同,但已经成为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吟诵,并不排斥传统的方言文读系统的吟诵。吟诵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让吟诵重新回到课堂,回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学会两种吟诵:普通话吟诵,以及立足方言母语的传统吟诵。吟诵工作分两个方面:推广普通话吟诵,传承传统吟诵。
普通话吟诵受到各地中小学师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自从一些学校引进吟诵,有些从前对古诗文不感兴趣的学生,爱上了古诗文,也爱上了语文,爱上了学习文化。很多孩子变得高雅,有志向,有气节。校园里,在课间和放学的时候,到处是学生自发吟诵的声音,流行歌曲被湮没了。这就是吟诵的魅力!
《学习博览》:听说你的“矿泉水调”在很多学校很有名呵。
徐健顺:我教普通话吟诵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地方的人凑在一起练习依字行腔,开始的时候各自并不一样,但很快就会找到共同的调子。在全国各地的吟诵学习班上,这个调子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事先的串通或准备,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大家一开口吟诵,必然是这个调子。这就是标准普通话吟诵调,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的调子。
比如《静夜思》,大家的吟诵都是这样的:
61 61 61 16 1 — 61 16 16 16 1 —
床 前 明 月 光, 疑 是 地 上 霜。
原来,大家唱的是“11111,11111”这个基本调子。61、16这两个音程,是用来表示升降调的,6近似个倚音。所以,实际上唱的是平调,而且是主音的平调,有所变化是因为依字行腔。有的学员把这个调子戏称为“矿泉水调”——讲课时我面前通常放瓶矿泉水。我也接受这个名称,因为矿泉水是单纯的,正好可以代表标准普通话吟诵的主音平调;矿泉水又是富含营养的,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正如标准调可以变出无限的吟诵调一样。
真相的力量吹枯拉朽
《学习博览》:徐老师,最后想问一问,你是如何走上吟诵这条道路的?
徐健顺:我教过2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一度颇以此为自豪。2004年,我意外地听到了吟诵;两年后,我心中的古典文学殿堂轰然倒塌——不是说中国古典文学不好,而是太好、太美了。此前那个所谓的“中国文学”是假的,是丑的,所以倒了。吟诵的价值和魅力,就在于它是“真”的。真相的力量摧枯拉朽,无往不胜。
如今,中国人集体遗忘吟诵,只当汉诗自古就是朗诵的,把汉诗当成poem。Poem怎么能叫“诗歌”呢?拜伦、普希金、莎士比亚写的叫“泡艾姆”,如果他们写的也叫“诗歌”,难道杜甫写的叫“泡艾姆”?很多人拿来杜甫的诗,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象征”、“结构”、“转喻”、“中心思想”——我们哪有那些东西!
连这么巨大的历史事实都可以抹杀、遗忘,还有什么不可以遗忘、篡改、歪曲、隐藏、抹杀的?
《学习博览》:从吟诵出发,你要重新理解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徐健顺: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这一百年来的学者所说的样子,很多东西要分清楚。
比如,“novel”,要叫它“诺奥”,不要叫它“小说”。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如果叫小说,而我们的《水浒传》也叫小说,那就麻烦了。一谈《水浒传》,就情节、人物、线索、高潮什么的——哪有这些东西!小说是说书,一天一段。novel是私密的,小说是公开的,二者目的有差异。
比如,中国历史,不是“黑斯垂”(history),不是阴谋史,而是仁义与利益做斗争的历史。
比如,现在的流行歌曲,是“丧”(song),不是我们中国的“歌”。中国的歌有腔有调、字正腔圆,是即兴的、个人性的。现在的音乐,已经成为极少数人的职业。他们为大众制造“丧”,所以只能迎合流俗,不是他们的真实情感。我们大众享用他们的产品,那“丧”唱的也不是我们的情感。只是互相欺骗。
我们也没有“艺术”或“文学”——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我们有的是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礼教乐教、医卜数术。传统文化的真相,因为西学的阐释而模糊了。
《学习博览》:原来你大力提倡吟诵,并非只为吟诵这么简单。你这些“另类”的看法靠谱么?
徐健顺:靠不靠谱,你自己吟一段时间之后再去体认。和中医、武术等相比,吟诵的独特性在于,它还没有被西学解释过。它是极少数被抛弃的传统之一,反倒是原生态的。通过它,更容易接近传统文化的真相——
中国的音乐,不是你知道的样子;中国的教育,不是你知道的样子;中国的政治,不是你知道的样子;中国的农业,不是你知道的样子……我们的祖先,不是你知道的样子。
吟诵的目的,不在于吟诵,而是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真相。见到之后,你才知道它的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