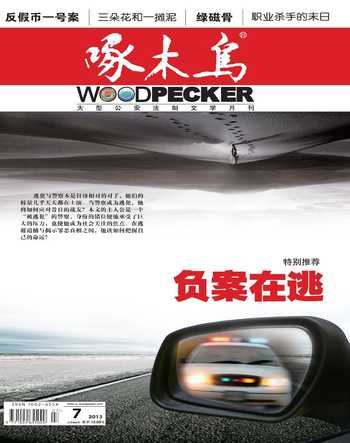俩县长
李立泰

张扬理、李文章二位,大学毕业分到地方工作十几年,农家子弟,没啥后台,靠工作积极、团结同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谋私利,入党提干。靠真抓实干一步步地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累得筋疲力尽、汗流浃背、心慌气短、腿肚子哆嗦,夸张点儿说,肠子快弄断了,终于——是终于,一腚坐到县长位子上。
该歇歇脚了,喘口气、喝点儿水,跟家人一起也吃顿清净饭。有点儿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不敢奢谈养精蓄锐。
可二位刚刚打了个盹,就警醒了。时间不饶人啊,都年过不惑了,“五”在正前方遥遥相望。
二位县长心里说:时间是硬道理,年龄就是生产力。关键时刻你大一岁,大一个月,甚至大一天也不行!看看文件明摆着,某年某月某日之前的离岗,提拔无望了。
你年龄小一天就可能留到这边,你若大一天就那边去了。
二位记住了老师的告诫:甭管干啥要紧的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是毛主席说的。
张县长,是学理工的,却好写文章。
李县长是学中文的,白浪费了文章二字,快十年没动笔了,因为一参加工作就写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简讯等等,写得眼花,写得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写得血压高。
张县长讲话擅长脱稿,不好照本宣科。
李县长讲话,好照稿子念,省心。
张县长在河东县。
李县长在河西县。
俩县的经济状况不相上下,在全区排名不是七八就是八七。当然后面还有老九老十,不是倒数第一第二,好在不垫底儿。
警醒之后,立马振作起来,不过二位的工作思路有了差异。
张县长上任伊始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三农”和水利建设上。连续召开农机、水产、农发办等部门的专家会、座谈会和吸收老农参加的“诸葛亮会”。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为河东的“三农”发展和水利建设出谋划策,拿方案出思路,一句话不嫌少,一篇文章不嫌多。张县长总结智囊团的意见建议,理清了思路,找到了制约河东农业发展的瓶颈。他执笔写出实施及整改方案。先从河、湖、堤坝开挖加固入手,大干三年,力争达到五十年一遇。
李县长上任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重点抓文化”的工作思路。
首先搞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合并。组建文广新局,暂时在原单位办公,到各单位一把手到龄离岗,逐步合署。然后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地区、省、国家,一级级地上报。面人、泥人、版画、剪纸先后被地区、省里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狠抓文化产业建设,敦促事业单位改制。河西的文化工作大有亮点,地区、省里先后召开现场会,推广河西县的文化工作先进经验。李县长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声,成了“文化名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二位干三年了。这年夏天,老天爷翻脸了,下开了涝雨。
以河为界,河东经过几年的治理加固,面对暴雨河水高涨,可以“高枕无忧”。
河西县则召开了“全县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涝灾害大会”。
李县长穿雨靴、披雨衣、扛铁锨指挥在、战斗在大堤上。
他心里明白,现在旱灾一般死不了人,水灾可就危险了,责任重如泰山,一县之长啊!身先士卒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哪儿有险情哪儿就出现了李县长的身影。
大堤临时“抢险指挥部”医务室大棚里,被同志们强拉下来的李县长挂上了吊瓶。
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和水务局的同志在查看险情时,晕倒在堤下的烂泥里。
省报、省台的记者们等在棚外要采访李县长。醒来的李县长告诉秘书,让记者到抗洪一线采访同志们,多少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啊,不要采访他。他不接受采访。
洪水退去了,大堤保住了,河西人民生命财产没受大的损失。
省报、省台连续报道河西县人民抢险救灾的战情。
但是李县长深深反思,自己是“犯了罪”啊——工作有失误。
他向地委递交了检查书,深刻剖析自己思想根源,要求上级给予处分。
上级很快研究了李县长的检查。
几天后,给李县长下了一纸红头文件。不是对他的处分决定,而是重用他,任命为河东县县委书记。
第二天,组织部部长送李文章书记赴河东县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