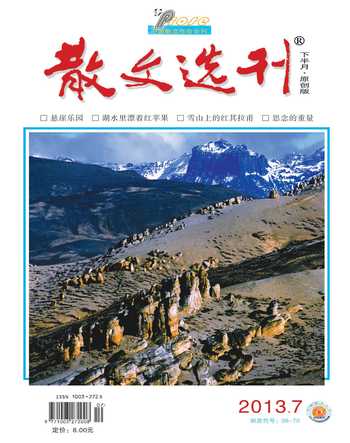喀什
何向阳
大约10年前,与母亲在北戴河度假,认识了一位来自新疆的朋友,仍记得在那两棵丰硕的核桃树下,那些个夏夜或者炎热尚未褪尽的傍晚,我们坐在树下聊天,核桃树的巨大的叶子盖下来,在谈话人的脸上投下暗影。已不记得都聊了些什么了,好像有一次,母亲说到了泰戈尔,那位维吾尔族朋友惊叫了起来,他说他“喜欢极了”这位诗人的诗。10年前的那个说起遥远国度的诗歌的夏夜,好像并不远吧,可是,母亲已不在了。
那个夏天时隔一个月后,秋天,我们一行作家到新疆去,从甘肃敦煌出发坐车西行,一路戈壁沙漠地走过,在乌鲁木齐,我又见到了那位热爱泰戈尔的新疆朋友,他带我们去吃烤包子,从喀纳斯回来后,他又一路送我们到机场,几乎将他认为那个季节最好的瓜果都给我带上了。新疆12天时间,北疆一天一个地方地跑,回到家,脸上的晒红还没褪去,就又收到了友人寄来的一个邮包,是什么?打开来,原来是一个由纸盒子装的许多音乐碟。怎么?打电话去感谢,对方在电话里讲,这次,你们去的是北疆,没有到南疆,而我们维吾尔族的文化主要在南疆,所以,你们并没有了解到我们的许多文化,只是了解了我们的风景。所以,寄去的这些音乐,是我们的十二木卡姆。有助于你了解我们文化的新疆。呵,原来!他还补充说,以后欢迎来南疆,你先听了这个音乐,你就会爱上新疆的。我在电话线的这一端听着他的诉说,我知道,我早已爱上了新疆。新疆有这样的友人爱着他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我爱它万千种理由的最主要的一种。
从新疆回来的一个多月后,母亲就生病住院了,在两年的治疗过程中,有时,我会拿出这些音乐,与母亲一起听,有时候,从医院回来取东西的间歇,我会把手头上的一个碟片放在家里的音响中,一边给母亲准备带的饭,一边听。后来,又收到了友人寄来的麦西莱甫光碟,记得一次,从医院接母亲回家,在家里的电视上放给她看,母亲那么喜欢,那种生机勃勃、充满欢笑的歌舞,我们看着,看着,那次,母亲笑出了声。
我当然把我们的喜欢告诉我们的朋友,他听了高兴极了,他在电话里说,要是全听下来,我们的十二木卡姆,要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呢。但是他哪里知道当时的一天一夜对于我的宝贵,那是日日夜夜在病床前的时间,现在想来,就是真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那时的我也不会有静心下来听它全本的心境呵。后来,他知道了母亲的病后,竟从新疆专程跑来,在母亲的病床前,他伸过手去,握着母亲的手,说,我也有一个母亲,她的岁数没有你大,你快好起来,我还想着在新疆接待您,安排两个妈妈见面。还有你喜欢的音乐给你听。临走时,他还用小米给母亲做了一个枕头,说天热了,总躺在床上会出汗,小米可以吸汗。可不是,那一年,距上一年说着诗歌的夏夜,也只是不足一年的时间。维吾尔族人对于友谊的看重,只在这一个事情上,我已感受很深。想想看,他只在一个海边度假时认识了我们,我们也只在核桃树下谈诗,他陪我和母亲去看过一次海上的月出,我们几个人在沙滩上一边散步一边说着什么我都记不清的了。但是一听说我母亲病了,他竟从遥远的地方跑过来,我曾侧面问他,你们都是这样待别人的吗?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说,你的妈妈是一个好人。我们都爱她。
母亲已走了七年了,但是每一年的清明节,我都会收到他的短信,读到他用汉语写下的对我母亲的思念,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去海边看月亮的夜晚,风有些凉了,我和另一位朋友走在海边,而他一直陪在母亲身边,远远的,我看见他和我母亲低声说话,远远的,我看见母亲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的样子,但是走在他身边的母亲,轻轻地笑着,显得是那么的开心。
后来,我收到一位西安朋友寄来的包裹,打开来,是十二木卡姆。这位朋友在新疆生活了近20年,知道我喜欢新疆,他还寄来不少关于新疆的书,有些是影印的,因为图书馆也就这一本了,他说。他说,上次寄你的木卡姆听了没有?要整个听下来,得一天一夜。是呵,这是我收到的第二套十二木卡姆,他和他说的是一样的,一天一夜!我多少次打开它们,但终究还是没有去听个完整,我知道,只要一听,我会想起一切,想起在我心里珍藏着的过往,但是不听,难道我会遗忘吗?那些过往,那些友情。不!我会难过,难过那个曾与我共度40年的母亲,我已经无法与她一起再共看海上明月了,我又如何对待我们两人都曾迷醉的音乐呢?我的心情和爱,都藏在那一旦响起便会深陷其中的声音里,我又如何一个人去听,去面对它们呢?一天一夜,我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敢打开那记忆之闸,所以宁肯它静静地躺在岁月里吗?如同,我如果深爱一个人,一件事,往往是静静地避开,静静地爱着,如果真的抓住,可能我会被那上升的火焰摧毁。所以,十二木卡姆,我从未完整地听过,它之于我,只是散在于我生命的各个历程,而且常常是最重要的时刻。
一天,曾和我一起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一位朋友,从新疆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一本《木卡姆》,上面的图片与文字一样让人过目难忘。我重又翻出我的新疆友人的书,他的一本用维吾尔语写成的关于木卡姆的传承与发掘的书,他告诉我他写的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怎么样,而是为了木卡姆,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惜一切地把它保存了下来。我写的是这个人。他强调着说。但是那些上升的舞蹈一般的文字,我一个也不认识,在他的书面前,我是一个文盲。我曾经多么的想去认识它们,学习它们,但是,我不如他,他已能文学地翻译汉文作品,而且出版,我呢,连看它们都是困难,又如何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呢。我曾向他表述过我的难过,他却哈哈大笑了,我会再寄一些书给你,你看得明白的书。我的书架上,多了西域乐器的书,就因为我说我对西域古乐感兴趣;而上海一位师兄也寄来了有关新疆的书,我那个时候,正在研究喀什的民歌,一本《喀什民歌选》,就这样来到了我手里。
到乌鲁木齐开会,新疆朋友听说了,高兴地开车带我去买唱片,他的车上正放着一个音乐碟,好听极了,我说,我听过这个碟,但不知道唱的什么,他说,我来翻译一下,这个歌词吗,是这样——地狱的火有一万倍热,我的爱比地狱的火还要热一千万倍。后来,我在一本《十二木卡姆歌词选》中读到了这一节,书中的译文是——人说炼狱之火厉害,哪儿比得上爱火的力量,对你的思念,像座大山时时压在我心上。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段我听过的音乐了,但从译文来看,比我的朋友还差点力道。
喀什,就在这样的思念中,渐渐近了。所以听到朋友们说要去喀什,我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上的事,直奔它去。在老街,走在后面的我,不知觉地就来到了一个乐器铺子里,三个做乐器的人,一个在低着头做着,一个在调音,一个干脆取了墙上已做好的热瓦甫弹了起来,我站在门口听,弹琴的中年人竟唱了起来,他绝对不是一个专业歌手,但是他唱得是那样深情款款,让人心动。后来我的两位同行也来了,他们听着,听着,也不愿意走了,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听着一个做乐器的师傅在用他做好的乐器伴奏着即兴唱着歌,这样的时光是不是一度离开了我呢?我听着,听见生命中的一些什么又回到了身旁,心里有一种感激。对面这人,他不知道,他只是随便地唱他的心情,但是他的歌之于我们,却是一种肃穆的唤醒。仍然是听不懂的,却好像一种难得的重逢。我宁愿它是:
没有你,我要这生命做什么?
没有你,要那天堂和天仙干什么?
苦恋于你我流了那多么多的泪水,
又要那淅沥不断的春雨干什么?
入暮当做你撩起垂散于面的柔发,
我还要那皎洁的月光干什么?
你眼若天仙,面似玫瑰,身材如桧柏,
有你在的地方,还要那些花园干什么?
倘若你想去江畔漫步游览,
就看我的泪眼吧,要那江上清波干什么?
请在你门槛边,赐我一席栖身处,
阿塔依还要那亭榭楼阁干什么?
从库木代尔瓦扎作坊出来,我们从喀什出发到莎车去,四个小时戈壁路,但想一想,我们几乎是沿叶尔羌河走,而目的地又是木卡姆的故乡,便安心下来。在庄子里的农家,我们再次与木卡姆相遇,一个简朴的院子,一面褪色的白墙,树叶的影子投在上面,来的人都是中年、老年人了,但是乐器在手,不一样的场景便铺开了,我的干旱的心也立刻像浇了水,变得湿润起来。仍然是听不懂一个字,一句话,一行完整的歌词,但是我知道那些由弹拨尔、热瓦甫、都塔尔、沙塔尔等发出的音色,和琴弦代人表达的爱意和忧伤,我知道唱歌的人,他心中的最深最深的由于爱情而来的悲凉与苦闷,我以为,只要是深深爱着的人,他的心中真的是一半喜欢,一半忧愁的,甚至,忧愁与悲凉多于喜欢,为什么,不知道,爱到了深处,其实是对于凄楚的最为广阔的体验,这是与我曾经以为爱情的快乐多于感伤的完全不一样的感知。所以,听着听着,你会为那从深心里发出的呐喊,感到震颤,那份悲情又在极热烈的氛围中消融了,或者冰凝了,你看不见,但是你却触得到,因为你也在爱着。深切地不悔地,爱着。所以,我听到的,大约是:
倘若片刻见不到你,我要这个世界有何用?
倘若心里不把你思念,我要这生命有何用?
你散开你如缬草般的秀发,纷披飘逸,
我成了流浪的乞丐,要居所有何用?
为一沾你樱唇间的蜜水我若一命归天,
赫孜尔那永生的圣水对我又有何用?
为了见到你,我把废墟当成了家园,
如今天堂里的花园绿洲对我又有何用?
我用泪水洒地,用睫毛清扫你走的路面,
你若去古丽巴合游玩,我待在这古涧有何用?
思念的隐痛使我的心成为盛满血泪的酒盏,
萨克,你若不斟酒我不饮干这血泪又怎么办?
求求你,别把麦赫尊从你的门前赶走,
我是你的守门犬,别的门槛对我有何用?
我真的不知道阿塔依是谁,麦赫尊是谁,哪朝哪代,我只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在爱中备受煎熬的人,他们是真的爱着另一个人的人。我尊重他们,他们的爱。正如我对新疆的爱,这种爱联系着母亲,接通着生命。虽然大多数时间,我和你,语言不通,表达不畅,但爱是真的,如歌里唱的:
大麦呀,小麦呀,
轻风可把它们与麦草分开来,
兄弟姐妹手足情深,
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分开。
而有种爱,就是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像那个漫步海堤看月亮的夜晚,在记忆中,它不一直从遥远的时光中不断地回来?!
喀什机场,我望着飞机外的天空,拨响了我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这一次无法去看他了,因为只在乌鲁木齐转机不出机场,那么你在哪?电话那一头问。
我说:“喀什。”
“啊,真的吗?”他的口气中又是高兴又是遗憾。
“是呵,是真的。”我回答说,“还要再来的。”就是为了木卡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行李,飞奔而去。
责任编辑:黄艳秋
绘画:朱玛·玉素甫
——以新疆莎车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