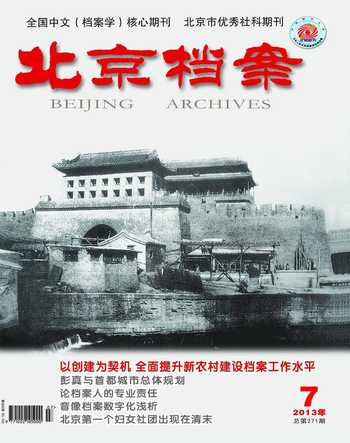一个女学生走上革命之路的回忆
我是1928年生人,父亲叫蓝公武,抗战时期是北平中国大学的教授。因为他在课堂上宣传抗日爱国主张,咒骂汉奸和日本人,很受学生的拥护和欢迎,也因此被抓坐牢。父亲当时跟张苏、齐燕铭、申伯纯、张致祥等相熟,他们都是在北平任教的老师,也都是中共党员。我哥哥蓝铁年对他们都很熟悉,跟陆平关系很好。当时父亲组织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有不少进步的学生都到我们家里来,哥哥经常把陆平拉去听课,所以我们家跟地下党很早就有渊源。而我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共产党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自然亲近和向往,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到解放区去
从1939年开始,在北平地下党的动员下,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到了解放区。1945年7月初,我上高三的时候,崔月犁这一条的同志又找到了我,劝说我到解放区去。组织上给我买了车票,把我送上火车,交给了定县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交通员,她告诉我到了检查站什么也别说,就说去定县探亲。后来到了解放区附近,他们发给我一套手工机器织的蓝布衣,但由于我年纪小,没有适合的衣服,套在身上显得特别肥大。我记得当天吃的是大麦米做的面条,第二天早晨就出发了。临走时,还给了我20块解放区的边币做盘缠。
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后,组织建议我改个名字,有利于保密,我就改名叫徐夫了。因为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她们的母亲姓徐,她们到解放区后都改姓徐了,我为了和她们保持一致也改姓徐。其实,当时去解放区的同志名字都很奇怪,因为都是为掩护身份临时乱取的,还有叫“七四九”的、“二一”的呢。
在解放区,我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那时听课的情况,在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听课时,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个布帘把自己遮住,彼此间谁也看不到谁,上完课大家就各自走各自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是为了防止彼此身份的暴露。因为学习结束后,大家还是要回到城里的,如果有人暴露了,又不想回去也是不行的。因为你的家人还在北平,这样做会连累家人。
我在解放区大概住了有十天,解放区的人曾提出让我留下来,别回城了。之后,我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二班。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缺人,到联大招人。因为我是高中生,普通话又比较标准,被选去当播音员了。
结缘新华广播电台
到新华广播电台后,丁一岚(曾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是我们播音科的科长,她是我的第一个领导,我跟她关系一直很好,从她的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
1946年10月,傅作义的军队进攻张家口,电台准备撤离。10月10日双十节,傅作义部对张家口进行轰炸,电台留下少数人值班,其余同志都出去防空了。因为我们的同志对这些事情比较有经验,大家躲到了屋檐下,所以所有同志没有一个伤亡的,而且此间播音一直未停。老百姓因为没有经验,听到炮声吓得到处跑,所以很多人被炸死。从防空地点回到电台后,已经接到上级命令,就准备撤离了。宁远放送所所长赵洪政同志亲自开一辆大卡车接我们。我们那一拨一共走了十几个人。卡车行出十多里,我们回头还能够看到“十三里营房”陆军医院燃烧的火光。
转出十八盘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这时国民党的飞机临空而来,向我们扫射。大家暂时下车躲避,飞机很快飞走了。我们的车没有遭到破坏,大家上车继续前进。天亮后到了蔚县西河营,先撤出的同志在那里等我们。在那住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又转移到阜平。因为那时我年纪小,一点也没觉得打仗很可怕,反而觉得很好玩。
到阜平后,我们住在栗园庄,广播台设在山上。由于电源工作情况不太好,组织上交办我出去联系姚依林,为电台找动力。我先到岳飞牌烟厂借了一匹马,骑马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广安,找姚依林同志求援。姚依林说他们那儿有一个日本的技术师,可以帮助我们,但要过几天才到,我就回去了,到阜平时天刚黑。过了几天,技术师来了,在胭脂河边设计了一个水电站,把一个汽车发动机安放在河边上,就可以发电了。但这个电台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设备不够完善,所以质量也不太好。
进城当“干部”
进城前,我在华北电专(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8年成立)学习,晋察冀通信联络处处长钟归祥兼任电专校长。我所在的班,全是高中以上学历,还有一个是东北流亡来的大学生。这个班叫电信工程班,学制相当于大专。后来西军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简称)给我们颁发了文凭,把我们算到它的历史上去了,这个学校一直可以追溯到开国中将王诤,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当时班里共有14个学生,除两个留校外,其余12个全部调出。这一批又分了两拨,每拨6个人。一拨是准备去天津的,在天津周围等待解放。我们这一拨是等着进北平的,当时就在石家庄附近的仓库里头,住了大概有一个月,中央军委三局的队伍才开过来。我们就合并到军委三局,跟着队伍一直走到良乡,等着北平解放后进城。
举行北平入城式的第二天,我们进城了,负责接管国民党第七区电信管理局。我那时很年轻,进北平时才20岁。因为干部数量少,我也变成了“干部”,去接收一些单位。七区电信管理局下设七个电话局,七分局最小,由我来接管。七分局在鲜鱼口对面那条街上,是一个人工局,有很多接线生。我进城后一直在那儿工作,当时局里还有一个老罗,负责总的事务,但他主管工会,我是管业务的。虽然在工程班学了有线电、无线电,技术理论都懂,但说到管理,尤其是管理一个电话局,我就摸不着门了。可那时候胆子大,懂不懂也得管,每天看看报表什么的。虽然一知半解,也学了不少专业的东西。
我在七分局呆到1949年3月中央进城,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进城后,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驻地,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为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时任北平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的王诤指示,务必在3月23日前建立通信专用局。于是,北平电信局职工和军委三局电话队的同志,加紧筹建香山电话专用局,地址选在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此时,我调到香山。3月10日装机工程正式开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全力以赴,夜以继日。3月23日,“香山电话专用局”建成。
那时有个同志叫彭润田(后来曾任北京电信局副局长),当时是三局的一个老同志,起初是他在那管着。后来,组织调他到八大处三局总部,就让我接手。一开始还没正式交接,我到那里后先协助他做一点工作,有时当当接线生,有时还装装电话。因为是学机务出身,装个电话机我还是挺灵的,就主动争取这样的机会。后来彭润田说:“小蓝,你愿意去就去吧。”
借装电话的机会,我见到了几位首长。首先装电话的是朱德总司令家。朱总司令和我握握手,问我:“你这装的电话是什么电话呀?”我说是半自动电话。他说:“半自动电话怎么使用呀?”我说:“要是内部电话,有个号码,您就可以直接拨了。您要往外打呀,还是要转人工的。”“哦,是这样呀,这比原来好了。”朱总司令旁边住的就是任弼时。在他家装电话时,他没问我怎么弄的,就看着我装,装完之后对我说:“啊,你走啦?谢谢呀!”后来,我还去过刘少奇那里,他住在半山亭。那天,刘少奇正好不在家,我没见到他。我很荣幸见到了任弼时,因为他去世早,以后再没机会见他了。
后来,我调到东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电讯修配厂。早期在北京参加革命的这段经历就此结束。
(口述者:蓝文长系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蓝公武的女儿、段苏权将军的夫人。1928年10月生于北京,1945年7月参加革命,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曾参加北平市和平接管工作,后调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电讯修配厂。1952年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雷达专业进修五年,先后在军委通讯部南京电讯修配厂、军委通讯部雷达局、福州军区国防工办工作。1975年10月调入海军,历任海司雷达声纳部部部长、海军装备技术部电子部部长,1985年起任海军装备技术部调研员、海军科技委常委、海军装备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离休。)
整理者:陈丽红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