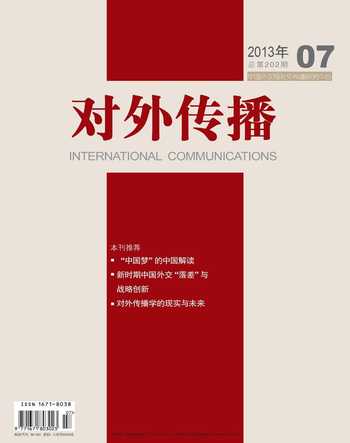“这简直就是中文!”
郑若麟


每次从法国回国休假都有人问我,法国人怎么看待中国和中国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一言以蔽之。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进入互联网和智能通讯时代,北京和巴黎之间只有1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要是法国的“协和号”超音速飞机没有停飞的话,那么至多3个多小时足矣。令人遗憾的是,法国人同其他西方人一样,对中国的了解似乎依旧停留在遥远的过去。我想,这倒不是他们对中国不感兴趣,恰恰相反,法国人渴望了解中国的一切:他们想知道,在他们眼中神秘的东方,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中国人的爱与恨,中国人的个人气质、集体意识、逻辑推理方式又有何特殊之处?中国经济增长领跑全球,却为何让世界害怕?面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人如何应对?他们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世界?
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法国驻华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中国驻法记者人数。问题是,尽管他们表现出欲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强烈意愿,但我对这些法国同行的能力甚为怀疑。
“这简直就是中文”(Cest du chinois ),是法国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说:“这简直难以理解!”我从一开始学法语就接触到这句话。
“女人就是中文,实在太难理解。你们能懂吗,反正我不懂……”
这是法国歌星甘斯布尔格一首著名歌曲里的歌词。由此可以看出,甚至在号称“天生情圣”的法国人眼里,中国人(乃至中文)居然如此复杂,甚至比之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向记者透露,他甚至在每天早晨对着镜子刮胡子的时候,也念念不忘自己有朝一日要登上总统宝座(对镜刮胡子寓意萨科齐似乎看到了镜中的“未来总统”),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是反躬自问,剖析自己的真正品性,这恐怕与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不无关系。中国不停地翻译外国人写的、号称剖析中国人个性或点评中国人生活习俗的书。这里可以提及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阿兰·佩尔菲特的《当中国觉醒时……》、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罗素的《中国》等等。
我们甚至还热衷于将中国人为外国人写的、在外国出版的有关中国人的书翻译成中文!三个名字即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陈季同、辜鸿铭和林语堂。林语堂堪称一位伟大的作家。在70多年前的上海,即1935年6月,林语堂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吾国与吾民》。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当时在美国,介绍中国的书可谓凤毛麟角。人们很难读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行为、家庭观、政治制度,以及分析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书。由中国人撰写的此类书籍更为罕见了。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鼓励下,林语堂直接用英文撰写《吾国与吾民》。《吾国与吾民》甫一出版即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前四个月就被加印7次。在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本畅销书成了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圣经”,影响了不止一代美国人。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待该书的态度。《吾国与吾民》问世后,中国先后出现过五个中文译本。最近的一次翻译是1995年,号称是《吾国与吾民》惟一完整的中文版!诚然,中国人在1936年第一次将此书译成中文时,主要是想核实一下他们的同胞是如何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然而,在1938年第二次翻译此书时,《吾国与吾民》已经被当作一种珍贵的工具,供中国人用以自我剖析。它证明了中国人确实一直热衷于自我和彼此之间的了解,以及对能够代表我们全体中国人之精神的理解。意欲理解这种现象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就必须在脑子里时刻铭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精神是通过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地理和极为复杂多样的特质而形成的。就如同一个巨大的、不停演变之中的大拼图,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面貌,就必须坚持不懈地重新组合这幅拼图。1949年后的将近30年间,中国人努力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如同一句法语俗语所形容的那样,“我们试图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
尽管林语堂的书早就被翻译成法语,而陈季同直接用法文撰写的书籍在近两个世纪以来也不断再版,但当法国人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时,依然会惊呼:“这简直就是中文!”如今,西方人关注的已不再是昨天的中国,他们着迷的是眼下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是他们难以解释其真实意义的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往往笼罩在矛盾的表象之下。简言之,法国人希望解开中国之谜,法国人渴望了解的是“此时此刻”的中国。
在林语堂生活的年代,关于中国的书寥寥无几。任何一个西方人只要懂一点中文和背几句中国诗词,就会被捧为“汉学家”。如今,中国成为西方国家长期研究的课题。书店里无数所谓专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书籍。我尽可能地翻阅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说确有上乘之作,但大多数是平庸凑数之书,还有一些则可称之为“卑劣”。这些良莠不齐的作品,让我更加坚信阿兰·佩尔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里所引用的那句极为中肯的引文:“没有比按照西方人的标准去评价中国而更有欺骗性了。”
令人备感荒谬的是,这句睿智的评论居然来源于当年英王乔治三世派往中国的首任使节马戛尔尼公爵。当马戛尔尼公爵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中国后,却固执地拒绝在乾隆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阿兰·佩尔菲特认为,这次会见是中西方文明之间首次富有成效的相遇,而这一历史机遇却恰恰由于马戛尔尼拒绝“磕头”而被错过。这位英王使节认为,中国的“三跪九叩”礼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因此,他不仅没有按自己的那句名言去做,当然也就不可能完成英王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了。
我在阅读外国汉学家的著作时,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比英王乔治三世特使更高明些的判断力。一旦他们试图走出有关中国的泛泛之论,接近现实的、真实的中国时,他们就拒绝应用马戛尔尼告诫过的箴言。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用固有的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偏见或成见毫无意识,因而缺乏足够的宽容,并以谦虚的态度来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我的职业经验告诉我,当分析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时,不应以中国标准为出发点,必须考虑整个事件形成的特殊性和不可比较性。否则,就可能做出欠谨慎的评价。西方人要理解中国,同样是这个道理。

其实要理解中国还有个简单的原则:如果放弃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话,中国以前就是、现在仍然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或者说是一种与西方文明并行的另一种文明。不仅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因素,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观念恰恰相反,始终将人际关系,特别是家族置于社会中心位置。在宗教领域,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一神教的世俗大国。至于儒教和道教,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另外,要理解中国,必须不忘另一个中国精神原则,即“天人合一”思想,这是很难在别处找到的。
从中国的表意文字来看,“天”这个字应该理解为“大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概念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西方精神中不是将上帝就是将人放在一切的核心地位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如今西方社会出现不久的环境保护学说和绿党政治相比,中国两千多年前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包含了环境保护观念。
此外在几乎所有方面,甚至包括国际关系领域,中国不断地呈现出与其他亚洲大国的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像印度那样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也没有像19、20世纪初的日本那样站在殖民列强一边去侵略他国。总之,中国自有史以来从来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因此,用平常的方法来理解这样一个国家似乎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如何理解中国?
近年来,法国大多听说过或读过《中国已觉醒了》①、《当中国改变世界》②、《当中国崩溃的时候》③…… 仅法国人撰写和出版的书籍就有几十本之多,中国题材显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过,如果说林语堂在其著作里描写的是中国人的性格、文化和传统的话,法国作者则极力解释中国人是如何享受突如其来的现代化生活;为什么中国人能轻易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张开双臂迎接全球化的到来。
所有这些书都在向我们介绍当代中国在伟大变革中的一些方面,虽然不全面但却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我还要写上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呢?理由很简单:上述那些书中缺少了一个内容: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西方人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但中国人是惟一的“缺席者”,看不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优点与过失、成功与失败。这种现象非常容易解释:即使是略懂中国现实的法国作家,还不具备写一本关于“中国人”书籍的能力。为什么?这正是我下面谈到的问题。
每年,除了几十万游客之外,绝大部分法国人并没有机会像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中的主人公——记者丁丁那样常年到世界各地旅行。大部分法国人只能借助于法国驻华记者的眼睛看中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法国人在阅读法国驻华记者撰写的文章时,并不知道这些记者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懂中文!④ 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在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记者都能讲流利的中文。而在法国外交部注册的30多名中国记者,除了两三名摄影记者外,都是能讲流利法文的“法语人”(FRANCOPHONE)。法国人的外语能力之差欧洲闻名,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在法文里没有“汉语人”(SINOPHONE)这个词!如果没有掌握驻在国的语言,做好驻外记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法语是一种严谨、抽象的语言,中文较直观而形象。两种语言不可能相互替换。因此,我为法国媒体写文章,包括撰写此书,都是直接用法语写,即便寻求帮助也在所不惜,因为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一种语言背后总是包含着其历史和特殊的文化。所有掌握两种语言的人都知道翻译是多么具有欺骗性。而且,在法语和汉语中,难点和陷阱又比其他语言多出百倍!
比如:法国人或笼统地说欧洲人在形容中国时经常使用的一些词“专制”、“极权制”、“独裁”、“寡头政治”、“暴政”、“君主专制政体”……欧洲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分这些词的含义,因为每个词都包含在欧洲历史中,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立刻就能理解。但是如果将这些词翻译成中文就很难。查阅任何一部《法汉词典》就可以看到:法文的“专制”、“极权制”、“独裁”、“寡头政治”、“暴政”、“君主专制政体”……所有这些词翻译成中文都是同一词条:“专制”或者“独裁”。道理很简单: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这些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实际上几乎可以说只有一种政治体制。
一次,我在巴黎同两位法国教授一道出席一场关于中国的辩论会,他们分别阐述了各自对中国政治体制本质的看法。一位教授说,尽管中国内部发生着深刻而迅速的变革,但中国仍然是独裁体制。另一位教授则表达了对这个观点的不满,认为中国体制今后更多属于专制体制。前一位教授用的词法文是dictature,中文法汉词典在此条目下是这样解释的:专政、独裁。而后一位教授用的则是autocratie,中文法汉词典在此条目下的注释是:君主专政制度, 专制政体, 独裁统治。在中文里两者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在法语里,两者所指却非常明确,且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前者dictature源于古罗马,指的是罗马公民大会在非常时期(如战争)将共和制下的权力交付给独裁官初选独裁统治,后延伸含义为一个或一群人拥有绝对权力,通过暴力进行统治;后者autocratie则意为君主自授最高权威(如俄国沙皇),起初意思相对于神权,后延伸为一个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因此,当法国人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与中国人截然不同。
再举一个例子,这次涉及的是象征领域。“龙”成为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时使用或者说“滥用”的一个字。龙出现在书籍、图画、照片、电影,甚至日常谈话里。电视播放关于中国的节目时,标题是《中国:龙的胃口》。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书定名为《混凝土做的龙:中国城镇革命及对世界意味着什么》⑥。有一本分析中非关系的书叫做《龙与鸵鸟》⑦。但令法国人意想不到的是,将中国“龙”字翻译成法语词“德拉蚣”(音译)是个典型的误会。
中国“龙”大概是中国原始先民的图腾之一。那时,因无法解释一些气候与天气现象,祖先们便想象出一种虚构的动物,这只想象的动物长着鹿角、骆驼头、乌龟眼、鱼鳞、虎蹄和隼爪。它能改变体形,时隐时现,上天下海,无所不能。所以,“龙”能呼风唤雨。欧洲的龙“德拉蚣”和中国一样,也是想象出来的。它也同样有鳞、角、爪,它也能飞。不过为了飞行,欧洲的“德拉蚣”求助于蝙蝠的翅膀,而中国龙却无翼升天。两种“龙”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西方“德拉蚣”不会呼风唤雨却能喷火,而中国“龙”则不会喷火,但会下雨。
尽管两种“龙”形似,但在东西方传说中所代表的意义却迥然不同。在欧洲传统中,希腊神话里的赫斯珀里得斯花园里,“德拉蚣”是一种有害、残暴、具有侵略性的动物,它毁坏土地、焚烧村庄和庄稼,是邪恶的象征。中国龙则代表了善良,是吉祥的动物,是9个孩子的父亲,是百姓的保护神和海龙王。龙与中国传说中的其他三种动物被称为“四圣兽”。根据中国的民间传说,龙曾力助中国第一个皇帝——黄帝战胜了凶残的敌人,故几千年以来,龙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国人确信皇帝是“真龙天子”,是真龙下凡来统治他们。上世纪80年代台湾音乐人创作的一首《龙的传人》成为全世界华人传唱的脍炙人口的歌曲。
试想,如果不借助汉语,怎么能让西方人理解他们的“德拉蚣”与中国“龙”事实上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因此,错误的翻译足以将中国“龙”和西方“龙”描写成相同的东西,且完全混淆了事物本性,给人造成错觉,即中国人崇拜一种不吉祥的动物!我坚信,即使当法国人了解了事实真相,但集体失聪的影响是如此强大,导致中国“龙”的形象在他们的脑子里仍然是负面的。
西方人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遇到的困难显然是多种多样的。不懂中文是困难之一,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不掌握语言,就必然缺乏感性认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写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他们却很少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交流,那很难与对方保持互信的关系。(何伊译)
「注释」
①阿兰·佩尔菲特:《中国已觉醒了——邓小平时代记事》,法国法雅尔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埃里克·伊扎尔维茨:《当中国改变世界》,格拉塞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③章家敦:《当中国崩溃的时候》,兰登书屋,2001年出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与许多美国汉学家一样,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却不会讲中文。
④我曾经核实过,目前法国在中国有57名常驻记者,而会说中文的人不到一半。
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中国人开始组成一些新词,如以“威权”来表达“独裁政体”。但该词表达的意思仍然混乱,且很不确切。
⑥托马斯 J.坎帕内拉:《混凝土做的龙》,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⑦阿达玛·噶叶:《龙与鸵鸟》,马拉喀什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