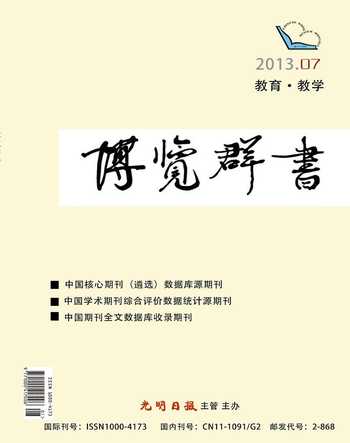人性的坚守与救赎
曹正勇 周娟
摘 要:蹇先艾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的重要代表。在他的成名作《水葬》里,深刻地展现了人性的阴暗:以“伸张正义”的理由高高标榜了他们的伪道德,把自己的官能快感建立在一个鲜活生命的毁灭上。两重悲剧与双重人性的表现,又将“人性的拷问”牵引出来。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和深刻的作家自觉。
关键词:人性;坚守;救赎;蹇先艾;水葬
蹇先艾,这位来自黔北地区的乡土文学作家,经受了“五四”文学思潮的洗礼,坚定“艺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念,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尽管没能从当时浩荡的个性解放大潮中抽离出来,却将写作焦点从城市浮华不安的现状移至遥远的乡村和乡民。这种关注,远非一种眷念式的叙述,而是一种自省式的理性反思。在他的小说里,始终有一种毫不夸张的切肤之痛。这种痛,隐藏在对遥远偏僻贵州山山水水、人文景观和人情风俗的描写叙述中;体现在对故乡落后残忍恶俗及乡民愚昧的批判和讽刺里。这种不可抑制的情感,在他的成名作《水葬》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小说讲述了一位青年农民骆毛因为偷窃被抓最后被村人按照风俗处以水葬的故事。小说通过骆毛的赴死和母亲的等待两条线索缓缓展开,人物和情节都朴实简单,却展现了遥远贵州的残酷愚昧和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生存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具有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小说描写的对象有四类:绅粮周德高之流,骆毛,看骆毛赴死的村民(包括朱三媳妇及她的儿子)和骆毛之母。小说对骆毛前往“刑场”的描写,让作者与读者之心灵与底层民众炼狱般苦难的生存现状来了一次正面的撞击。对于“水葬”,骆毛应该是有心理预期的。虽然赴死,骆毛也就显得具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但兄弟王七的话,让他不得不想起自己的母亲,于是先前的“硬汉”形象被解构出来,不怕死的心情,冷了一半。开始担心自己死了之后母亲无人照顾。此刻,“硬汉”没有了,却重构了一个孝子形象。由此看来,骆毛物质上的贫困导致了他偷盗行为的发生,但并没有泯灭人性的存在。
同行的人,除了押解的家丁,还有“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服装,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在他们看来,对偷盗者进行极刑,是冠以“伸张正义”和遵循祖宗遗训的道德之名的。对以周德高为代表的有权有势之人,所谓“伸张正义”,已成为他们捍卫自己利益的借口。所以对骆毛进行“水葬”,是想通过骆毛的死警示梧桐村的乡民。所以在骆毛赴死的路上,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是他们所期盼的。否则,一次偷盗,且没有成功,何以处死?他们的计划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样的处置在村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在作品中,村里人对骆毛因偷窃而被处死并无异议。他们对骆毛施予了精神“暴力”,成为了助推骆毛死亡的帮凶。因而骆毛个体生命的终结便带有了宿命的色彩和无法摆脱的悲剧性。
人,往往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总要把另一些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作为被毁灭的对象。文中的骆毛,便成为了这样的牺牲品。他独自一人生命的消陨,精神也随之消逝,况且他也没有精神可言。倘若有,便是他赴死的那种从容——“再过几十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汉吗?”但他的毁灭,在周德高之流的眼中,是维护和捍卫了自己在梧桐村的权势和地位。他们认为,骆毛的死亡同时也是拯救了梧桐村所有村民,尤其是一路不辞辛苦跟到小沙河看熱闹的人们。即以个体的毁灭来换取群体的新生。这是一种高高标榜的“伪道德”,是对人性良知的“文明”践踏。
更悲哀的是,所有追求热闹的人们,似乎与骆毛无任何关系,仿佛已成为正义的化身,将最终见证“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瞬间。素不知,他们并没有比骆毛高贵,他们的“正义”行为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旧社会作为社会底层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但最终他们还是以骆毛无法抗拒的力量结束了骆毛年轻的生命。骆毛是无法用身体去反抗的,甚至于在他的心灵深处,偷盗被罚是应该的,甚至于被“水葬”也没有出乎他的预料。唯一出乎预料的,是他的即将的死亡成为了村民快乐的源泉,所以他愤怒了“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这样阿Q式的呐喊,只是表达不快罢了。骆毛被“退佃”,还以“偷盗”来表达反抗,而他们却认为“反抗”是扰乱了梧桐村原来的生活秩序,是不能安分守己的表现。所以最终骆毛心理上那一点点难得的反抗意识也在众人“正义”的威逼和麻木不仁下显得苍白无力了。所有看客们在欣赏“水葬”的“壮观景象”之时,却不知道他们也是权势之人眼中的“被看者”。同是看客,村民们关注的是获得肆虐的快感,而权势之人关注的更有骆毛的死亡能否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维持和巩固他们已在梧桐村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但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倘若被水葬的不是骆毛而是别人,骆毛会不会成为众多看客中的一个?与此同时,众人却也不明白,或许有一天,他们也将和骆毛一样,成为证明其他看客“正义”的物品。也许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正义”是什么。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那就是看“水葬”可以获得官能的刺激与享受。这也是他们不辞辛苦的真正原因与动力。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他们从不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被看的对象,只要能获得官能的享受与欲望的满足。而且因为如此的享受与满足出于生命的本能,所以,只要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这种享受与满足的事情还会经常发生,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骆毛沉落下去之后,“天空依旧恢复了沉闷的铅色,梧桐村显得格外冷落。”其实,冷落的,不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梧桐村,而是梧桐村内心冷若冰霜的人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骆毛的死,会给那样一位“住在孤独立在半山坡上的茅草房里,身体非常虚弱,脸上堆满了皱纹,露出很高的颧骨,背有点驼,头发斑白”的老母亲带来什么。难道也是要“拯救”这样一位孤独无助可怜的母亲吗?如果说周德高自行处死骆毛是出于权势,那么,所有村民对骆毛被处死“毫无异议”是出于什么?是因怕势而苟且偷生,还是遵循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这是人性的哀痛,还是文化的哀痛?但不管怎样,那位老妇人依然努力“摩挲着老眼,不转睛地向着远处凝望”,等待儿子骆毛的归来。然而最终等来的是朱三媳妇对她的善意欺骗和末了的深深叹息——“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尽管母亲并没有见到骆毛的最后一面,但从她在朱三媳妇面前独自的咕哝里“毛儿他从来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回家的,到哪里去了啊?”我们可以推测,老妇人心里是有隐隐不祥的预感的。她那份伟大的母爱却在作者创造的无望的等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笔者认为,作者有意为之,表面是给母亲一种“等待戈多”式的不确定, 实际是一种不知道的绝望。但这样一种善意,却成为了对那位母亲的残忍。所以,鲁迅曾经这样说过:“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无论是朱三媳妇的有意说谎,还是作者创设的非团圆的结局,都是在有意表现人性善良的同时无意走向了人性的另一恶端,永远走不出二元悖逆的怪圈。如果那份善良没有沉睡或者没有死亡,骆毛也许能得到另外一种保全生命的惩罚方式。但遗憾的是这仅仅存在于假设中。骆毛终究还是没有逃离死亡。但死了便死了罢,母亲却因为众人的“善意”而不知真相只能在无望的等待中唉声叹气,或许到生命结束,她也不会知道儿子骆毛已经沉于水底。这是不公平的,正因为这样的不公平,作品的悲剧性显得更加的浓烈。
所以,作品不仅表现了梧桐村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人和特殊的风俗,还窥斑见豹地表现了整个旧贵州的人文风貌,正如有人评论作者时说的“用西方人道主义的眼光去反观贵州内地生活”。它有别于都市的乡间世界,亦不同于其他乡土作家笔下的乡土。作者把个人的情感完全融入了这块让他流连的土地,通过对这块土地特性的张扬和表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地位。表达了与时代相吻合的特有主题,不仅指向对局域落后习俗和精神麻木的批判,更是对共通的深层人性的揭示与批判。人们往往在出于人性善意驱使的同时做了非善的事;常常在拯救自己或者他人的同时将另一些人推入毁灭的深渊。这是善还是恶?或许人性的悖论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怎样做,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值得思考的。所以,梧桐村不仅仅是贵州的梧桐村,更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作品的广度与深度,借“人性”的纽带紧密相连。正如它所表现的,是要从视生命如草芥的习俗里拯救人们,还是要人们扬弃这种可怕的习俗。或是在拯救人们与扬弃习俗间寻求兼顾各方的另一条路?
从作者的经历来看,当年他若没有融入代表中国最高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大都市,接受民主主义思潮的洗礼,他就不可能以人性关怀的眼光和立场去审视这片乡土上原始的习俗和世态。所以,《水葬》的成功,源于作者本真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国边远省份依然存在着的野蛮风俗。作者的这种不满之情,流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乡民们非但没有认识到,反而浸染其中,成为这种风俗“发扬光大”的推手。素不知,他们生活困苦与落后的根源是经济的不发达。因而也不可能寻找到一条变野蛮为文明,化愚昧为智慧的正确之道。面对这样的人与事,作者除了展现强烈的憎恶,只能对骆毛的非命表示深切的同情。并通过骆毛阿Q式的反抗完全展现出来。由此看来,怎样改变这种吃人的风俗,作者是做了思考的。正因为这种贴近家乡的思考及兵荒马乱的现实,使得许多作家不免心生“月是故乡明”之感。对故土的无限思念让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小说里,作者充分地展现了落后愚昧的乡民被蒙蔽甚至被扼杀的人性。不仅仅是老人和妇女,就连儿童和襁褓中的孩子,也成为了给骆毛“送葬”队伍中的一员。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就在看热闹的路途里被静悄悄地销毁了。因而,骆毛的死,不仅仅是对一个生活无所依靠的母亲的伤害,还揭示了梧桐村里人们“爱”的伤疤,有些鲁迅“救救孩子”的意思。然而,像骆毛一样无知而又无意识的农民,在过去的贵州和中国里,是随处可见的。所以,骆毛的悲剧也便有了普遍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作者不仅是站在经济物质的角度去审视偏僻遥远的贵州,更是从精神自觉的层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给予理性的观照与思考。因此,作为像蹇先艾这样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文字引起人们对“民众精神救赎”的关注,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是《水葬》,还是作家其它的作品,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对底层民众的关照促使他们获得人的解放。尽管他们的作家自觉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种呼喊,应该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蹇先艾代表作——水葬[M].华夏出版社,2009.
[2]杜惠荣、王鸿儒.蹇先艾评传[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曹正勇(1981-),男,贵州普定人,贵阳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文化与语文教育。
周娟(1982-),女,贵州贵阳人,南明实验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