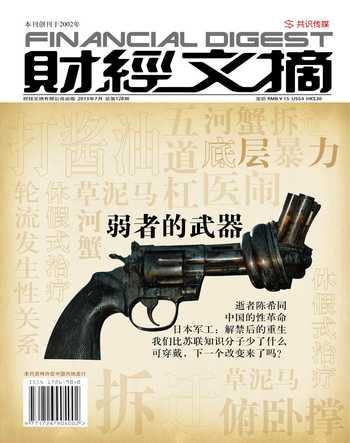大悲之声
李俏云



鲁迅曾言:“沉痛至大之声”。此语遭逢杨大飞呕心沥血二十三年创作的《荷殇》组画,一语成谶。
《荷殇》组画中的荷花,丽质妖娆,却备受摧折,生命的盛开与绽放,紧紧伴随着的却是死亡的骤然与狂暴。荷之殇,之痛,之悲,充塞于画幅,激荡于心宇,深长旷久。可以说《荷殇》描绘的正是生命悲怆之声。
解构“荷”
抵挡如注的雨箭 你的身躯
狂烈地扭动 扭动
你火焰般腾跃的舞步啊
似呼啸的飓风
你颤栗的激情 令疲惫的日子
警醒
即使在搏斗中像一杆战旗
倒在
血泊里 荷
你那不屈的笑容 珍藏于
历史滴血的心灵
——诗人孟倩
荷花,自古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在中国的古典想象中,有“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之清丽,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高洁,有“莲花台,严净香妙可坐”之禅韵……很少有人将其与苦难、牺牲和悲怆联系在一起。
然而,当你面对杨大飞的《荷殇》组画,却自觉胸中块垒无法纾解,荷之古韵荡然无存,爆裂焦灼的受难形象取而代之。
组画以萧瑟的秋风、迷离的长空、如注的暴雨以及残破的荷叶、枯死的花朵等诸多景观,营造出一个苦难的世界。荷花形象或者是皮开肉绽、血痕累累;或者是匍匐在地,在痛苦中死去……置身画展展厅里,几十幅荷花仿佛在呻吟、在呐喊,如同面对着一场屠杀。有人用“悲怆、苍凉、沉雄、激越”八个字评论杨大飞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
“回眸过去的20世纪,大大小小的运动、事件、斗争乃至战争充满了百年历史的每一天。持续性的社会动荡伴随着的是社会暴力,暴力中的胜利者戴上争议的光环,失败者沦落成一切罪恶的背负者,我脑海中始终勾画一幅图景,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苦难。我想办法将这个体现出来。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写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后几十年,描写整个民族的心灵创伤,是对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审判。他的创作观启发了我。”不同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用小说针砭时弊,杨大飞以画笔勾勒苦难。
“传统中国画讲究意境和留白,个体意识是缺失的。我不喜欢太过空灵的状态。我的画看起来很满,我喜欢有视觉冲击力。”
进入21世纪,杨大飞的作品主题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红色铺满了画面。如果说早期的《荷殇》表现的是肉体的伤痛,后期的《荷殇》则是精神上的、内心的苦痛,但是又是内敛的、平静的。
《三藏法数》中将荷花与菩萨的“十善”作比,离诸染污、不与恶俱、戒香充满、本体清净、成熟清净等风姿均在列内,杨大飞后期画面趋于平和深沉,悲悯、博爱的情怀流露出来。
建构“殇”
世上所有的花儿全都绽放了,
却迎来了他的死期。
可是一个简称大地的行星,
骤然变得无声无息。
——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
未家短折曰殇,《周礼》中这样解释“殇”,与《荷殇》之“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美学追求意境,残荷一般象征着文人士大夫出仕、伤感的一种心绪,一般意义上都是枯荷,自然死亡。我这里的‘殇意指没长成就死,是夭折。创作的过程中想到这个词。”杨大飞说道,荷,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美好事物、君子、烈士;殇,就是死亡、夭折,是年轻的生命进程的突然中断。
《荷殇》系列是杨大飞绘画的一个持续性主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中他完成了六十多幅《荷殇》作品。荷花的生命形象是高洁玉立的,是丰韵饱满的,而杨大飞所画的荷花却是将最有活力、最具魅力的生命形象突然放置于一个摧折状态之中,鲜活的生命在险恶的环境中死去,仿佛时间定格在了瞬间,把受难、牺牲这样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还原成画面,让人充分、详尽地观看到死亡的细节,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死”,获得了形而上的生命意义。
事实上,从“荷之殇”到“人之殇”再到“社会之殇”,这才是画家20年来纠结于心的命题。
“对于‘殇这一悲剧,作者并没有政治道德判断,没有是非、善恶的裁决,只有审美意识,只有生命所负载的美与尊严。由荷花这一美丽生命所呈现的生命的形而上意味,是对人类生命体验模式的某种普遍性意味,通往博爱。”艺术评论家帅好认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用一组画,用二十三年的时间来描述一个事件、一种理念的升华和变革。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的艺术多是政治的附庸,只能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或者成为市场的俘虏而出卖自己。即便是在艺术本体问题上,也是以“情趣”“意境”等取代艺术本来应有的担当和使命,把严肃的审美变成了“把玩”。从这点来看,《荷殇》组画无疑具有空前的意义。
“多数中国画,充满道气,无为至上,没有担当,从有记载始,很少表达真相和事实,更多是风花雪月,抒情玩赏,对现实苦难总是逃避,越逃越远,这种逃避的脚步,在《荷殇》这停下来,才有可能调转方向再前进,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理过程。”杨大飞在长达二十余年时间里,孑然孤寂,创作不止,在“一次关于树的谈话也几乎是一种犯罪”的时代,通过画笔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坚守艺术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