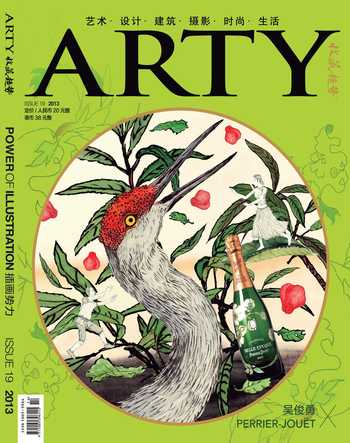贼喊捉贼
吴梦

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相恋的七八年里创作了一系列挑战自我,挑战艺术极限的作品。他们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讨论如何“赤裸裸”地接近人的内心。这些不只是艺术家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更能让人从中找到应对周遭不堪世界的勇气。
最近,乔治·奥威尔完成于1948年的小说《1984》销量猛增。这本当时的未来小说虚构出小人物温斯顿先生生活在一个监控人们一言一行的“大洋国”里。对照现实新闻每天现场直播的“棱镜门”,有人揶揄,是该夸奥威尔先生有先见之明呢,还是笑骂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创意。不知奥先生的在天之灵此刻是何感受!无论奥巴马带着狡辩和恐吓对美国民众说,“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和100%便利,”之后,他还要加上一句,“当然这需要在司法部门的允许之下。”可见他也害怕自己的道德受到质疑,被媒体冠上“贼喊捉贼”此类的标题,为他的政治生涯留下污点。
此类的事情到了艺术中会怎样?我来讲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地点是在柏林。故事的主角是艺术家恋人乌雷、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一幅油画。话说有一天,乌雷在柏林新国家美术馆看到一幅1839年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尔·施皮茨韦格的作品“贫困的诗人”。它曾是德国最为传统的油画,描绘了一个贫穷的诗人在阁楼里裹着毯子,瑟瑟发抖。他的头顶打着伞,以免屋顶漏下的雨把自己打湿。还焚烧自己的诗稿取暖,苦苦寻找灵感。据说这位艺术家及这幅画都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当乌雷看到这幅象征德国分裂,并经由希特勒堕落成法西斯主义的绘画竟然悬挂在本该安放现代主义作品的地方时,他的心里涌现了一个主意。
在经过了几天的踩点后。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一起进入美术馆。她带着一架摄像机和两卷录影带。设计让保安离开展厅后,乌雷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钢丝钳,剪断了挂“贫穷的诗人”的钢丝。警报响起,乌雷夹着画就跑。阿布拉莫维奇拍下乌雷跑下楼的样子,一堆保安也跟着他穿过大厅。他的长腿跑的很快,飞快地出了门,跑进大雪中,钻入逃跑用的雪铁龙汽车急驶而去。而此刻的阿布拉莫维奇迅速在保安和警察到来之前,替换了磁带,并把它好好的藏了起来。此刻,另一台车上还有一组摄像镜头在对着乌雷。画面中,乌雷驶回克罗斯堡(这里三面环柏林墙,是为土耳其移民划定的犹太区边界),跳下篷车,又走入一幢公寓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那样,敲开了一个土耳其家庭的门。他径直走向壁炉,取下一幅粗劣的油画,把“贫困的诗人”挂了上去。这件历史性的作品被挂在了德国最封闭社区的一个移民家庭里。至此,乌雷希望介入“当代艺术、种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作品终于完成。他打电话给新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告诉他哪里可以找到他们的画。馆长和警察很快赶到,乌雷也被逮捕。他身上带着几天前起草的声明,宣称这只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是简单的偷窃。
第二天,当地报纸头条或嘲讽或调侃地报道了这件事,标题写着“左派激进分子偷了我们最美的画”、“一件有关艺术盗窃的行为艺术”、“画家的朋友拍下这次抢劫”。如果要拍成好莱坞大片,这也绝对是个好题材,里面充满了成功电影的要素——俊男美女的爱情,才情卓越的艺术家,紧张却不失风趣的偷窃故事,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还有艺术和种族问题点缀其间。然而,抛开这些。最值得称道的是,乌雷用自己的行为开拓了艺术的可能性,并做到了极致。有艺术评论家称,乌雷的这件行为作品“艺术的违法接触”,更深广的拓展了它的伦理暗示。
突然有些同情起小伙斯诺登来!我同时在你和乌雷身上感受到了浪漫、刺激和英雄主义,还有最可贵的个体与政治之间的博弈。不同的是,你不是艺术家,你做的也不是行为艺术。但我相信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你已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同我最尊敬的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