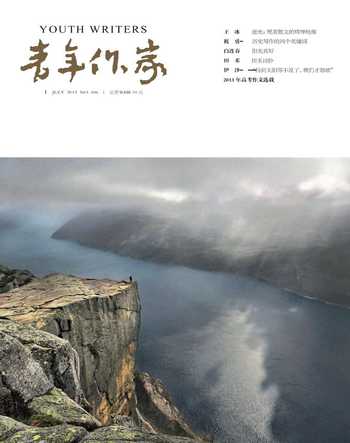模糊的车厢
黄啸
五点四十,他终于让一辆班车带走自己。他不知道它开往哪儿,也不需要知道它开往哪儿。终点的不确定性,会让旅途染上淡淡的感伤的紫色,那可爱的小指头(我有这样的经验),将抚摸他的每一寸肌肤,最后会准确地抚摸到他的耳廓,它柔软、富有弹性。当他沉醉并感激于那小小的感伤时,指头将被允许一步步探进他的身体,抚摸那些突然莫名悲伤的内脏。
一个乘客歪着头,睁开快要牵出蛛丝来的眼睛,斜了他一眼,旋即闭上,掩上车门,像是某种责怪。仿佛他的加入破坏了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平衡,现在,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把搅动了的空气重新安定下来。看样子是长途客车,应该是,车厢的某个角落响起的轻微鼾声正被左边角落的粗浊的鼾声呼应。这是冬天,窗外渐渐黑下来,田野和树木飞跑着追赶远处落日的钟声,它们的背影越来越暗淡。风紧贴车窗,手爪抓扯着玻璃,仿佛已经抓出了十道深深的凹槽。寒气从凹槽渗进来,他抱紧自己。
下午的阳光真好。睡眠的传染病,从同座昏睡的身体里爬出来,悄悄爬上他的眼皮,在汽车反复的摇摆和颠簸中,他终于像睡着了。也许还顽强地醒着,但闭上眼睛是如此放松并且享受,世界一下子在身边睡着了消失了,再也不需要分一只手照看它们。他久久闭着只属于自己的两只眼睛,全身心地感念着下午的阳光,仿佛专注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能将它们召回来一样。那些阳光果然响应了他,慢慢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伴随他惊人的专注力,它们越跑越快,那一刻他想起了读小学五年级时参加的一次跑步比赛,那些在掌声里不断燃烧的小学生总会跑到终点。阳光也终于沿着他修筑在神经上的跑道跑到了终点,在他怀里,一团团阳光像一群温顺的猫,有柔软光滑的皮毛,有微微的喘息,还有热气腾腾的汗水。
此刻,阳光照耀着他,是两份阳光照耀着他。在冬天,这显得奢侈,每个角落、每个器官都洒满了金色的光。香味,应该有一点,至少应该有一点。他记不清了,好像米酒或者干燥的稻草的气息。有点晕,也有点眩,他仍闭着眼睛,把那些柔软的小猫搂在怀里,彻底让自己晕眩起来。他感到身体里的另一个身体,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就在陀螺快要倒下的瞬间,他听见一片融雪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他差点睁开眼睛,但马上回过神来,自己在车厢里,而且川西多年不下雪了。凝神细听,确是融雪的声音,细细地贴着骨头,一节一节地送进耳朵里。那声音卷裹着被解放了的欢乐,潮水般扩展开去,奔向大海的另一个海岸。阵阵温暖的潮湿的浪花泼溅了他一身,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和每一个毛孔。当眼睛也被泼溅得潮湿起来的时候,他的手指告诉他,他哭了。
我不知道这脆弱而羞耻的融雪事件,他从没对我说起,即使在酒醉之后。毕竟,一个四十岁的男人,雪化成水从眼睛里流出来,那被称为“眼泪”的东西,太可耻了。二十岁多好,哪怕三十岁呢,至少有最低度的真实性。四十岁就太不一样了,何况有了白发,可恶的还秃顶。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他一流泪,我的眼睛就潮湿了,我竭力忍住,但那被称为“眼泪”的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如果不是有人敲门,我也许真的就哭出声来了。
他的办公室紧挨我的办公室,玻璃糊了两层报纸,光线减弱,空间就缩小,他不开灯,他喜欢呆在昏暗的屋子里。我几乎知道他所有事情。他只讲事情的轮廓,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塞入了许多省略号。但是,我清楚被他省略的细节,他的眼睛和耳朵会告诉我。我闭上眼睛和耳朵,它们就被某种神秘的电波直接传入我的大脑,令我苦不堪言,在我享受他的快乐和幸福的同时也必须享受他所有的痛苦。睡着了,或者刚从午睡中醒来,我会觉得我和他是同一个人,他是我的影子,也许相反。我也在那辆车上吗?
那些雪一直藏在我的身体里。
儿时,那时候还下雪,每一年都下,每一年都会吞一把雪藏在身体里,我喜欢那冰冷的感觉。夏天,没人的时候就把它们偷偷拿出来,捏成雪团,捏个小雪人,然后再轻轻放回去。每一场雪都堆在那儿,今年的雪压着去年的雪,我像是被雪喂大的。后来,不下雪了,很多年很多年不下雪了,它们知道我玩厌了。童年的积木遗忘在黑暗的积满蛛丝的屋子里,像一堆孤儿,我不再去看望它们,任它们一年年肮脏、发霉。
也许,也下过两次雪,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如果真下过,那时我在哪儿呢?
他说他也玩过雪,守着每年的最后一场雪,直到最后一片雪融化在天空中。每一年春天的第二个月他就开始低烧,夏天烧到四十度,烧成一双红宝石兔子眼。立秋的第一场秋雨后才开始慢慢消退,眼睛渐渐呈现温和的蓝色。头两年还看医生,吃了一抽屉的药,没用;服了许多偏方,找了十个巫婆,烧了比他还高的纸钱,喝了神水,没用。母亲流着泪守着他死去,但没有死。他说冬天就好了。冬天果然就好了。那时,没有朋友,自己和自己玩,雪是唯一的玩具,他说,儿时的记忆中只有雪。
他向我讲诉他的童年和雪的时候,我以为在讲我的童年和雪。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再也瞒不住我的任何事情了;而他,也甭想瞒过我。所以,他的手指告诉他,他哭了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手指,从他眼睛里流出的是不是我的被融化的雪水。但是,那一刻他真的在车上吗?我感觉他就坐在我隔壁的办公室,静静的,一团虚无的空气。或者,是他代替我登上了那辆班车。
天已经全黑了,黑得车厢里只剩他一个人。一辆只有一个乘客的班车,没有司机,没有终点。这辆载满幽灵的班车在每一个站台停下,车门打开,阴冷的风扑住他的腿,像一群饥饿的乞丐。一些幽灵到站了,另一些幽灵钻上来。车门关上了哑巴的嘴。
下午的阳光已经从怀里消失,冷裹挟着那些座椅空出的苦涩,从总是漏风的领口和敞开的鼻孔灌进去。雪化成的水倒灌着,从嘴唇倒回脸颊,倒回眼眶,被眼睛一点一点吞下去,在那间隐秘的黑暗的屋子里重新成为雪,黑色的雪。
我确信,他裤包里的手机没有振动。一上车他就咬牙关机了,怀着对自己的仇恨,像我一样不希望自己被打听,虽然多么想知道自己是否被打听。手揣在裤包里,好像摸着手机指尖就能触摸到黑匣子里不存在的微弱的电波。我看见我坐在他的旁边,太黑了,看不清他悲伤的嘴角。为了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雪,为了某种关乎自己的同情心,我关掉手机,黑色外壳的手机。
他趁自己意志脆弱的时候,开机,随即关上,并且反复开关。这一点,我并不清楚。我会这样做,很多人也会这样做。可能我太有小人之腹了,难道他就没有一颗被绝望折磨得勇敢的心?关掉手机,像个孤独悲壮的勇士,一种由紫色变成深灰色的悲哀,如手机的黑色外壳,光滑、顺手。他的指尖水纹一样波动着被千分一安电流击中的一丝微麻。
车窗外的风终于累了,世界安静下来,缩回到原点。只有他的心在跳动的声音,血液低缓像一头被痛苦和孤独捕获的狮子。他从来不是狮子,我也不是。我和他的身体里伫满了雪,随时会化成水的雪。
那头狮子,被允许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尽情悲伤,它还能被低垂的星空轻轻拍打。但是,他在车厢里,唯一的车灯已经熄灭。他感到自己是一只停电的灯泡。我需要安慰他一个电话,响了,熟悉的铃声。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一长串盲音,深海吐出的一串气泡。我是另一只停电的灯泡。
对不起,我们才了解他一点,就已跟着他走了两百里。但是我必须忠实于他的内向和沉默,这样我才忠诚了自己的木讷。得等着机会,比如现在,汽车的门窗关得死死的,我们小声点,他可能听不见。不过,还要再观察一会儿。
我还想讲讲那头狮子,在他睡着之前。其实,是他讲给我听的。有二十个晚上,他都梦见它,不吃不喝,一天天消瘦,锋利的骨头几乎戳穿它破败的皮毛。他对狮子说,捕猎吧,哪怕捕一只最小的老鼠。狮子悲哀的眼神回答,我要你的雪。那是他很小时候做的梦,他哭着醒来。他说,狮子怎么知道我藏着雪呢。第二十一个晚上,他带着他的雪躺下,闭着的眼睛却始终醒着,直到太阳穿破窗户拨开他的眼皮。从此,他再也没有梦见那头被雪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狮子。
我没有做过相同的梦,听他讲的那个夜晚,我想帮他把梦做下去。天快亮的时候,才在紧张期待的困倦中睡去。真快,那头狮子闭眼就来了,仿佛一直守在枕边;不是从草原的那头跑过来,是从布满星星的天空降下来的,我脸上的毛孔感受到一股热呼呼的野蛮得近乎纯洁的气息。我惊恐地闭紧眼睛;睁开时,看见天花板被雨水浸渍的随时可变的神奇图案。
对此,我抱着强烈的怀疑:是六岁时我做过这个梦呢,还是由于一种友情般的意愿成全了这样的虚构?说实话,我并不清楚这头狮子意味着什么,就像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雪意味着什么一样。《周公解梦》和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我都读过,既没有狮子,也没有雪。也许,要把它们严丝合缝地焊接在一起才能配成一把钥匙。一把可变的钥匙?
好了,他终于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轻微的鼾声在说,你说吧,听见了我当没有听见。但不能说得太多,我的耳朵随时会醒。
他写诗,狮子和雪就有了一把合理的钥匙。似乎可以这样开始,但问题在于,我根本不会讲故事,虽然小说在我的阅读中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比例。而且每读一本好小说,我都会想入非非,来一部小说如何?数不清的片段开始涌进来,在大脑里折腾,只需把它们连接连接,一部伟大的小说就会诞生。但要不了三五天,凌云壮志就会烟消云散,汹涌的片段沮丧地退出去,像溃败的杂牌军退回到一个本不存在的地方。我知道,就算把我所有的废话脏话粗话统统写进去,也写不了那么长。故事真的要命。
他的故事在哪儿呢?
童年,蔚蓝的根须……但它过于隐秘,像一个人的伤口,不希望愈合也不希望被人挖掘。或者像树埋入地下的根,在黑暗中吮吸——那儿有蚂蚁、蚯蚓、死去的蜻蜓和蝴蝶,有他玩过的细沙,捏塑的小泥人早已散开,重新成为泥土混合在众多的泥土里。这仅仅是他童年的碎片,很小的部分,我们都这样玩过。难道它们暗算了他的未来,甚至具体到了某一天,细节到了这个夜晚的旅途?你看他在汽车的抖动中睡得多不安稳。
怕蛇,被袖口的毛毛虫吓哭,谁不是这样呢?打过水漂,玩过陀螺,差点在村边的小河里淹死,吃过笋子虫……这是我们童年的共同秘密。或许,找到他的专利,事情就好办了。那是一条线,从蜘蛛的肚子里无穷无尽地抽出来,他牵着这条线,一直往前走,走到今天,走进这辆不知所终的长途客车。现在,线头握在他睡着的手心里。
我必须沿着线头往回走,但不惊动他。
他坐在晒场上,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偷偷绕到前面,那是一张精致的小脸,身边摆放着几块从河里捡来的石头,青色、圆润、光滑,被手掌摸上一层油。眼睛直盯着前方,像在等那儿走出一头温顺的小兽。
这是夏天,屁股下的混凝土已经着了火,他是一块烤肉,全身正滋滋地冒油。他一动不动,从上午坐到下午,六个小时,什么肉都烤熟了,有一点煳味朝我的鼻孔散过来。我捂住鼻子,把喷嚏吞下去。否则,他会被惊醒。
我惊讶于他一脸的坚毅,那样子有苦行僧几十年才有的道行。但他哭了,哭了五次,哭得现在都难以想象地专注。五个大人走过他身边时都打趣他,想妈了。他们一说,他又哭了。
此刻,他睡着了,梦见了自己的童年吗?那几颗青色的石头呢?但愿没有梦见我偷窥的眼睛。今天我才想到,他的整个童年也许都是坐在着火的晒场上度过的,前方也许真的走出了一头温顺的小兽。
这是他的专利?能构成狮子和雪的钥匙吗?它的雏形,还未炼出铜的矿石?敏感、细腻,坚毅而脆弱,轻微可爱的神经质,蓝宝石一样镶嵌在他身体里,连同那些一年年藏起来的雪,在夜晚发出蓝幽幽的光。
汽车继续行驶,在我窥探他童年的时候又走了五十里,把一座小镇甩在身后。这次,它没有停,怕明亮的灯火惊醒他而快步跑进了深深的黑暗中。那黑暗,荡漾着母亲子宫般的安宁和温暖。
我踩着细细的蛛丝了吗?我得停下来歇歇,把胸口久久憋住的气吐出去。他在车厢里看不见的星星在我头顶闪烁,远远地向着天边低垂。那儿有他的草原,有从他的幻想中走出来的高山,有他涂抹在纸上的大海。这一切像快要活过来的童话,那头狮子正从群星中缓缓降落。
他的手指在裤包里震动了一下,电流从指尖滑走了,就一毫米的距离。他的头侧向右边,嘴唇疲倦地展开,在嘴角收拢,被身体里的另一张嘴咬住。我在请求自己为他分担。一株幼苗长成一棵大树;一个人的童年成长为它的壮年;那巨型灯泡,太阳一样悬挂在空中,它的光无论他走多远都会罩住他。
我直起身,深吸一口气,再深吸一口。这次,我准备沿着细线走得稍远一些。
那年,他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毫无缘由地喜欢上了顺口溜,并给班上每个同学编了一小段,而且无师自通就押准了方言的韵。这诗歌的远亲,是否暗自开启了他的命运之门?教语文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一笑就漾出两个酒窝,灿烂如教室外洒在月季花上的阳光。当老师第二次在作文课上,用糖水浸过的声音念他的作文时,他的脸被二十三个男同学的四十六只眼睛烧得红红的。
后来他想,就是在那堂作文课爱上漂亮的语文老师的。他把这当做自己的初恋,成为做梦也在琢磨一个词语一个标点符号的动力。他像一匹刚配上马鞍的小马驹。把作文写到满分,渴望把小脑袋胀得满满的。那红红的三位数,一个一,两了零,一条鼓满风的帆船,幸福地驶向他的小心脏战栗不已的大海。那许许多多的满分不正是老师兑现给他的爱吗?每周共享的秘密。到五年级放寒假的时候,他每晚要把作文本翻上一百次并放在枕头下才能安心入睡。
他多么想变成一只小虫子飞进老师的酒窝里。当老师的目光全洒在他身上时,强烈的感情在年幼的身体里激荡汹涌。他甚至产生了长大娶她做妻子的石头般坚定的念头。即使她老了,有了白发和皱纹,跟母亲一样,我还是要娶她。
来不及表白,来不及登上鼓满风的帆船,他就失恋了。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当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揽住帅气的数学老师的腰时,他就失恋了。那个下午灰蒙蒙的,而帆船载着他一个人沉没在远处的大海。两个星期后,便狠心要成为一个作家,把失败的初恋写成厚厚的小说,让她好好后悔,好好伤心。
他开始读小说,很长的小说,繁体字,边猜边跳读了几十本。战争的、历史的、演义的,都读。那时还没有言情的。
还没有等着难堪的婚礼,还没有等着小说开头,小学就毕业了。漫长的直冒汗的暑假把语文老师的影子抹得越来越模糊,漂亮的酒窝被村边小河上游冲来的泥沙填得越来越浅,最后消失了。
我在这儿已经呆得太久,察看别人的隐私让我脸红。也许他会甜蜜地梦见童年,但这段羞怯的小溪一样清澈的初恋,还是令他远远地绕开了,好像一不小心踩响一块石头,老师就会转过脸来,何况她还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揽着数学老师的腰。
毫无疑问,那部厚厚的小说还没出生就被枪毙了。他像我一样写诗,拙于故事。但我肯定,它们已化整为零,揉进了难以寻觅真相的分行文字。
这是从矿石中炼出的初铜,那把还未打出齿来的钥匙?我本想看看他放在枕头下的作文,那条鼓满风的帆船,但怕被他贴上“偷窥癖”的标签。何况他警告过我不能说得太多,他随时会醒。现在是午夜,时间不多了。
汽车终于驶向碎石路。我随着他的身子晃动了一下,靠紧他,以免他被摇醒。我可以陪他睡一会儿,使劲想着狮子和雪,以便把礼物送进他的大脑里。
是不是该放弃呢?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乘客睡着了,我却从他们的包里掏出钱夹、存折和钥匙。但他们团结一致的鼾声鼓舞着我,让我上瘾,忍不住把手伸进了他们的“口袋”。
那条线呢,我当然记得,丢了我就永远回不来了。
我差点忘了,他曾写过一篇小说,写了十分之一,两千字的样子,丢在抽屉里生锈,虫子也许早把它们吞进了肚子里。我看过,虽然用的第三人称,但有很强的自传性,我隐约记得其中的一些情节。但说实话,几乎不能算小说,倒更像一篇童话、一则寓言。
他离过婚。即便在小说中魔幻和变形,也只是换了一件从不穿的衣服而已,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鱼或者一头狮子。正如卡夫卡把自己变成了甲壳虫,在另一部小说中又变成了土地测量员。
这样我会轻松些,让他来讲我不擅长的故事,虽然他也不擅长。我只需集中精力,在回忆中把那篇半途而废的小说还原。需不需要改换人称使之更具真实性,还是给予作品充分的尊重?算了,还是为难“我”自己吧,因为未经允许我就把他不打算发表的小说公开发表了。
我知道有这一天,一开始就知道。
初二下期突然就感到孤独,孤独不停地从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像气泡一样冒出来,烟雾般弥漫。天空每天都昏沉沉的,出太阳也昏沉沉的。周日就整天呆在屋子里,关上门窗,独自一人才能稍稍喘息。现在才知道,那是青春期荷尔蒙制造的孤独。
那会儿,老梦见一个很大很大的水缸,大到没有边际。只有一条鱼在水缸里游,从一个夜晚游到下一个夜晚。中午爬在课桌上午觉,它也从远处游过来。是一条眼睛比身子还大的鱼,它始终朝着我,我看不见它的身子,只知道它会有一个像身子一样的东西。每一次,都在快游到身边时,我就醒了。
她恰好掉过头来,眼睛看着我。那一刻,她的眼睛大大的,就像那条鱼的眼睛。当晚,那条鱼就和她不停地争夺眼睛,它们争吵、挤兑、谈判,凌晨六点终于达成协议。它们必须相互妥协,再过一刻钟,我就要起床上学了。
第二天,她一直躲着我,我走到前面也躲着,头垂得低低的。放学离开教室时,我才逮着她的眼睛,一半是她的,一半是鱼的。
她们每晚撕毁协议,重新争吵、谈判,再签署新协议。她眼中的鱼眼一天比一天少。第七天早上,刚进校门我就看见那双已完全属于她的眼睛。
这是他流产小说的第一部分,我说得没错,一篇童话或者寓言,不过写得还行。第一部分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从此,我的身体变成水缸,塞满了她的一千只眼睛。
我本以为他还会写些什么什么的,像一部真正的小说那样展开。但是没有,刚鸣笛启动的火车,猛然停了下来。他肯定在这长长的间歇抽了整整一包烟,满屋子缭绕的烟雾,也缭绕在他久久闭着眼睛的身体里,呛得我嗓子发痒,如果不赶快离开,我会呛出眼泪来。
不会讲故事,就只能学习跳跃。但步子跳得太大,比一匹马跳得还大。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教书,一座寺庙改成的学校。偏僻的地方,更加偏僻的夜晚,老师都不住学校,除了门卫。总得找点事情吧,写小说是万不可能的了,年轻漂亮的小学语文老师我已经忘了,碰见时我差点没认出来。她已经发胖,早不是原来的样子,酒窝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脸上显得怪怪的。看她那幸福模样,幸亏没让她好好后悔、好好伤心。
写诗,上中学我不是胡乱写过吗?那就写诗,在屋子的黑暗里写,醒了睡不着又写,不写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听它们在黑暗的抽屉里朗诵,有时也听雨在玻璃窗上朗诵。
收到她的信是在一个星期六上午。门卫说,你的信,我立即就知道是她写来的。虽然,好几年不联系了。信果然是她写的,她说她毕业了,她说她还记得华严寺古曲的样子,还记得校门口那棵五个人也抱不过来的老黄桷树。
古曲,她用“古曲”这个词,我打了个激灵,一下想起她的眼睛,那曾在我身体里繁殖了一千只眼睛的眼睛。它们全都活过来了。
“古曲”,这个幽僻的词让我爱上了她。莫非,我一直在等这个词从深黑的地方爬出来?古典、浪漫、忧伤,散发着丝绸一样的光泽。放进身体里,会与你的内脏、你的雪、你的狮子和平相处。
那天夜里,想写一首很长很长的诗,但一句也写不出来。我整夜听见一群温暖的小兽簇拥在窗外的夜色中。
因为一个词语和一千只不存在的眼睛而爱上一个女人,并和她结婚,我永远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比一千零一夜还多了一夜。这是孤独熬制的疯狂,虽然在一次喝醉酒后痛苦地直觉到它被中断的命运,但仍义无反顾地迎接了未来失败的婚姻。直到调到另一所学校,才在梧桐翻飞的落叶中把悲伤消化为感伤。
他再次骑上那匹快马,远远地跳开了,我差点追不上他的影子。
我知道有这一天,一开始就知道。
我能接受这些粗暴的礼物……(整整一页的省略号)
拿到离婚证的瞬间,突然就想起了那次醉酒后写在笔记本上的话,字迹潦草像酒后的风,一字一页。
那时,我们才刚刚开始。
原是一个提纲,故事的影子也没有。那些故事呢,是不是切成了碎片,插入了他转了三趟车的诗句里?
小说就这样完了?没错,完了。这和融雪事件有什么关系呢,一点也没有,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趁他睡觉,绕一大圈,偷窥他的童年,恋母般羞耻的初恋,流产的小说,离婚证,我感到越来越沮丧,一次完全失败的跟踪调查,而且脱不了非法的嫌疑。
好在他醒了。在碎石路上,最好的司机也免不了向睡觉的乘客道歉。我必须趁他还没有完全清醒钻进他的身体,藏起来,该我睡觉了。也许我睡不着。
果然睡不着。他身体里,四周挤满硬块,挤满冰冷的石头。青色的,黑色的,青黑色的,都有,足够装满五卡车。它们刺得我浑身酸痛。
我闭眼养神。但狮子、鱼眼、温顺的小兽、女教师、小说和离婚证,齐齐向我飞来,杂乱的翅膀拍得我晕乎乎的。我试图用一根线把它们拴起来,让它们安静。我感到它们是一张脸的易容术,一把钥匙的不同部分。拴住了狮子,鱼眼又从手中挣脱,飞到空中。当我终于像拴蚂蚱一样把它们拴成串时,我实在累坏了。
我猛然发现我手中握着的不是一串蚂蚱,是一把钥匙。使劲揉揉眼睛,千真万确:一把钥匙。不是铜的,是一块蓝色的薄薄的冰。不能碰,一碰就碎,就会重新变成乱跳的蚂蚱。也许,我能用它打开他寓言般的过去,并洞见他晦明的未来。
冰钥匙突然在我手中挣扎,它察觉了我的阴谋。他在发抖,每一块肉每一块骨头都在打颤。他已经完全醒了,在车厢的黑暗中只能找到另一些黑暗,和无人分担的寒冷。
我的手指快要被冰的寒冷烧爆,但最后一秒钟挺住了。冰似乎累了,在我手中渐渐安静下来,一匹被驯服的野马,温顺地发出柔和的蓝光。一个奇迹,我怎么刚才没发现身边的石头刻满文字,诗,一组还未被他写出来的诗。我真想把它们偷出来。
一点一点地死去,你的脚趾、踝骨、膝盖、大腿,你的指尖、腕骨、肘和胳膊。一点一点地死去,你的眼睛、耳朵、鼻孔,你的嘴和舌头。一点一点地死去,你的阴茎、睾丸,你的胃,你的肺,你的肾。一点一点地死去,你的神经,你大脑的灰质、沟槽;你身体的铁和铜,你的每一块骨头。就这样,一个个部分的死,终于集合为一个整体的死。我手表的指针也死了。——然后——这需要多久,仿佛天空给了你所有悲悯——在一个雨不再敲打玻璃窗的夜晚,在一个墨水涂抹掉所有笔记本的夜晚,在一个地名变成另一个地名的夜晚,在你的脸不再呼唤我的脸的夜晚,我梦见他一点一点地活过来,从脚趾到死了仍在变灰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活过来,一点一点挪出那黑暗之穴,眼睛转动,它打量镜中的另一双眼睛。没有人守着你,没有人惊呼这奇迹,他看着自己,并开始对自己说话。
像风一样奔跑,像闪电一样奔跑,让大腿的血跑起来,让心脏的血跑起来,让血管里的血都跑起来。跑过你的手指,跑过你的舌尖,跑过你颤栗的火和冷漠的嘴角,跑过你的性。一刻不停地奔跑,让这条路也跟着跑起来。像风一样奔跑,像闪电一样奔跑,把一座熟悉的城市跑成一座陌生的城市,把一张嵌入大脑的脸跑进遗忘。像风一样奔跑,像闪电一样奔跑,把自己跑出自己的身体,直到把记忆跑成另一个人的记忆。有一天,当你停下来,那追赶你一生的暴徒,将你痛打成一个巨大的线团。
像一件钝器,终点撞来。我是下不了车的乘客,流失的光阴消耗着它的未来,而另一个终点已开始在身体里低鸣。我的火车载满雪正驶向南方。那些羽毛簇拥的夜晚,那些还在雾中的清晨,汽车转弯,驶向一个用旧的站台。你把手探出窗外,风握紧你的手,你从未想到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今夜,请允许我成为你口水中的野狗,为了你的同情心,请把石头紧紧地攥在手中。为失眠向自己的身体道歉吧,为没有好胃口向精美的食物道歉吧,为走神向骂粗话的司机道歉吧,我的火车载满雪正驶向南方。
雪涌上五楼的窗台,你去过的地方都被覆盖。这时间之雪,现在是干净的,来不及蹿上肮脏的脚印。它围起火炉,堵住了所有去路。你嵌在屋子里,空间一天天被压缩,你只能撤退,一步步,从眼睛和耳朵里撤退——从手撤退到肘撤退到肩撤退到胸,从皮肤撤到肉,从骨头撤到骨髓,撤到坚硬的核。也许,已经没有春天,必须剥出来,剥出肉和骨刺,雪就停止生长,带着羞愧低下窗台。你的指尖,一条河开始流淌。
我埋下时间之果,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却十倍地弹回。我已洗不掉身体的昏暗。这是夜晚,是十月就开始的冬天。对不起,我没有准备更多的火;对不起,他有陈年的关节炎。蜷曲,紧一点,再紧一点,膝盖抵着胸口,像一头刺猬,仿佛这样就缩回了母亲的子宫。卷帘门卷起又一个夜晚,你得打开,用冰冷的水清理眼睛。换一身干净衣服吧,并打上领带。红灯,你不能跟着汽车闯过去,你必须是个文明人,让失眠的双腿站稳。给母亲打个电话,说正在赶车回家。
来不及分行,来不及标点,来不及偷走最后一行,字已从石头上隐去。蓝光消失,我不知道冰什么时候融化的,手指残留着它的最后一滴水。我再次置身于浓稠的黑暗中。
我无法相信,这绝不可能是他的诗。前两首,暴雨夹杂着冰雹,快得我追不上它的嗓音。以前,他会命令词语把冰雹吞下去。以前,他写得多么低音,每个词都在转车,把情感的旅行包,全留在车上。后面三首,往常的低音才找到他,从空中压向一片痛苦的开阔地。
他,终于背叛了自己和自己的诗。
如果是批评家,诗歌的侦探,我会像剥坚果一样,剥出果核,释放那些词语的能量。一定有一个难以言及的故事,被它们深深地囚禁了。一定有的,尽管只是故事的尾声,但只要找准词语最初的线头,就能像推理小说一样查清案件的真相。但累了大半夜,我实在困了,上下眼皮稍一使劲儿我就被推进了早有准备的鼾声中。
看样子碎石路已经结束了,汽车非常平稳,满盆的水一滴也不会泼溅出来。他打开手机,脸映得蓝莹莹的,染着幽灵的气息。一条迟到的短信,天气预报,阴天。他把手机贴在脸上,仿佛要将脸埋进去。
到站了,他久久未动,幽灵得到应有的尊重。最后一个幽灵在车门口停下,转身鞠躬,回表感谢。下车吧,司机的声音像在求饶。
路灯半睁着眼,疲惫而昏沉。一条街的鼾声迅速被另一条街压下去,在空中纠缠着、扭打着,把所有还游荡在街头的人变成了幽灵。除了自己,他什么也没带。他不知道我躲在他身体里,还有那些石头、雪和早已忘掉的鱼眼。如果算上石头上的词语,行李说不上少。
加入幽灵的队伍,还是凑合着找个旅馆?他停在路口,摸出一支烟,接上。和我一起睡吧,但他听不见我的喊声。他一下车,我就醒了,他的脚一会儿停下,一会儿摔打出脚步声。里面太逼闷了,我想钻出来透透气,这座陌生城市的气息让我兴奋,差点像小狗一样吠出声来。
旅馆还算挺干净,重要的是床足够睡下我们。刚坐下,房间里的电话就响了,先生,需要服务吗?声音很甜很软很腻很黏,像儿时吃的棉花糖。他没遇见过这事儿,但知道是什么。在听筒快搁上机座时,耳朵重新凑了上去,好的。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老处男!我太清楚他了,思想的解放者,却患特号的行为自闭症——被他痛斥的洁癖。从今夜开始,他必须学习背叛自己的身体。只有背叛,砍掉枯死的老树,新的生活才会到来——一份明早端在床头的新鲜早点。我说不出话来,我无权阻止他。如果一具身体囤积了五百吨昏暗,那就只能切开一个口子,把它们流出来。而女人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巨大的容器。
门铃响了,颤抖着,在寂静的走廊里警报一样急促、嘹亮,盘旋在这座城市和另一座遥远的城市的上空。他坐在床边,埋着头,感到自己像儿时的沉船一样沉下去。要是手机铃声此刻响起,他会哭着逃离这座城市,回到他熟悉的城市的黑暗中。那温暖的黑暗,有一双闪动的眼睛。
门铃继续在响,第三次了,狠狠捶打着他的内脏。他走到门边,闪开一条缝。是个年轻的女人,不丑,也不漂亮,但很饱满,胸口刚好开到眼睛可以自由探进的尺度。一个上好的容器,足以装下五卡车的石头和五百吨的昏暗。
对不起,话还没说完,门已经关上。另一扇门也“咔擦”一声永远关上了。那一刻,他突然被一千磅的拳头击中,心脏猛然收缩,像顷刻塌陷的地窖。那力量穿透他的肉和骨头,重重倾泻在我的腹部。老处男,我咬牙痛骂。
他蜷缩在两床被子下,一张拉断的痛苦的弓,再也射不走身上的石头。它们倾倒在五百吨的昏暗中,为一具五百五十吨的石棺疯狂搅拌。
哆嗦,害痢疾一样哆嗦,全身的零件都惊了,拼命将自己抖松,把一个整体主义的机器拆散,然后惊叫着鸟儿一样逃走。整个旅馆都被传染了,地板在每一层楼的每一间屋子里发抖、抽筋。电热毯开了,空调开到了快要爆炸。冷,冒着汗水从床垫下钻进去,钻进毛孔,把能量的针剂注射在血液中,搜索他最深处的体温。
寒冷的火熊熊燃烧。
我知道,他没有病,内部器官完好无损,胃安静地消化着中午的最后一粒食物。把自己想象成生病的样子,并在幻想的痢疾中高烧不止,只是为了不那么无耻地享受被另一个自己惩罚。很快就会不治而愈,很快就会在悬崖勒马的惊险中奏响胜利的鼾声。
他睡着了,一头饱食了五只羊的野兽。餍足的嘴唇微微开启,一条灰色的河在身体里静静流淌。他从未舍得把那些昏暗和石头倾倒出去,它们成为他的儿女,他需要更多的儿女。
我终于从他松开的嘴钻出来,像灵魂一样上升。在空中,我看见宽大的床上摆放着一具不再被孤独和悲哀煮沸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