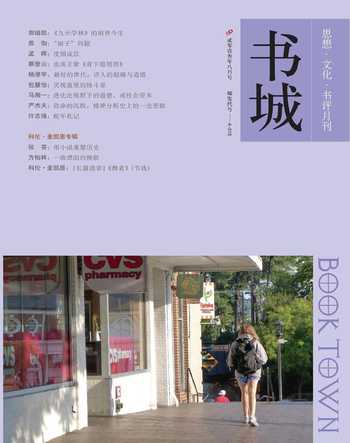书城莱顿
书玉
骑自行车的小城
到达莱顿是五月初。从伯明翰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俯瞰,比起英国乡间起伏的丘壑,荷兰的田野真是平坦,那是荷兰人填海造田从大自然手中讨出来的结果。再近些,就看到一片片整齐而色彩缤纷的彩色地毯。过了很久才恍悟那是大片的郁金香农庄。五月的郁金香是荷兰特有的风光。
大学城莱顿在荷兰最大的两个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之间。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只要十五分钟。城市真的不算大:从最北边的中央车站横穿老城中心到我位于城市南端的临时公寓,走路也只要半个小时。据说人口只有十万多一点,其中五分之一是莱顿大学的学生、教授或者我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

小城的魅力以它别具一格的自行车向我展开。从中央车站的游客中心取了公寓钥匙,我走向车站广场。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放松地享受着五月的阳光;一个卖热狗和烤肠的食品车;街边的店里走出的一对恋人拿着令人眼馋的冰淇淋;不远处矗立着一个荷兰的象征大风车,一副小地方的温馨和亲切。没有汽车来往鸣叫,却看到旁边停车场里铺天盖地上下几层的自行车,气势蔚为壮观。显然,因为地势平坦,街道比较狭窄,加上城市本身不太大,这里是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去住处的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匆忙而快乐的骑自行车的人,轻捷地穿过密集的后巷和纵横交织的河道。明媚的五月天里,他们看上去都那么健美、年轻。即使年纪大的人,因为骑车都显得富有活力。车子跟人一样,高大结实,大多是用了很久的老车破车,看不到在北美用来做运动竞技的那些名牌车,但自然就有一种笑傲世俗的潇洒和实在:世界上还有像自行车这么好的交通工具吗?又环保,又锻炼身体,而且不用花时间精力跟别人比虚荣心。它令我想起了大学岁月,校园里那些破旧却永远年轻的自行车。可毕业后,我们那么轻易甚至迫不及待地丢弃了它们,去追逐似乎速度更快的汽车和别的东西……
这个一直骑自行车的小城自信而富足,充满着书生气。
莱顿的书店
小城的另一个魅力就是它的书。我从没有见过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密集的书店。
从我临时的住所,位于莱顿南城的Hogewoerd144号到我临时上班的办公室,位于城西莱顿大学旁边的亚洲研究国际交流中心(IIAS),只有约十分钟路程,可是除了第一次上班的那个早上,我以后都要花少则半小时、多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因为路上的诱惑太多,有太多的东西可看:在纵横交错的运河上看形态各异的桥,在古城中心看残留下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市政大厅的壮观设计,在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里,看沿河高大民居的墙上用异国语言写的诗句,还有那些穿插在大街小巷里的古董店和书店。
记得到达莱顿的第二天,我从办公室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决定在市中心的那家V&D百货商店买急需的床单和浴巾。从Breestraat街的主门进去,一进门竟是书籍和文具部分,而且铺开一大片,几乎是一家小书店的规模。这一不寻常的安排陈设让我对莱顿刮目相看。如今世界上还有几家大的百货店进门处不是化妆品就是首饰?
Breestraat街是莱顿城最繁华的两条商业街之一,而除了辉煌宏伟的市政大厅坐落其上,它还以“书店街”出名。仅在我上下班经过的这后半条街上,就有三家卖新书的书店。最有档次的是正对着市政大厅的Van Stockum 书店。这个书店坐落在有着高屋顶的十七世纪建筑中,高大敞亮,室内装潢却很现代。进门迎面的高墙上就是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死亡》(On Death):
Can death be sleep when life is but a dream,
and scenes of bliss pass as a Phantom by,
The transient pleasures as a vision seem
And yet we think the greatest pains to die
……
浪漫主义诗人这忧郁华美又有些轻灵超脱的诗句一下子就把从喧闹的大街上走进来的人拉到一种静寂与反思的心境。读读书吧,让忙碌的脚步有一刻停歇。
书店里主要的书都是荷兰文,跟一般书店一样按主题分类。中间长桌上推介的是畅销或最新出版的。荷兰语是个小语种,当代荷兰作家也不多,但是书店里荷兰语出版的书、铺天盖地。多数是翻译过来的,世界各地的书最新的书在这里似乎都能找到。以小小的荷兰人口计算一下书的市场,可以想象荷兰人读书的勤奋和对世界的好奇。荷兰人几乎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问起原因,他们很谦逊地说因为我们是小语种,就要学习其他语言。但实际上,这种出版各种语言的书籍的传统是有历史渊源的,十八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论报纸“莱顿公报”(Gazette de Leyde)就是用法文出版的。
书店楼下还有专卖大学课本的部分,为莱顿大学直接提供合作服务。
出来沿街走过几家店铺就是另一家书店Boekhandel De Kler 。它看上去似乎更通俗些,因为一进门有很大的杂志和畅销小说部分。可是稍往里走,才发现内中胸壑。不仅各个题目的书颇有选择,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英语和法语书籍。这个书店其实也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最早是 De Kler 家族拥有,故得名。在荷兰有五家分店,各家选书都有自己的特色。莱顿这家分店目前似乎在重点推介惊怵小说Thriller,好像在寻找通俗市场。果然,与其中的店员聊了一会,发现他们也在感慨做实体书店越来越难。
在两家书店之间,还有一个专卖儿童书籍的书店。没有进去,但看着门面招牌的五颜六色和橱窗里的喜人陈设,可以想象孩子路过时会如何动心。后来发现莱顿全城大概有四五家专门卖儿童少年书籍的书店,即使像一般的书店,也都无一例外专门设有儿童阅读角落,装饰得花花绿绿舒适温馨。让孩子直想坐下来,跟爸妈一样看书。
Breestraat街过了桥就叫Hogewoerd,也就是我住的那条街。沿街的房子与河边那些高顶的带花园的公寓比算不上好区,都是三层的出租公寓。密密集集,每隔几步一个大门。门外的名号牌上有着十来个住户的名字。住的大多是学生、游客或访问学者。街上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店铺。咖啡馆,室内装潢用品店,自行车店,二手货古董店和西饼店。大部分商店门脸与北美或中国的比起来都太小了,有的如果不注意会以为是民居的一部分而走过。它们静静地趴在这些建筑的一楼,不喧哗不夺目,融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条街上的“五月花书店”(Mayflower bookstore),在莱顿也算小有名气,因为专卖英文书。一个五十平方米开外的大房间,右手是新书,左手是二手书。左边靠窗部分,背靠背放着两架钢琴,而稍后的一角是摊满书的一张长桌。几乎就是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感觉。偶尔有一两个人进来,四周看一看,与热情的女店主打个招呼,让她帮着订一本书,走了。小店又恢复了宁静。
在实体书店日衰的今天,在人们越来越浮躁只想刷屏的今天,到了莱顿,徜徉在各种各样的书店里,即使多数书我读不懂,也满心喜悦。有种奢侈,有种感动。

免费书店“莱顿书阁楼”
对那些喜欢读书但又不想买书或怕背着太沉重只想随手捡几本书在客居时看看的旅行者和背包客来说,莱顿还有一个秘密的好地方,那就是可以享受免费书籍的大书库“莱顿书阁楼”(Book Attic Leiden),在城东一条美丽优雅的街上。中午时分,从刚刚泛绿的树丛后面可以看到年代久远的Marekerk教堂圆拱顶。近处整齐的院落里一簇簇的盆花在盛开。“书阁楼”的大门紧闭,上面写着一个什么慈济会的名字。经过路人指点,我才看到旁边像是车库的院落才是通往阁楼的大门。
“书阁楼”在一家堆满杂货和弃置的雕塑作品的大仓库间。通往“书阁楼”的楼梯陡陡的,暗暗的,但一走上去就豁然开朗。足有二三百平方尺的大空间里是一架架一堆堆的书。这里的书都是由个人或各种机构图书馆书店捐出的,也包括出版社多余的书或者样书。因此是各种语言、各种类型的书籍大杂烩。除了荷兰文,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最多。书籍也大多是旧的,甚至有些年代。不过是免费的,每个人都可以任选七本带走。也欢迎把不用的书再留在这里,让后来的人受益。
听说这个书籍回收中转站的主意是一群莱顿的志愿者想出来的,两年多前付诸实施。每周服务三次,周二晚上七点到九点,周四、周五下午一点到五点。我去的那天在这里工作的五六个人都是各种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在不同的角落里拆包登记,给书上架,或帮来访者找书。听我说想了解荷兰作家,一位叫彼得的老先生热心地向我推介荷兰畅销女作家Cissy Van Marxveldt (1989-1948) 。Cissy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拥有大批年轻女性读者,以她的系列小说Joop ter Heulz最为著名。这个系列从Joop作为高中女生到恋爱结婚,生儿育女,里面穿插很多书信日记,塑造了一个有主见、不断成长的二十世纪荷兰新女性。我不好意思拂老人的好意,告诉他这好像太历史了。因为一个星期下来,发现在莱顿时间好像可以很慢,而且过去与现在也不见得有那么大差别。老人还帮我找到几盘专门为说中文的人学荷兰语的磁带,介绍我认识另一位志愿者玛塞拉。玛塞拉是智利人,来荷兰也有二十年了。现在在莱顿大学读硕士,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来这里帮忙。当发现我跟她一样,是满世界跑的世界公民,她圆圆的脸上闪着激动和热情,留下电话,约我再见面。又指着墙上的一个告示,说周日这里还有一个读书会,完了之后大家会换个地方去喝酒。
莱顿的朝圣者博物馆
除了新书店和免费书店,莱顿可能也是拥有最多古董店和古董书拍卖商的地方。你想,大学里有那么多藏书丰富的老教授和收藏家们,再加上悠久的历史,东西南北来历复杂的居民,这里的古董和珍奇书籍自然丰富。
莱顿卖古董书的老字号拍卖行叫Burgersdijk & Niermans。坐落在莱顿最古老的街区,靠近圣彼得大教堂的Pieter Skwartier那一带。那周围有保存最好的古老建筑和很多高档古董店。走近这间看上去不起眼的三层建筑,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写着拉丁语的黑铁招牌“所罗门的圣殿”(Templum Salomonis)。这个店名和建筑都是来自十四世纪有名的法学家和书籍收藏家Philips Van Leyden(1328-1382),这里是他的住宅,因他的私人图书馆而得名。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房子几易其主,但都跟书有联系,不是印刷工就是书商。B&N公司的两个创始人Pieter Burgersdijk 和George Niermans本来也都是大出版集团Brill的雇员。一八九四年两个人接手Brill原来的拍卖和古董书收藏部分,并在现在这个地址上开始了他们的生意。
店铺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面是书店,主要是卖一些珍本书、古典系列和学术书。后面就是办公室。公司每年举行两次拍卖活动,五月的这次刚刚结束。雇员们正紧张地把拍卖出去的书打包邮寄。
B&N自己也出版一些小众型图书,尤其是有关荷兰和莱顿的文化历史。有十八世纪三个最有名的书商的旅行日记,有关于莱顿城的建筑历史,还有一本再版多次的英文历史书《老城新人:美国朝圣者在莱顿》(J. Kardux & E. van der Bilt – Newcomers in an old city. The American Pilgrims in Leiden, 1609-1620)。这本书帮我意外地了解了莱顿与新大陆的联系,还把我引向莱顿另一个有名的地方,朝圣者博物馆 (Leiden American Pilgrim Museum)。
博物馆实在很不起眼,就在市公共图书馆和艺术中心的斜对面,我却转了两圈,问了三拨人才找到。在一个低矮的十三世纪的老房子里,朝圣者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导游Bangs博士一边带我和另一对参观者看不大的两个房间,一边讲解朝圣者的历史。
原来,当年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在英国成为国教,也叫圣公会(Anglicanism)。圣公会内部的一些教徒反对僵化固定的教会仪式和严格的等级规定,认为除了《圣经》是最可靠的上帝之词外,个人有权选择与神沟通的方式。他们后来被称为分离教派(Separatist),也就是Puritans。分离教派在英国受到打击和排挤,很多教徒被罚款甚至入狱。于是一批教徒在William Brester和John Robinson带领下离开英国,寻找可以给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他们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莱顿安顿下来。更多的人陆续投奔这里,最多的时候达到五百余人。他们聚居在一起,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朝圣者之父”(Pilgrim father)的那批人。
这个博物馆展示的就是十七世纪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传教士家庭的大致情形。住处分成内外两个部分,里面靠着壁炉为中心,是家人活动吃饭的地方,而外面的一半空间就是用来纺布的。Bangs博士对这里的一切很熟悉,对我们无知的提问也很耐心。他一口英语说得实在太完美,一问才发现其实他是美国人,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来莱顿大学读博士。后来就留下来,因为他的研究兴趣是十六七世纪的莱顿艺术史,因此创办了这个博物馆。但他的主业其实是收集历史档案资料,研究和写书。他最近的一本书就是关于朝圣者在莱顿的历史,书名叫《陌生客和朝圣者》(Strangers and Pilgrims)。据他解释,当初英国的教徒之所以能在莱顿安身,是因为当时荷兰对宗教信仰相对宽容,而莱顿繁荣的工商业也使这些人找到了可以做的事。莱顿大学成为他们传播思想的平台。当时Breaster在莱顿大学教英文,Robinson在大学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并参加当时的宗教辩论。他们还印刷小册子,传播他们的宗教思想。这些人在莱顿生活一段时间后,后来又再度起航,登上“五月花”号轮船,于一六二○年到达北美洲,在东部麻省的Plymouth 落下脚,这就是新英格兰最早的欧洲移民。 Plymouth Colony和感恩节一样,奠定了新英格兰的传统,是今日美国精神的基石。但也有一些朝圣者客死莱顿。比如Robinson,于一六二五年去世,他的墓碑就在莱顿城中的圣彼得教堂。
离开博物馆时,我发现了Bangs博士脸上的一丝落寞。又是一个写书人,一个在文字中寻找家园的人。他看上去也有六十岁了。当初他来莱顿并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他在客居莱顿的那些朝圣者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了吗?
莱顿的出版传统
莱顿对书的情有独钟是有历史渊源的,莱顿的出版印刷也有其独特的传统。
中世纪,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都有各种各样联系的荷兰是罗马天主教和欧洲君王权贵割据相争的对象。荷兰几个世纪在封建割据中试图独立的状态,可以从处于新旧Rhine河交界之间形成的小丘上的圆形堡垒Burcht Van Leiden 看出一端。这里已经成为莱顿从一二○三年到一四二○年再到一五七四年几次被围但终究生存下来的象征。
自十五世纪末开始,莱顿的印刷业和纺织业开始驰名欧洲,尤其是粗棉毛布和羽纱,成了莱顿的名牌产品。Burcht旁边的市图书馆的老房子就是当年接待来往商人的客栈(Inn and Coach house),现在如果你去逛当地的周末集市,会看到很多摊贩上卖的还是大幅的布匹。
小镇在十六、十七世纪开始繁荣,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五七五年莱顿大学的建立。据说,欧洲“八年战争”期间,莱顿人站在反戈的荷兰贵族一边,抵抗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者。一五七四年五月到十月间,小城整整被围困了近六个月,有一半人失去生命。后来运用河道才运进物资供给,市民得到拯救。这一情形在当时的画家Otto Van Veen 的画作《莱顿的解围》(Relief of Leiden, 1574)中得到栩栩如生的表现。如今每年的十月三日,都是莱顿的“胜利日”,是要举城相庆的。今日荷兰王室的祖先,当时的“护国公” 威廉一世为感谢莱顿人,让莱顿人在减税和建一所大学之间选择一项,作为奖赏。有眼光的莱顿人选择了后者,也因此成就了小镇此后几百年的名声。
当时莱顿最有名的工商业除了纺织还有印刷。荷兰在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以对宗教和信仰的宽容及言论自由的态度闻名。而莱顿大学的成立,吸引招徕了欧洲各地的学者、宗教分离主义者和持异见者,成为一个论坛和思想传播集散地。新教的理论家以大学为基地,热衷于编写大量的神学著作,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也相继出版,莱顿因此也成为欧洲印刷和出版的一个中心。
这一阶段莱顿历史上出现了几位很有名的书匠,最有名的是Christophe Plantin(1520-1589)。这个出生在法国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的印刷工既是一个手艺非凡的书匠,也是一个见识渊博的出版家。一五八三年,他在安特卫普的生意被西班牙人搅乱,而莱顿这个新建的大学城又急需一个好的印刷工,他就迁居莱顿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Plantin的到来使莱顿的印刷出版上了一个新层次。他出的希伯来、拉丁和荷兰文的《圣经》因校对准确、印刷精美成了后世的典范。Plantin还出版了大量的希腊罗马经典、法文和拉丁文图书。同时期另一个书匠叫Lodewijk Elzevir(1540-1617),他曾在安特卫普跟Plantin学艺,后定居莱顿,是Elzevir印书馆(House of Elzevir)的创始人。这个印书馆以十八世纪出版了被教会视为异端的伽利略学说而为后人铭记。
可以看出,莱顿的印刷人出版商在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知识传播上的巨大贡献。他们本人不止是术业有专攻的技工,而且都有远见卓识,敢于为思想知识行动。
买卖图书的书商们与莱顿大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十七世纪当地很多书商都是一边卖书,一边出书。世界上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社Brill的创始人就出自一个有名的书商Luchtmans 家族。Brill 于一六八三年创办,借助莱顿大学里众多教授和学者的力量,当时以出版各种语言的《圣经》、东方语言、神学和种族学书籍为强项。三百年来,这个古典语言和人文学书籍的传统一直得到延续,并在法律和社科方面也有发展。一方面,出版很多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其中大量的书籍被用作大学教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学术出版商。不过Brill二战期间因与纳粹合作提供多种语言的军事手册和课本而使公司声誉一度受到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金紧缩,Brill关闭了伦敦和科隆的办公室。九十年代后又有所发展。至今,在莱顿和波士顿有两间办公室,每年出版有一百余种学术杂志、六百余种学术著作和参考书。其中的莱顿汉学书系(Sinica Leidensia)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由最著名的汉学家组织编写,丛书收录有专著、文集和翻译作品,以古典汉学和权威作者而著称。近年来,也开始积极组一些当代研究的书稿。去年我还应邀为他们审读过一部书稿。
莱顿的城市精神
前几天在网上看国内的一个凤凰网读书会栏目,在清华教书的加拿大人贝淡宁(Daniel Bell)正为他与人合写的一本新书《城市的精神》对话汪晖。在讨论什么是城市精神和爱城主义(civicism),贝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独特的城市精神才能让人产生归属感。
到莱顿已经不知不觉快两个星期了。我对小城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也差不多走熟了。在这个到处都是学生、学者和书店的地方,我有一种久违的宾至如归的感觉。
天气好的时候,沿着小城外围的Singel河从城南到城北绕城一周,可以看两岸草地上的绿柳红花,看运河船里喝酒作乐的人,看写在墙上的诗,来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字。阴天下雨,就可以待在书店、图书馆,或者去朝圣者博物馆隔壁那家古董店,在一堆堆故纸里,挖掘十七世纪的荷兰版画(engraving)和各种各样的地图。窗台上摆的青白瓷罐很眼熟。原来这就是著名的Delftware,盛行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荷兰特产,最初正是模仿中国青白瓷器,是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的一部分。
如果用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来形容莱顿的精神,我想就是书吧。这里的人是读书人、写书人和出书人。连这里的墙上也写满了字。“写在墙上的诗”是莱顿城的一个文化项目,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已经有逾百首来自世界各种语言的诗被精心描画在大街小巷上的各式建筑的墙壁上,包括美国诗人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56)的这首诗:
Love is like water or the air
My townspeople
It cleanses, and dissipates evil gases.
It is like poetry too
And for the same reasons.
爱像水,像空气,
城里人,
它清洁,消除邪恶之气。
它也像诗,
因为同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