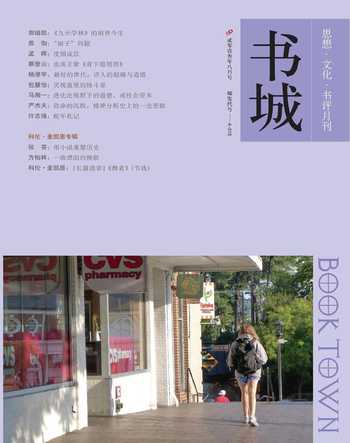蛇年札记
许志强
伍迪·艾伦《午夜巴黎》。那几个艺术家角色蛮有趣:海明威像恶少,菲茨杰拉德像买办,布努埃尔像工贼,毕加索像神经病,达利像白痴。
在汉娜·斯米基的公寓聚会。有趣的是,这些美国姑娘似乎总有点像男子汉。
为备课重读《诉讼》。第二章对法院的描写堪称绝妙。要说明我对卡夫卡的敬佩,那就挑几段给学生读一读。
《诗经》是我的童年。我的童年还有街巷边的土城墙、河沟和桑树地。
春日慵困,街巷无人,桑树地里行路的乡下人在说话。
卢西恩·弗洛伊德那些有大叶子观赏植物的室内小景都画得很美。
弗朗西斯·培根最有味道的还是他那些三联画。
画家在塞尚的传统中增添一些语汇、视角和话题。哲学家也一样(列维纳斯),在胡塞尔的传统中增添一些语汇、视角和话题。
汉娜·阿伦特那篇写教皇(龙卡利)的文章中提到,这位模范基督徒不仅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后者尤可为怀。
想起《山上宝训》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为避免汉语歧义,这里“虚心的人”(the poor in spirit)应直译为“精神贫乏的人”。
除非用另一种文明衡量,否则如何得知某个文明的集体精神错乱症呢?(鲁迅《狂人日记》)
有写《狂人日记》和《祝福》的鲁迅。有写《马上支日记》和《阿金》的鲁迅。前一个鲁迅被谈论得多。也应该谈谈后一个鲁迅。
哈金的《战废品》和《自由生活》非常出色。叙述视角是从某个选择的困境展开。在此意义上讲,哈金所有的长篇都是同一个视角。
我觉得《等待》的结尾部分处理得不够理想。描述孔林和曼娜的婚姻结局以及孔林最后拜访前妻,让悲剧的性质变得模糊起来了。
看波德莱尔照片,一张大额头、贞烈美妇人的面孔。
德拉克罗瓦画中披红袍的圣约翰,像猫王,已经梳着摇滚乐手的发型了。
拉萨之行。黄昏街角酒吧门口瞥见蜜色皮肤的藏族时尚少年,神态极高傲,透着这个年龄享乐主义的冷漠和憔悴(蓄着细细山羊胡须的脸)。
可可西里的雨消失在蜿蜒消失的草地和沼泽中。
见了才知道这里连一只飞鸟都见不到。
这个八廓街早就不是更敦群培从窗口眺望女人的那个八廓街了。
我没有能力评价更敦群培的绘画技巧。他的素描和油画我很喜欢,手提油壶的印度少女像,还有白度母画像等。这位酷爱女人的画僧是个伟大的诗人。
更敦群培对知识、色欲和佛陀的兴趣,处处显示人的自我定义的原创性。(《西藏欲经》)
藏民的家屋,黑颜料髹漆窗框,色彩感大胆的装饰,衬以蓝天和高原光照。
宝鸡一带,绿油油的田地时见孤树一棵。那些小砖房,门面都做得像寿星的红漆棺材。
兰波的福音散文。写毕士大的洗身池一节,笔调尤为深邃。
巴别尔、博尔赫斯和达尼洛·基什也善于此种描写。
兰波那种异邦人的视界,—在神性中表呈凡俗,在凡俗中注入神秘。
巴别尔深得其象征主义精髓。
惠特曼和普鲁斯特不都是毕生在写一本书吗?
惠特曼一首诗的标题—《处女膜哟!有处女膜的人哟!》。
读热内《小偷日记》。作者身上显然流着麦尔维尔血液。转瞬的奇想和狂热,流浪汉信仰和“同志”情谊,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欲和揭示欲。
文学批评,博学固然好,最可贵的还是乔治·斯坦纳细读《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份用心。
乔治·斯坦纳深明批评的职责与权限。他将文学批评置于从属性地位。他遭到“憎恨学派”的讥笑和诋毁,有什么奇怪的呢?
同样是谈《安娜·卡列尼娜》,他比帕慕克(诺顿演讲)谈得更有启发性。
熊秉明认为伦勃朗《拔示巴》画的是母性肉体(“母体”),不同于鲁本斯“兽体”之肉感。这个看法也许需要修正。伦勃朗画中的女性都是些村妇,唯有这个拔示巴(确实是做过母亲的妇人胴体)画得秀色可人。
读《红与黑》,读到于连在贝尚松神学院突然昏倒那一幕,觉得这本书像是以前没读过似的。司汤达有不少笔触是奇特而有趣的。写主教在穿衣镜前试衣,这个细节读来让人着迷。
译《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康拉德的笔触极为精致,但一旦带有腐蚀性的嘲讽,其表现的力度就减弱了。(写日内瓦那些章节)
《八月之光》的十七、十八、十九这几章感觉还是有些粗率。海因斯夫妇和珀西·格雷姆的出场像是滑稽剧里跑龙套的,又有一种梦魇的气味。这是福克纳小说的一个特点,角色全是古怪的(孕妇莉娜这个人其实也是古怪的),他们轻易即可进入剧情的核心,像魔术师的道具召之即来。作为配角他们显得太过独特和主动,作为主角又明显戏份不够;他们的故事不能在已经设定的框架内充分展开。福克纳对布局和线索的配置经过反复考虑,是精心加以控制的,用他的话说就像是设计师布置橱窗展览。但是这几章的处理似乎还是显得有些聪明过头,最后给人的感觉严格说来有点像是在堆砌。
昆德拉何以没有看出马尔克斯激流般的语言是源自于福克纳?
《八月之光》写克里斯默斯的部分尤其浓艳。
《八月之光》写得最动人的还是克里斯默斯的成长史和初恋。还有莉娜的性格,也写得妙,单纯而又深不可测,她那种单纯似乎到了让人觉得有趣而害怕的程度。拜伦·邦奇和海托华牧师的那几场对话也写得十分出色。
福克纳擅长将恶棍的故事写得凄恻感人。莉娜和克里斯默斯,这两个人物都不是观念的象征或某种抽象观念的人格化产物。他们的形象中糅进了深刻、富于活力的思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善人与恶人,纯然鲜活的。这两个人物的光芒似乎将另一个主角海托华牧师掩盖了。然而,无论是克里斯默斯、莉娜、海托华牧师还是拜伦·邦奇,这些形象唯有在青春的善感和青春的追思之中才能被创造出来。
性挫折,失败感,孩子气,一事无成的荒废,恐惧生活者,老处女,神经失常和精神分裂,被社会驱逐的人……福克纳创造他的人物谱系,经由丰富的内省和诗性的直觉,揭示了这些表面上毫无干系的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珀西·格雷姆割掉了克里斯默斯的生殖器,这一幕的耸人听闻与金鱼眼用玉米棒子强奸谭波尔并无差异。克里斯默斯的无能与金鱼眼的无能在本质上也没有差异。
唐纳德·亚当斯(Donald Adams)的评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同情和公理已进入此书,在道德主题的表现上是一个飞跃。
强烈的沉思性格和强烈的自然主义,两者本质上有一致取向。
强烈的沉思性格。风景画的悲剧味。(雷斯达尔的风景画是与绝对物展开的对话。)
《敖德萨故事》插图本(戴骢译/王天兵编)的封面,是一幅巴别尔的照相。明朗的大额头,眼镜片后面那种一览无遗的嘲弄而快活的眼神,他惯常的狡黠笑容,像是随时都在伏案聆听或构思他的滑稽故事。
对巴别尔来说,写作等于是搞宫廷政变(借用木心的一个用语)。
《敖德萨故事》中文版收录有作者发表于一九三二年的自传小说《路》,回忆一九一八年冬,他只身一人从敖德萨前往彼得堡,投靠刚成立的苏维埃肃反委员会—契卡。由于故事的叙述加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细节让人着实感到震惊。
作者叙述他在基辅换车后,车站报务员开始检查证件,坐在巴别尔旁边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是教师。“报务员看了他俩由卢那察尔斯基签署的委任状,便从皮袄里拔出一支枪管又细又脏的毛瑟枪,朝着教师的脸就是一枪”。随后,报务员的助手“解开死者裤裆的扣子,用一把小折刀割下死者的生殖器,将它塞进教师妻子的嘴里”;“教师妻子柔软的脖子一下子粗了起来。她一声不吭。……犹太人被逐出一节节车厢,撵到雪地里。枪声像人声那样时起时伏。”
巴别尔侥幸逃过一命,穿过这个严寒的布满枪杀和凶兆的人间地狱,忍饥挨饿,最后到达目的地。在设立于皇宫的契卡办公室参加工作,他的感受是—“一天未过,我就应有尽有了—有衣服、饭食和同志,那是忠于友谊、生死与共的同志,除了在我们国家外,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同志。”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我的思想充实而愉快美好的生活,就这样在十三年之前开始了。”
巴别尔大概没有想到,就在这间办公室,也是犹太裔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后来亲眼目睹契卡的官员胡乱填写死刑名单,那种草菅人命的做法简直令人发指。诗人因愤怒至极而失去理智,竟疯狂袭击契卡人员,差点丢掉性命。
巴别尔本人则于一九二○年加入布琼尼元帅的骑兵军进攻波兰,在曼德尔斯塔姆闹事那会儿,他已经不在那间办公室工作了。
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忠于友谊、生死与共”的同志,是否要比火车上残杀犹太人的同志更加富有人性,表现得更好些。
《路》对革命暴力的描写是出色的,就像巴别尔的其他作品,寥寥几行字便将某个不寻常的场景浮雕般刻画出来,而形成这个场景的历史和社会学原因,通常需要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才能解释清楚。这是作家巴别尔过人的本领。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行文简洁经济,就像人们提到海明威的文字时称颂的那样,还不如说,巴别尔的作品包含着他老师莫泊桑也未必具备的写作诀窍,那是一种独特的腌制和加工原材料的方法,是一种“言语的炼金术”。
《路》的基调前后不统一,尽管故事的线索连贯,交代也是完整的。前半篇叙述令人屏息,充满残酷和震惊,后半篇则别有意趣,是在枯索寂静的呢喃自语中荡漾的一点氤氲热气。作品虽写暴力和黑暗,基调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为读者可以发现,小说结局不是前面叙述情节的一种解脱或解决,而是加入了另一种质料的东西,加以调制和混合,—融入他的幻象或迷人的自我镜像。
也许,《路》最感兴趣的读者未必是同时代犹太裔作家爱伦堡、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未必是作者深表感激的契卡办公室的同志,还有崇拜他的那批固定的读者群。它的第一读者应为阿尔蒂尔·兰波,诗人和冒险家,已在前一个世纪末的马赛港医院里去世。
兰波拜读小说会作何感想?看到这个精通法语的犹太小伙子九死一生逃脱劫难,以其亲身经历兑现《彩画集》的幻象,—在被占领的宫殿里,身穿国王打补丁的睡袍,秉烛细读这个朝代走向毁灭的编年史……
是的,巴别尔兑现了兰波诗歌里的幻象。也许他做了诗人梦寐以求也做不到的事情。在皇后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的书房里,他抽着沙皇的雪茄烟,断断续续听见帷幕后面有人在介绍他:“小伙子是自己人……”于是,他便成了携带毛瑟枪和死刑令的契卡一员。
小说结尾交代此次冒险的结果,如同是兰波诗歌的一个注脚或片段:“……在原彼得堡市政府大厅的一个单独的角落里,我开始翻译外交官、纵火犯和间谍的供词。”
姜白石:“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是孤魂,亦是诗魂。
李长吉:“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
“梦中梦”(爱伦·坡一首诗的标题)可用来概括李长吉。
陶渊明:“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以陈寅恪所说的“新道家”看陶渊明,顿觉索然无味。
庐山某展厅挂有一幅陶渊明家乡全景图。凑近观之,蓝天下昏睡的一片平地,令人略感怅惘的平原风景或平面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