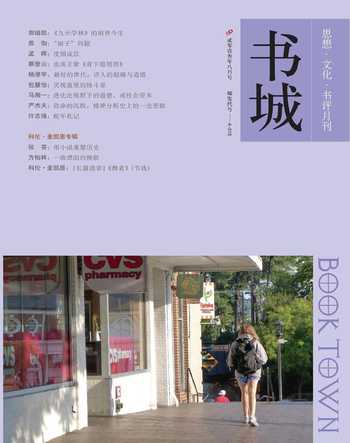“面子”问题
思伽
五月,《蒋公的面子》来到北京,戏外比戏里热闹,情节更跌宕,冲突更激烈,人物更丰满,情绪更微妙。
面对“业余”的批评之声,该剧导演吕效平教授把观众分成了“知识界”和“戏剧界”,说前者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后者,比如在北大的演出是多么火爆啊!然后,有“戏剧界”人士认为吕教授在戏外的种种“秀”令人厌恶,以长微博宣战。针对戏的“批评”呢,也有,有大夸特夸宣布“历史上见”的,有戏没看过本子没读过就敢抡棒子的……
这番热闹,让我这个观众小小兴奋了一阵之后,忽地心中一凉。其实,我只想听人谈谈,《蒋公的面子》作为一出“舞台剧”,好在哪儿,不足在哪儿,而不是泛泛地谈“文化”,说“灵魂”,高举“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大旗,挥舞批判“果粉”的意识形态大棒—特别是在这出戏的分量原本不足以承载这一切,甚至完全错位的时候。
《蒋公的面子》,就导表演等舞台呈现环节而言,是得不到高分的。有人称其“质朴”,这个无法赞同,它只是简陋而已,就像那没什么想法,约等于照明的舞台光。演员吐字不清晰,稍一转身,我坐在侧面就听不清台词。舞台调度单一,全剧节奏单调,在“文革”与民国时空交替的框架下,人物“争吵—缓和—争吵”的模式不断重复,我想,节奏的某种琐碎感,也与导演处理欠火候有关。
戏剧不等同于文本,必须结合舞台呈现来整体衡量,但作为一出从综合大学走出的戏,《蒋公的面子》导表演弱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它所创造的“奇迹”,人们首先赞不绝口的,是剧本,是一个三年级本科生的“天才之作”。确实,这出戏才华闪耀,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我的疑问是,我们需要夸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如其分而不至将人“捧杀”呢?难道戏剧评论,可以仅仅停留在人物分析层面,再意淫一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满足了吗?我进一步的疑惑是,这出戏在剧作层面上的毛病难道不明显吗?既然导演都说它国内“一流”,国际上则是“三年级习作”,为什么不能好好分析、争论一番它的短长,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创作呢?
再一想,觉得自己太矫情了。现在的微博,就喜欢借力打力,借题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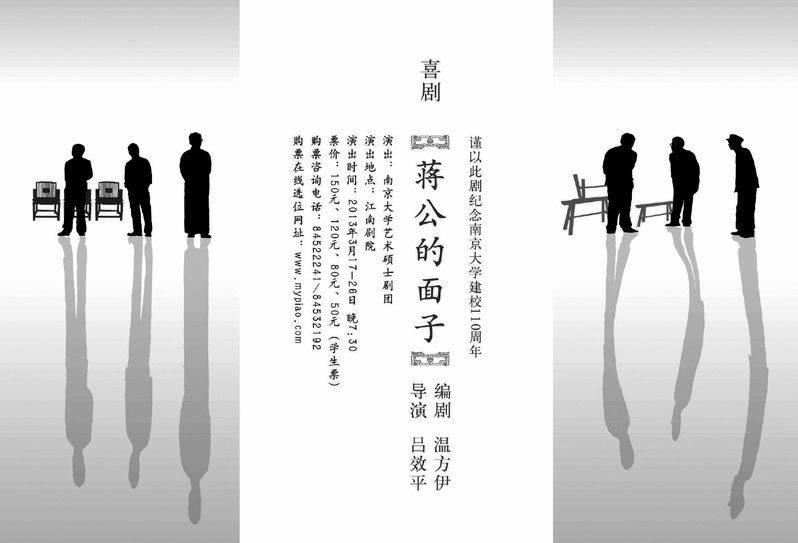
《蒋公的面子》有一个非常好的戏剧动机,也有很好的角色设置,包括三个人性格色彩的分配,体现了难得的戏剧思维。成就一出戏剧的核心发动机和主要部件,都闪闪发光,耀人眼目。但是我觉得,要看我们在什么体量上来衡量这部剧作,如果作为一出独幕剧,它完成得不错;如果视之为三至四幕的完整大戏,它只完成了第一幕,最多是走到了第二幕。
“文革”戏在全剧中基本只起了结构上的作用,戏的主干集中在民国时空:三位教授面对要不要去赴宴的矛盾,各怀鬼胎,经过一连串的争吵,相继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剧情到此为止,“文革”中三人记忆混淆是个尾声。这犹如一个大功率发动机,还没有造就足够的光和热,就停转了。剧情发展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对人物内心的揭示也就不够狠,不够高。完整的好戏,要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层层翻高,在最高处终止、坠落。《蒋公的面子》翻出了漂亮的跟头,但刚刚向上飞了一层,还没有够到最高点。
三位教授的戏,是在争吵与暂时和解中展开的,两人斗嘴,一人和稀泥,其间不乏精彩的段落和台词。然而这种戏剧冲突模式不断重复,在相继揭示了三人的性格,翻出了各自的底牌后,就失去了实际作用,被同样的动机和情绪支配的争吵不断重复,导致戏剧的行动线不够明晰,前进得不够利落,节奏显得有些琐碎和拖沓(不过,我没看过剧本,节奏问题与导演处理也有关系,可能会影响对剧本的感受)。
还有一点想法,是关于台词。很多人喜欢这部戏的台词,时有妙语警句,而且文绉绉的,又吟诗又唱“不提防”。确实,三位教授出口成章,很符合他们的身份,但特别有“文化”的台词,放到舞台上不见得都是好台词。我更喜欢那些生活化的口语,针砭时弊的台词很自然,并非生硬造作胳肢观众,十分难得。
戏中的“文革”段落,是三个老人原地转磨,弱点比较明显,就不多说了。
还要从剧本回到演出。我是在海淀剧院看的,和传说中的北大演出一样,观众也很爱笑,现场气氛也很热烈。我不能说自己看得很投入,这不是创作者的问题,是我自己的缘故,现在看戏难得动感情。戏看久了,会麻木,会挑剔,会失去一些本质的快乐,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火爆的演出现场的确令人兴奋,但如果坚信观众反应的热烈程度和戏剧质量成正比,那就有点奇怪了。多年前有个台湾剧,说现在的剧场是“三声律代替了三一律”。何谓三声律?“掌声、笑声、安可声”。用掌声和笑声来衡量戏剧水准,和用票房来衡量又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句多余的话。写下这篇东西,没有苛求编剧的意思,温姑娘的确才华出众,令人佩服,而且戏里戏外那股轻松自如的气息,非常清新,感觉和较劲拧巴的老一辈大不相同,绝对值得期待。不过,她还不是大学期间写出了《雷雨》的曹禺。所以我觉得,谈戏比夸人更重要,谈不足比夸戏更重要。多谈谈戏,以防“天才”出现时,我们认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