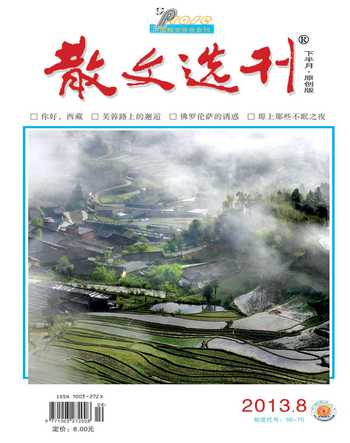老屋旁的水井
丁长兴
清明时节,我来到父亲坟前,祭拜父亲后,顺道看望了年少时曾居住过的老屋旁的水井。
水井,离我住的老屋有800多米。听大人讲,这口水井,解放前国民政府建福源炼铁厂四高炉时就有了她,可谓历史悠久。水井不大,仅有一米深、直径最多也只有一米左右。水井终年细水长流,无论天干大旱、打霜落雪也从未见干枯结冰。最奇的是毛主席逝世那年,附近的竹子冻死干枯、河水断流,但井水仍然满盈。闻讯后,方圆几十里的群众成群结队的赶来喝“神水”。我母亲为了方便人们喝水,还叫我把家里的水瓢放在井边,方便喝水的人饮用。
水井,不仅滋润哺育了我,还承载了我年幼时的童趣。我住的老屋是个大院子,同院住着10户人家,每家大人小孩加起有七八十口人,加上附近职工宿舍的职工有将近两百来人。这两百来人的饮用水,主要靠这口水井供给。小时候父亲工作地离家较远,每天上下班要走十来里路。母亲体弱多病,也难以承担重活。家里吃水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和兄弟的肩上。不知什么原因,大人把挑水叫背水。开始几年是我和兄弟抬水,我稍大后就一个人背水。我们上学去了,不管哪家没水了,大人只要叫一声,同院的人或在休息的职工就会帮着去背水。水井没有盖子,无论是住在附近的大人小孩或是路人,从未向水井里扔任何杂物,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水井。水井里飘落了杂物,背水的和路人都会主动把她清理干净。水井用久了,一年需要淘两三次井。淘井是件十分严肃庄重的事。井里空间小,只容得下一个人,干这活的一般都是各家各户的男人。淘井,先要用水桶把井里的水提干,然后再安排人下去淘泥沙。下去的人先要把脚洗干净,遇到冬天还得喝口酒。把水井里的泥石沙淘干净后,再放进去从河里捞起的鹅卵石和粗沙。等到水井满后,再用水桶将其提干,如此反复两三次后就可饮用了。站在井旁看热闹的小孩,总是争着抢着去喝淘井后的第一口水。
最有趣的是抢“银水”。那时我们院子有大年初一抢“银水”的习俗。年年初一凌晨,父母都催着各家小孩起床。说是抢,但院子里的小孩都在互相邀约,等到齐了才会一起去背水。大人叫把水背回家才能喝,往往是我们一帮小孩到了水井,排队轮流把水喝了,才把水背回家。不知是哪位院子里的孩子王兴的规矩,每年喝“银水”按年龄大小排序,记忆中,我在院子住了十几年只喝了一次第一口“银水”。我们几十个小孩,可能有小朋友搬家后也没喝上第一口。特别是水井因1976年那个特殊时候出名后,来喝“银水”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天亮了,还有人在排队喝。尽管我们年年都在喝“银水”,但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小孩仍然吃不饱饭。
水井里的水十分香甜可口。院子里住的大人小孩,一年四季都喝井水,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烧开水泡茶。经常来家里的熟客,久而久之也养成了拿个碗在水缸里舀水喝的习惯。挑回家的井水存放在水缸里,喝到嘴里凉爽宜人,冬天也不冰人,从未听说喝了井水不舒服或生病的。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后,三番五次请父母同住,不知是父母住惯了老屋,或是喝惯了井水,一直不愿与我们同住。直到父亲走了,母亲才肯来与我们同住。尔后,除给父亲扫墓外,就再也没有去喝过井水。
这次清明节给父亲扫完墓后,看到老屋仍在,就想起去喝口井水。当我兴致勃勃走到井边一看,水井面目全非,已被弃土填埋,杂草丛生,只有一块井石孤零零地露在外边。听现住在老屋的人说,水井前几年就已干枯了,山脚下的小河的溪水也断流了,已有好几年附近居民的吃水也成了问题。问起原因,说是山上山下开采煤窑破坏了水源,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耳闻目睹水井的此情此景,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好想再喝一口老屋旁的井水……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杜凤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