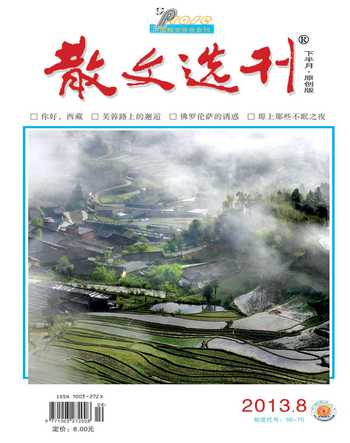幽光沉静话“包浆”
初玩收藏时,不知“包浆”为何物,乃至行家点破,方才领悟。原来,“包浆”就是那道经岁月流逝而于器物表面形成的光泽,恍若老竹席表面那袭暗红光润之色。按作家汤世杰的说法,便是“虽微弱含蓄,却润泽幽隐,能予人一份淡淡的亲切,有如古君子之谦和雅蔼;而细聆深悟,便觉有高僧鸿儒之隽语如诉,既清凉也温润”。
“包浆”之所以“能予人一份淡淡的亲切”,恰恰是因为它也是古代艺术品的历史沧桑和人文信息最直观的体现。诚如著名节目主持人、收藏家王刚所言:“说某某器物有‘包浆,不是指它有多么贵重,而是指它因时间的流逝而沾染上了浓浓的‘人气儿,有了‘贵气,这样的气质,再高明的高仿也仿不出来。”
前不久,我应邀去浙江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鑫建筑艺术博物馆参观。据董事长王水鑫介绍,不但其收藏的许多建筑老构件是纯正的“徽州”货,博物馆所建的许多栋梁、椽子、大门等也是“徽州”的老东西。定睛细看,便发现了岁月流逝在这些老物件上留下的特有的质感和色泽。走近它们,这里摸摸,那里嗅嗅,那曾经的徽州建筑,便一幢幢、一片片从幽光沉静的“包浆”中透出向我奔袭而来——恍如电影中的慢镜头,诱我的心跌入修长的徽州历史纵深、文化卷轴,人则分明成了这幅国画里的一滴墨。是啊,变幻的“包浆”恍若湖光山色,几经转折,终究生生还原出徽商曾经的繁荣。看,徽商们停靠在渔梁埠边的船舶,正堆满谷子、生盐巴、上等的茶与土乡特产,将要从这里扬帆出发。
或许,谁也不会相信,其实,石头也可以有“包浆”。它可以是政治象征、经济载体、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可以是文化书写的对象。“石头不仅存在于遥远的神话、模糊不清的历史、高高在上的幻象,还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曾经踏上过位于浙东大运河南岸绍兴县柯桥镇上谢桥至钱清镇秦皇段古纤道,其全长7.5公里,或单面临水,或双面临水。那以青石铺设的纤道,因了纤夫的踩踏、水浪的冲刷,更兼风雨雷电的打磨,青石板上竟有了挥之不去的“包浆”。伫立其上,青石上的“包浆”让我定格在我想象中的过去年代里,幻想着与那时风和雨的回声一起荡漾,与那时的船家、纤夫重逢。散文家郑休白女士曾经感叹:“历经千年沧桑,古纤道已经从最早的实用价值,嬗变為当今的审美价值。负载太多的苍凉和悲郁,也早已遁进了历史的厚尘,所有的惊异震撼,都凝聚成一声叹息:古纤道太美了!”是啊,这种美,质朴而亲切,精巧而灵动,浩大而细腻,那牢牢附着于青石板上的“包浆”,便是最生动的见证者。人与自然掺和造就的这“包浆”,亦让著名电影导演谢晋相信,其是历史感、沧桑感和诗意化的化身,于是也便有了《祝福》、《舞台姐妹》在古纤道的拍摄。当古纤道上的“包浆”成了另一种摄影机的时候,她要昭示的当是“苦难与美好的结合,柔与刚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包浆”,当是有着自然的时间的外来因素的作用。然而,当人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那种“包浆”才叫可眼可心。我的外祖父,早先毕业于上海美专,是刘海粟大师的学生。他不仅画得一手好画,而且写得一手精致的蝇头小楷。大凡给人写信,他都是用毛笔写的。尽管街上已有现成的墨汁可买,可他愿意自己现磨。在书房,我发现外祖父那方有着精美雕刻的砚台色泽沉稳,砚体莹润,周身散发出古朴的气息。问之,则曰:“关键在于用砚养砚,要坚持每天磨墨洗砚,以防墨干燥龟裂而损伤砚面;再就是要注意只磨洗砚堂而不可磨砚的其他部位,否则会磨损‘包浆,以至伤及雕刻的细部。”而今,外祖父已经走了,这方石砚已然成为我的收藏。每每抚摸这方石砚,总觉余温未散,透过温润的“包浆”,则如晤外祖父。是的,我仿佛看到外祖父正聚精会神磨砚持笔,仿佛看到他正小心翼翼洗砚养砚……是啊,每每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那含蓄温婉的“包浆”其回眸一笑,终能给人以莫大的心灵慰藉。
石砚如此,紫砂壶更值得玩赏。前些年,我去杭州市滨江区韩美林大师家拜访。临走时,他与夫人周建萍赠我一把紫砂壶。这把造型别致的紫砂壶,在我看来,自代表着一种出尘脱俗的人格,若入茶续水,必能满足色香味的要求,浸润自己的心情。有人劝我不要去使用这把壶,而要好好收藏。我不以为然,不去使用,便无以打通与这把紫砂壶交流所需的气场,也背悖了大师与夫人赠我紫砂壶的初衷。在请教行家以后,我便开始了与紫砂壶的耳鬓厮磨。几年下来,这把壶看上去朴拙粗粝的紫砂质感,抚摸时却像婴儿肌肤。尤其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包浆”,不仅契合了紫砂曾经沉睡了千万年的泥性,也暗合了天光的神韵。想起了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的话:“世上最伟大的和震撼人心的吻是天空亲吻大地。”我油然想及,这紫砂壶上的“包浆”,不就是“天空亲吻大地”留下的吗?
不知为何,我天生喜欢紫砂壶。无论在家抑或在办公室,我就是愿用紫砂壶沏茶,不啻因为用紫砂沏成的茶别有滋味,更因为紫砂壶“是积蓄、酝酿和守恒,像极了人生,缓缓、迢迢的过程”。近年来,我还有幸收藏到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鲁迅美院教授关宝琮先生,以及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师汪洋先生刻制的紫砂壶。自然,我亦不愿束之高阁,而是捧之抚之。因为经常使用,也因为不辍养壶,那足让人怡倦眼、安心魂的“包浆”,还竟然骗过了一些品壶行家——他们以为这是二三十年前的紫砂壶。作家徐风说过:“文人喜欢紫砂壶,可能跟紫砂质朴内蕴的特质有关。紫砂器的构造充满自由和灵性,可以暖心温心,可以成就一种包含生命想象的大美,于是品呷香茗、把玩紫砂壶渐成为古时文人的风气,人生感怀寄寓其中,枕石醉陶已经足够,仕林官场已经忘情。若果既能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在一把紫砂壶上寻找入世与出世的平衡点,岂不妙哉!”我算不得文人,充其量不过是半个文人而已,但对于徐风先生的这番话,则信以为然。那精光隐润的“包浆”,不就是我一手持壶品茗、一手操笔抒怀的生动铺垫吗?想起绍兴乡贤、才高气傲的徐文长,为了寻觅一把紫砂壶,专门从绍兴跑去宜兴,并写下了“青箬旧对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的诗句。假若这把紫砂壶还幸存的话,想必定当是“包浆”满满的了。拭去尘埃,徐文长其脾性其气度其操守连同满匝匝的故事,便会从中流淌而出,那是怎样的一种诗性情绪呀!
“包浆”,已然成为我们与时空沟通,与器物对话的钥匙。自然,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通感”现象的客观存在。要知道,“通感”是实现有效“沟通”与“对话”的黏合剂、放大器。“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是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名句,常被用来解释“不同感觉在大脑中互相沟通交错”的现象。英国一项最新研究说,这种现象有其生理基础。研究显示,如果把大脑皮层敏感度调得更高,受试者的“通感”表现就更为明显,而如果降低大脑皮层的敏感度,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通感”现象。由此类推,“包浆”就是敏感度,“包浆”愈纯正愈醇厚,则鉴赏者的“通感”能力就愈强。反之,则不然。想想也是,一件被拭去了“包浆”的老物件,因为缺失了时空交错、历史文化交汇的生动故事,终让人无以“通感”。事实上,真正的行家,就得靠“包浆”来“通感”,来辨别老物件的真伪优劣,进而去把握其价值。
不谙“包浆”,“通感”能力弱,无论收藏抑或鉴赏难免频频上当。清末“洋务派”的中坚人物、曾任湖广总督,后又任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等要职的张之洞,有一年,其奉皇上之命回朝述职,住在南门附近一家旅馆。他闲暇时喜好收藏文物,有一天在一家古玩店发现一口形状古怪、古色古香,缸体四周刻满小蝌蚪状的篆字。在听了店主编造的“故事”后,他愈发动心,决意收藏,最后讨价还价至两千两银子成交。一天晚上,天降大雨,第二天早上张之洞起床后径往观赏,然而,缸口四周的篆字已让大雨冲得只字不留。原来,那东西是用一种牛皮纸做的,再用蜡涂上黑面光亮如釉的颜色,然后镌上铭文。张之洞之所以上当受骗,原因之一是他不会看“包浆”。他财大气粗,喜欢奇特的、贵重的,加之不懂装懂,难免屡屡上当。如果他懂得“包浆”为何物,如果他经常看察“包浆”、触摸“包浆”,就不至于被“牛皮纸和蜡合成”的所谓“光亮如釉的颜色”蒙骗。毕竟,真假“包浆”在行家眼里,那是泾渭分明的。
其实,一个真正深谙收藏的人,不仅懂得“包浆”的来由,而且也一定参与过“包浆”的制造。或许,用“制造”这个词,似乎显得太粗粝、太呆板,用收藏界的行话,应该叫“盘”才对。“盘”,就是用手不断摩挲器物,如石头、青铜器、玉器、瓷器、木器、牙角等,都可以是“盘”的对象。
我的一位好友同时也是著名收藏家、书画家的娄国良先生,其腰间挂着的那块斧形汉玉,已然被他“盘”了整整30年。每每读书、看电视,他都会解下来,用手“盘”玩。那“包浆”,在不经意间重新塑造了汉玉的形象。他告诉我:“这块斧形汉玉,不仅我合手合心,每每与藏家交流,大家也都被这汉玉上温润的‘包浆震撼。曾有一位台湾的藏家愿拿贵重的藏品与我交换,我委婉地谢绝了。因为朝夕相处,我早已与这块汉玉有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了。‘包浆是这块汉玉的眼睛,每每与之对视,我们就会流露出相互倾慕的眼神和彼此心领神会的灵犀。”
有位文物鉴赏家说得好:“‘包浆可以由土埋水浸造成,但最好的,还是在‘盘玩之后留下的岁月痕迹——它沉着冷静、中庸和谐,显露出一种温存的时光感。”想想也是,不必说被动的地下生成显得生硬,人的“盘”玩,毕竟因为有温度而显得温润,有人性而通灵性,而即便是用现代打磨技术快速生成,也不如用双手“盘”玩来得更亲切更自然,也更少物理性的伤害。有位哲人说过:“人与机器的关系,本质构建于人的自觉、自由、创造性的活动和发展的联系之上。机器程式化的重复劳动和人类个性化的创造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电子舌头能判断出来的只是一瓶葡萄酒的优劣。而人却可以体会到酒香里蕴涵的情感与思想,甚至结合自己的阅历传递独到的图景和感悟。”其实,盘“玩”古董何以不是如此?现代机器的打磨怎与人的“盘”玩相提并论?
事实上,一个“盘”字,也终究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分离了出来。谷泉先生曾说过:“東西方文化的差异,在‘盘玩上大相径庭。以石头为例证,中国的石头,无论玉石、翡翠、青田石、寿山石,还是灵璧石、太湖石、英石、昆石等,皆以‘盘玩后浓厚的‘包浆为上。西方的钻石、红蓝宝石,或者是祖母绿、蛋白石等,被人抚摸过后,原本耀眼的光芒退去,就需要重新清洗,以保证透明发亮的特性。这与中国器物‘盘玩后更加光彩夺目,完全相反。”于是,想到了《说文解字》里对“盘”的解释:“盘为承水器,以匜沃水,以盘承之,古者晨必洒手,日日皆然,引申为日日新。”是啊,中国的器物皆为自然材料,其似乎有着更为宽厚的包容之心,尤其当与人的双手产生良性互动之时,器物表面终于“每天发生变化,日日为新”,而双双的“情感和心态也日日为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藏家的“盘”玩不仅仅是抒情,更不是煽情,而是一种真情的投入,一种对承载历史文化信息的物件的敬畏,一种静下心来、垂下头来的聆听,一种向往古典并将那物件和自己的身体与心连为一体的境界。
一件破残的老古董,虽说人世间再沧桑的脸,在它面前,也显得幼嫩了点;再苍老的生命,在它面前,也显得鲜明了些,但只要“包浆”在,就证明它还活着,心跳着,眼亮着,话说着。至今,我才渐渐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痴迷收藏,除了有一部分人是冲着经济价值去的外,更多的唯在于“包浆”的诱惑,因为透过“包浆”,里面有着太多的“鬼斧神工”,太多的温度与质感,太多的人与物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