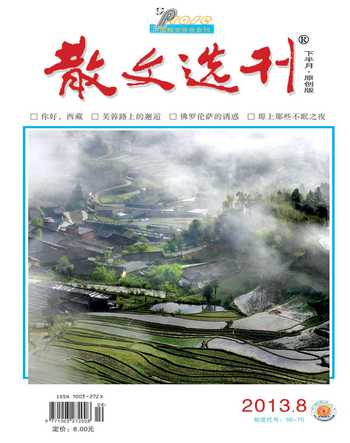大写的“妻”
胡封亮
一
妻出生在农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弟弟。在那个动乱年代,初中毕业便辍学在家,用稚嫩的身躯挑起生活的重负。结婚,对妻子来说,简直是从风雨中走出又进了泥潭。我姊妹五个,结婚时一个弟弟上高中,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读小学。婚后,要和父亲耕种20多亩责任田,全家人的穿戴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为让全家人都穿得体体面面。妻让父亲买了台缝纫机,并利用农闲时向邻居学习裁剪,比葫芦画瓢地给弟妹们做衣服。年复一年,直到他们成家。
两个儿子相继问世,她仍固守着那份责任。那年月的冬季,农村供电极不正常,往往深夜两三点才会来电。每天吃过晚饭,她就早早哄着两个儿子睡觉。来电了,便起身穿上上衣,两腿夹着大儿子,身边躺着小儿子,倚在床头纳鞋底,织毛衣,为的是让全家人过年时能穿上新衣新鞋。星期天回家度假,看着她这样没明没夜的辛劳,总是心存愧疚。“没法,这活儿谁也替不了我。”她就是这样的乐天性格。
在农村老家的15年中,家里的20多亩责任田,除麦秋两季收获时在外工作的几个人回家帮几天忙外,其他都是她和父亲两个人侍弄。
15年中,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从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所有的学费及生活费都要靠家里种地的收入。妻总是告诫爸妈:“别让他们手里缺钱,让别人看不起咱”。
弟弟妹妹相继成了家。盖房子、送彩礼,办婚事她都亲历亲为,毫无怨言。成家后的弟弟妹妹,农村老家成了他们的“旅馆”,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来家小住几天,然后各奔东西。妻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因此,直到现在,虽然这个大家庭已是四世同堂28口人,弟兄、姊妹、妯娌、婆媳仍是情同手足,相敬如宾。没有任何不和。作为大嫂,妻总是一呼百应。每年的除夕,全家人都要在我家团聚,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其乐融融。
15年中,她没和爸妈红过脸吵过嘴。村里人都羡慕得对母亲说:“您的儿媳妇就像亲闺女。”那年,妻和两个儿子农转非后,在县生产资料公司安排了一份工作。回去搬家那个下午,老爸唉声叹气,欷歔不已,老妈泪流满面,寸步不离。“你走了,这个家可咋过呀?”“妈,看你,县城离家又不太远,我会常回来的。”妻故作轻松地调节着气氛。
拉着家具的汽车启动了,出了村子回头一看,村头,瑟瑟秋风中,仍屹立着两个遥望的身影。
二
结婚的第二年秋天,二弟考上省城郑州的一所大专。
这消息对于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的八口之家来说,可谓喜忧参半。虽然入学后国家对大学生有伙食补贴,可眼下家里连转粮食关系所需的一百斤玉米都拿不出来,那几天,父亲整天愁眉不展。
妻抽空回了一趟娘家,回来笑着对父亲说:“爸,玉米我叫俺妈准备好了,你明天骑个车去带走,到乡里转粮食关系吧。”
接下来,妻子又忙活开来。去集上给弟弟买衣服鞋袜,从为数不多嫁妆里,挑出褥子、被子、床单、枕头、枕巾,就连同事用钩针钩的,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的盖被子的饰品,都一股脑地给了弟弟。
三年后,弟弟学成归来,参加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份工资,自己一分都没舍得花。专门骑自行车跑了40多里从县城回到家。“嫂子,这50块钱是我领的工资,你拿着,去给您和侄子买衣服吧。”50块钱,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目,推辞不掉收下后,晚上,妻又如数把钱交给了母亲。
第二天,弟弟得知后,“妈,不行不行,把钱拿来,那是叫嫂子花的。”母亲笑着把钱拿出来,塞给妻子,“他嫂,这是恁兄弟的一份心意,你就接着吧。”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俗话说,过日子比树叶还稠。但妻子以身作则,无私奉献赢得了家人的信任与尊重。老爸老妈对她言听计从,弟妹妯娌以诚相待,二弟对她更是有求必应。走上处级领导岗位后,二弟仍不改初衷,以至于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弟弟妹妹及弟媳们便会异口同声地推举,“叫咱大嫂给二哥说。”一次,二弟来县城看父母,我们姊妹几个聚在一起闲聊。三弟开玩笑地说:“咱家你就听大嫂的。”二弟笑着回答:“当然,长兄如父,老嫂比母呀,咱家就大嫂的贡献大。”那时,妻子露出少有的开心。
父母搬到县城后,生活很不习惯,老两口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妻子变着法子哄老人高兴,今天给老人买件衣服,明天做点老人喜欢的饭菜,打电话让爸妈来家团聚,隔几天带着老妈去洗个澡,剪剪头。老妈双膝患骨质增生多年,行动不便。那天她去看老人,见老妈坐在凳子上用双缸洗衣机洗衣服。她二话没说,去门口的家电部买了台全自动洗衣机送去,并手把手教会老爸使用。爸妈高兴得合不拢嘴。
老妈入院半个月,那天是周末,在安阳工作的四弟也回来了。全家人坐在母亲的病床前,妻又发议论了。“瞧吧,咱妈病好了肯定不会走路,以后离不开人伺候了。”咋办?要不妯娌几个轮流去给老人做饭;要不花钱雇个保姆照料老人的生活;要不……议论了一会儿,大家都沉默了。倒是老爸挺身而出,“没事,以后我就是恁妈的专职保姆。”可谁都清楚,老爸虽然勤快,但不会做饭,一日三餐怎么解决?“没事,早上门口有早点,中午路边就是饭店,晚饭有豆奶和纯奶、酸奶。吃饭不是问题。”老爸的自信并没有缓释大家心头的纠结。
不幸被妻子言中。出院时的老妈双腿疼得连下床站立都很困难。这不,送了几天饭后,她没和任何人商量,没给任何人打招呼,便“自作主张”把爸妈接到家里。用妻子的话说:“老妈大病刚好,不在身边我放心不下。咱这个大家庭,就我是个‘闲人,可家里这一大摊子,我实在无法守在父母身边,想来想去,只有把二老接来。再说啦,我感觉,老人健在时给他们端口水喝,也比过世后哭天抹泪,大操大办强得多。”
朴素的道理,会派生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美德,感动着上一辈,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三
虽然农转非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妻子总也无法淡化她的土地情结。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我的工作性质又不能经常回家,每年的麦季还好对付,可秋季的水稻插秧、浇水、施肥、打药、除草都靠妻子一人请假回家忙活。盛夏季节,暑热难当。那年,水稻该打二遍农药了,妻子请假回家,下午,已参加工作,在县经贸委当司机的大儿子去郑州,我交代他下午顺道去老家把妻子接回来。下班时,儿子告诉我:“还有一方水稻的稻草没有薅完,俺妈说明天薅完草后打车回来。”我听后说:“不行,天这么热,打药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走,咱回家把恁妈叫回来。”
下晌没吃晚饭,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妻子见又来接她:“不是说了,我明天一早把稻草薅完就走吗。咋又来叫?”“天要把人热死了,稻草咱不薅了,快洗好衣服,咱回县城。”我的话不容置疑。妻子好不情愿地坐上车,连夜返回县城。
在烩面馆,一碗饭没有吃完,妻便头蒙恶心,吐得翻肠倒胃。农药中毒!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慌忙把她拉到县医院抢救。医生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给妻子挂上点滴。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呀,借助药物,妻子顽强地与死神搏斗,每一阵惊悸,都像利刃扎进我们的心脏;每一声呻吟,都撞击着脆弱的心理防线;每一次挣扎,都搅乱了两个儿子婆娑的泪眼。若非医生一次次地宽慰,真不知能否度过这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夜晚。
东方终于透出了鱼肚白,药物与毅力最终战胜了死神的威胁,妻子渐渐地安静下来,苍白的面孔,凌乱的头发,满身的虚汗,让人不寒而栗。中午,妻子才从昏迷中醒来,她强睁无神的双眸,看看守在身边的亲人,“我这是怎么了?咋会在这儿?……唉,要不是你非叫我回来,我恐怕难活到今天。”那凄楚的笑容,让人读出几多辛酸。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妻子每天都是六点多起床,打开火给老爸老妈煮荷包蛋,爸妈起床后就让他们吃下,送走上幼儿园的孙女后开始做早饭,然后端到老人房间。九点后就马不停蹄地上街买菜。然后紧锣密鼓地做午饭。下午三点多忙完后,就去陪老人聊天,想着法子逗老妈高兴。鼓励老妈康复锻炼。五点钟左右,再给老妈热桶牛奶,接着操持晚饭。往往到了晚上九点,才能把一天的家务忙完。
在妻子和老爸的精心伺候下,老妈天天眉开眼笑,一步一步地摆脱疾病的纠缠。那天,老妈勇敢地丢下拐杖,亦步亦趋地走出卧室,穿过客厅,走到餐厅的餐桌前。尽管老妈走得艰难,但毕竟让人看到希望。
妻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生气了她也會发脾气,累极了她也会抱怨,烦闷了她也会使性子,但全家人都知道,一会儿就会雨过天晴。在她眼里,日子就像一片片树叶,永远都是鲜嫩的。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