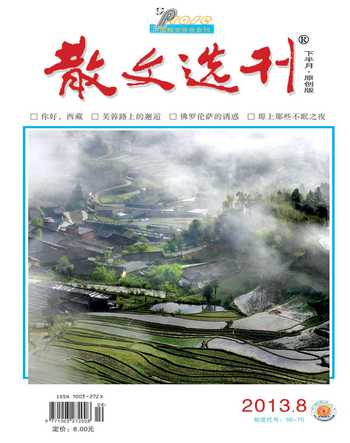我的肉体穿上盐的苦衣
南子
疼。痛。
她终于撞上了这个词。她一直想说和一直说不出来的,就是这个词。疼痛。
疼有多疼,痛有多痛,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热闹的餐桌旁,酒醉人酣。她一个人是清醒的,盯着一盘剩菜上的软蔫的叶子看,一直看,她微笑着,一切就这样了。她一遍遍地想。男人们抽烟、喝酒、谈笑……那些话像充了气的气球,怎么也碰不到她。
可她就是疼。
和男性不同,作为女性,会有许多不能表达的疼痛。疼痛仿佛是她们的一种特权,一种始终无法避免的东西,仿佛就是她们的激情,不能感知疼痛就仿佛失去了爱欲。这种疼痛在她的生命中将培植她的身体和她的目光所注视的地方。被不同的人说出,而有了一个具体的形状。
譬如我,是个耐痛值非常低的人。无论肉体还是精神,这两种痛的滋味我都不能够轻易忘却。对我而言,疼是一个更为简洁的名称,和我敏感的天性相对称。这在小时候不留心跌倒,遭遇病痛的折磨以及每一次发生的情感冲突中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在我看来,人的身体是所有事物中最为隐秘的东西。“我的身體”这样的事实只属于我自己。从我出生开始,我的身体就紧紧攫紧了我。我完好无缺地存在于自己的肉体中,不多不少,如同天平的两端——我是多么的健康啊,我这么轻而易举和完美地驯服了自己的身体,这恐怕就是身体与自我达成的一种和谐,让我发现自己并非贫穷。
我发现了自己的富饶。
我爱我的脆薄的身体,不要它疼。不要它受到外力的侵害。
比喻在某些时候,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事物的内部。
那么多的词,只有疼是不可以比喻自己的,它只能和痛对应。这种不适在人群中像穿了一件不合体的衣服,既然隐蔽是不可能的,那索性就穿上它。索性让自己在人群中成为一个有缺陷的人。
我判断不了,甚至完全不能判断自己除了疼痛所带来的不适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不适的感觉,我没有去想。
为什么会这样。
从小我就不是个诚实的孩子。
我六岁。在一个意外中。一只瓷盘子被我不慎失手碰落,碎瓷四处溅落,每个碎片都带有锋利的锐角,或疏或密地分散在地上,分离出瓷片上不完整的花朵和枝叶,大大增加了我的观赏乐趣,而暂时忘掉了即将到来的恐惧和危险……而气急败坏的父亲不声不响就在我的身后,生硬粗暴地用手钳住我细小的胳膊,我没有及时躲过他落下来的巴掌,一阵缓慢到来的晕眩后,疼痛使我清醒过来,我及时涌出了伤心的泪水。
父亲气急败坏的脸让我心生寒意,我怎么会爱他?强悍的人用暴力炫耀优势,弱势的人回避暴力以寻求安全。但所有怯懦的人都有一颗脆弱而敏感的心灵。我想我也是。
但我爱我知冷知热的、温暖而有弹性的肉体。对它拥有绝对的爱,使它成为我身体中秘藏的营养。及时将锋刃对准自己,那个叫做“疼”的神经在瞬间虚拟着我的全部的神经。“疼”的感觉遍布我的身体。它藏匿着,每个危险的处境都会藏着无数的疼。
我佯装被突然降临的眩晕击倒,捂住胸口,紧闭双眼,大口地喘气。身体渐渐痉挛起来。
伴随母亲的叫喊,父亲再次扬起的巴掌,弧线一样停在半空中,我在瞬间权衡了我的危险,伪装突发的心脏痉挛,让我一次次侥幸为避免受到责罚,而逃过暴虐父亲的铁拳。
不光彩的回忆让我略带羞耻,这是不是对自己的最早的伤害?为了逃避责罚所带来的疼痛,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成年后,我带着一种非理性的自嘲和厌恶感,视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
疼痛是一个不详的馈赠,不能具体度量。遭受疼痛的人会更加接近上帝吗?持续的疼痛带来一种厌倦。让我相信疼痛是一种赎罪。
疼痛对我而言,有时是一种不得不顺从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睡去的,但我知道我是怎么醒的。因为牙痛。
和痛风一样,牙疼都是属于医学描述过的最古老的那一类疼痛。疼痛是在瞬间发生的,令人猝不及防。
牙疼。让我在夜晚中不能安然入睡。疼是肉体的一根刺,或者潜伏的一只兽,有着过于清晰锐利的外形,时时等待着苏醒。让人不可思议。这一局部的疾病,当它发作起来的时候,却带来全身的震撼。里面像是插满了无数钢针,密集得如同液体,我的心因无法承受坚硬和尖利的东西,而变成一种巨大的空。没有颜色以及温度,让冰凉遍布我的全身,它散发出寒气,又像是为寒气所驱动。
我把脸埋在毯子里,但空气在毯子狭小的空间形成一股股弱小的气流,在与毯子的接触让我难以忍受。如波浪,震荡着我的脆弱的牙神经。就连汽车驶过家门口过立交桥时所引起的地板震动,也能加剧我的牙疼。
不眠之夜中,我被波浪般汹涌而来的疼惊醒。仅仅是一两粒痛牙,却让我整个的肉体一时间陷入了危机。浑身像着了火,又像是带来了凉。冷汗直冒。那是一种闷痛,无法形容,无法说出的疼,它持续地疼,像一枚钢针推进肉里,是碎裂,含混不清同时又是凝聚和绞合着的疼。没有方向,但又无比明晰,像另一种真实的快感在不设防的瞬间一下子袭击了我,或者说是占领了我。让我猝不及防。我想以惊恐的尖叫来缓和这种疼痛。但是很快,这种混浊晦暗的疼更为尖锐,如一股强劲无比的风带来短促而明亮的触角汹涌而来,带来锋利的断面,它来得太过强劲,像一个偷袭而来的敌人,一开始我就已输掉了。
最终,我噤住了声,眼眶里含满了绝望的泪水。
疼痛有特殊的编制详细的词汇。第二天,我用手捂着肿胀的脸,来到医院。我看着医生,用手抚摸了一下脸颊。因为不能选择一些恰当的词来描述,而使我看起来比没有疼痛时更加虚弱。疼痛的感觉又一次涌了上来。跟情欲涌上来的速度是一样的。我觉得自己虚弱极了。
人的自爱能力使每个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求欢乐。谁会憎恶自己,让自己感受疼痛?人人都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处于自然、完整的状态下,免除疼痛的烦扰。了解自己。人们也许将这样一句神谕格言运用于对自己身体的检视上。
但是,这可能吗?
刺破、灼烧、叮咬、拉扯或摩擦、挫撞到被毁坏的程度时,都能够产生疼痛。疼痛,与人类敏感的天性相对应,始终在维持和重新形成普遍秩序的过程中起着作用。因为它比训诫,更有威慑力,并对人们的美德和优点加以考验……疼痛是一种自我发现的形式。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受:“我遭受疼痛,所以我在。疼痛不在时,就有了欢乐。”
没有人天生是快乐的,除非他理应如此。正如苏格拉诺在《扉独》开篇刚被解除了镣铐时所说的那样:“朋友们,‘欢乐一词看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它和‘疼痛一词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寻常啊。二者不会在同一人身上共存,然而,如果我们得到了其中一个,那么另一个也会接踵而来……”
因而,在我们的生命中,注定要承受疼痛。
疼痛的方式,具体到某一细节,预示着对疾病的判断。
它是大有裨益的经历。是感官的呼吸,是我们的心智在提醒我们防备将要出现的危险。论《传统医学》中这样讲道:“哪里疼痛,哪里就需要治疗。”
疼痛是证明自己存在着。人如果无法感知疼痛,那绝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可悲的世界。
我去医院看望姐姐。
她的邻床是一位年轻女性,她是一位失疼的病人。失疼,就是对身体失去痛感,一个失去痛感的人,他的周围的世界同样是危险的,或者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危险当中。排斥真实的疼。却不知道,人的肉体意识正是由疼痛唤醒的。
世界著名的医学家保罗·布兰德教授毕生在对人类的疼痛进行研究。他说:“我并不希望,甚至不敢想象无痛的生活……如果我手中握有权力,能使肉体的疼痛从世界上消失,我也不会运用这种权力。”
因为身体失去痛感,而成为可怕的疾病。她用剪子截伤手腕,用滚烫的开水浇在自己的皮肤上,看一大块滋滋冒着白烟的皮怎样在手指尖上粘连,弯曲……但是,无论怎样发泄,她都无法唤醒身体最深处的一点点痛感。
“她没病。她装的。装病。”说话的人嘴角露出讥诮的口吻,她是个患狂躁抑郁双重精神疾病的女患者,她指着靠近墙角平躺着的一位女病人对我说。
这位女患者始终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她的脚、身体以及双手被白色的,略显脏污的纱布重重裹缠、捆绑。略显脏旧的床单边沿上粘有块状的红色暗血。还有地面上同样凝结的血斑,凝干的血渍颜色混浊,特别脏而触目。
她裸露的手臂上面留有新鲜的血道。这些抓痕是她对自己施展过暴力的见证。她刚被医生施用过镇静剂。现在,她平躺着,紧闭双眼,脸上有一种经过挣扎后隐忍的表情。
“她为什么用手伤自己?”
“她不怕疼吗?”
“除非她对自己充满了懊丧和绝望。”
疼痛一词在本质上说常常和“消耗”、“吞噬”有关,就根据疼痛的程度而论,是微微疼痛,还是轻度疼痛,是强烈疼痛,还是尖锐刺痛?肉体多么脆薄,对它的拉扯、切割和破坏都会产生疼痛和肿大、挤压、变形,所产生的疼痛是一样的。疼痛是对世界的一种否定。“噢,我疼痛的应该有人慰藉,疼痛和抚慰应该并存。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而不会有疼痛之感。”
我母亲自小生活在湘西一个地处相对偏远的农村。缺乏健全的医疗手段。当有人被山坡滚下来的石头砸伤,镰刀割破手,或者突发疾患……让人宿命地忍受疼痛,而成为一种不得不顺从的力量时,有乡村医生尝试着发现一些土方法来控制,缩短或减少病人的痛苦。他们在对付疼痛的这些疗法中,“以痛制痛”是常用的一种。
同样是一种疼痛,但有些人相信,疼痛有时会自己搭救自己,用另一种疼痛来刺激身体的某一部位,使得人为制造的疼痛比原有的疼痛更加剧烈。以此来缓解后者,仿佛疼会消失在疼痛中。或至……或至少提供一种有益的注意力分散,祛走病症。
妈妈说,当地人是用一种艾草。用艾草进行治疗的方法是这样的。把一些植物扎起来成一小棒或一小束,然后放置在离患者处尽可能近的皮肤上,点燃这束艾草,直到患者感觉到烧灼的疼。因为当地人相信,只有当两种疼痛同时存在时,比较强烈的一种疼会遮掩住另一种相对较轻的一种疼。也就是说,前者使后者消失了。这种“滑稽”的有关“转移”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是对幽默的亵渎。
当艾草在皮肤患处灼烧时,皮肤上会有灼热感,很不舒服,很强烈。它燃烧得很缓慢,释放出能量,带来更加剧烈的疼,那种疼痛的感觉是关节扎了一根钉子,比钉子更强有力的钳子的钳来把肉撕下来,被恶狗咬住,而锋利的狗在牙啃他们的骨头……疼痛的人用最恐怖的比喻来说明自己所忍受的地狱般的折磨。
她想挣扎逃脱,可是被一双强有力的手臂按住了,她扭曲着脸,眼泪掉了下来,看起来像个行刑者。
疼痛,是整个人类的遁词。现在,是我的遁词。
这个词是有味道的。但是说不出来,不如把头深深地埋下去。然后,在疼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年轻的时候,我的身体易于和自我达成和谐。现在不了。我经常和我的身体闹别扭,对它有着隐隐的苦恼……和不信任。在这种与自己身体的紧张关系中,有时对它是切肤的爱,而有时是萌生恨意。还有困惑。我的身体,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拜斯说:“一切肉体穿上盐的苦衣。”
而我修改了的话。
我说:“我的肉体穿上盐的苦衣。”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