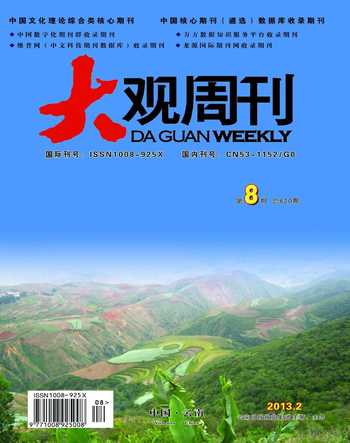对自然资源用益物权问题的一些思考
严驰恒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并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及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制度。制度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法律角度的研究恰恰能为其提供理性层面的建议。
依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我国对于矿产资源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正是由于在我国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以《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将采矿权视为一种用益物权,而立法之所以如此定位,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土地和矿藏等自然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利用,保障权利人履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义务。
正是基于上述对于采矿权乃国家所有、用益物权的定位,我国才相应地实行了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制度,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和第十條的规定,在我国依法取得采矿权,一般而言须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当然后续还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等。
众所周知,矿产资源的两大特征乃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也就是说国家出让的供特定人开采的矿产资源在经过开采后就不复存在了,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都是一次性的。但根据物权法的精神,用益物权是一种限制物权,即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标的物进行支配,权利人并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而且用益物权是一种有期限物权,有一定的存续期限。并且笔者认为,所谓用益物权,标的物必须具有能反复使用的特性,否则立法就没有设定用益物权的必要了,因为在使用后连所有权客体都消失了,还谈何所有权、用益物权!这样看来,采矿权就很难称其为用益物权了,首先,在采矿权行使中,用益物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不得破坏准许开采范围以外的矿藏及维护生态环境上,而对于所准许开采的矿产资源,似乎是没有限制的,采矿权人事实上取得了近乎所有权人的地位,可以任意处置;其次,采矿权的存续期限也无从谈起,采矿权作为一种权利,其客体应是所开采的矿产品,但矿产品一经开采使用便不复存在,所谓的存续期限实际上只是国家许可权利人开采的期限,这与用益物权作为有期限物权的含义截然不同;再次,经过开发后的矿区就没有了再次开发的价值,当初用益物权的客体已经消失,即使可以再次使用,其价值也是大大降低的,那么又如何再次设定客体相同的用益物权呢?
综上所述,国家在采矿权出让的过程中出让的并非物权法层面上的用益物权,而更接近于所有权。而将采矿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并以用益物权的标准去衡量、评估采矿权的价值,显然是大大降低了采矿权及其背后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似乎也正是造成当前社会对于“煤老板”等采矿权拥有者争议的众多原因之一。
通过物权法的立法规制和建立自然资源的用益物权制度来加强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初衷固然是好的,但如何才能真正使制度、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还需要有更务实的审视。就采矿权而言,首先,无论从理论角度抑或实务角度而言,采矿权的出让都应定位为一种“准所有权”的出让而非用益物权的出让,即使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无法以所有权之名进行出让,也不应将其简单得视为用益物权而贬低其价值,对其法律性质、客观价值都应有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一方面是基于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其次,对于采矿权的价值应有更客观、合理的评估,既要包括所出让的矿产资源的合理价值(综合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和矿产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矿区土地、草原、林木、水源等的使用费,还要考虑国家在前期勘探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最后,对于采矿行为给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国家可以收取一定的环境治理、恢复费用,作为环境保护的基金。
我国在采矿权领域出现的问题在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出让上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生态文明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法律角度而言,通过立法建立切实反映自然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稀缺性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利用税收等手段补偿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对于环境的破坏,加强对于滥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执法、处罚力度,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等价有偿”和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才能切实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也才能真正促进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