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一生都在解惑
张菲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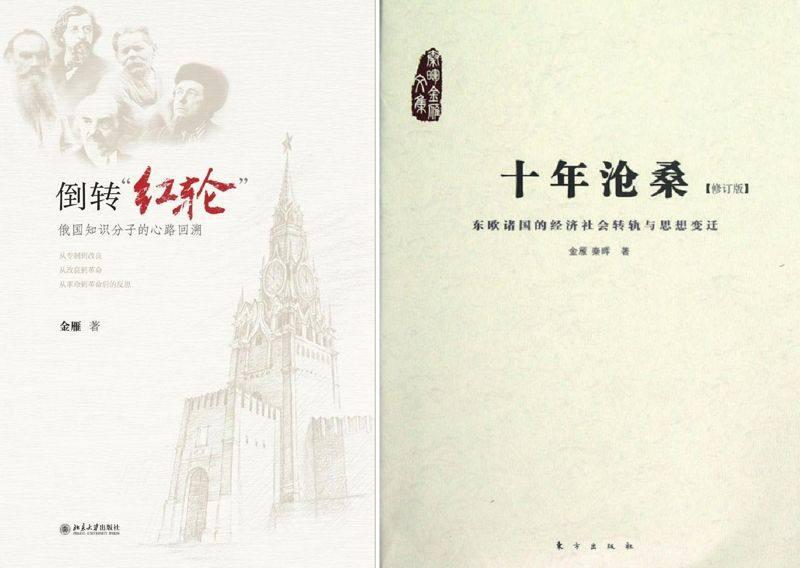

作为一个资深的东欧学者,金雁有很多关于东欧解不开的谜团。为什么高尔基在不同历史时期观点都不同?红色专制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社会主义都是从理想主义者开始,最后都会走向专制、强制?……
这种“不解之问”,金雁有很多,“照此罗列下去,恐怕几张纸都写不下。”
有人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话回答说:“俄罗斯是矛盾的、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但在金雁看来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无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搞不清楚自己心里的坎就过不去。”于是“解惑”成为金雁一生做学问的动力。
注定的东欧学者
在众多学者眼中,金雁似乎是一个注定的东欧学者。
和许多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学者一样,痴迷俄罗斯作品几乎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但金雁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却更加深刻。
那是“文革”前夕,金雁的父亲因为在《九评》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甘肃农村劳改,作为“黑五类”子女,金雁没能读成高中。“初中那三年也都在搞‘文革,我其实只能算是小学文化水平”。但对于知识的渴望,金雁是迫切的。
父亲对她说,虽然家里的很多书都烧了,但还剩两套书,一个是《马恩全集》,一个是《列宁全集》,你若能把这两套书读完了,哪个大学都毕业了。
就在插队期间,金雁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了《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70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
一次读书疑惑,金雁徒步40里去找爸爸,父女俩在麦草堆旁讨论“拿破仑战争”“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
“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金雁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更激发了金雁对晦暗的沙俄时期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
俄罗斯作品是金雁人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因素。“那个年代,如果没有俄罗斯作品的相伴,我的人生该是孤寂和寂寞的。”
所有这些看似无心杂乱的积累后来都成为金雁1978年考苏联史研究生的知识背景。1978年金雁重新再回兰州大学读书,能够在课堂上与导师和师兄们一起讨论心仪已久的俄罗斯问题,是金雁那些年最开心的事情。
由于从外语专业转到历史专业,基础比较薄弱,对于师兄们见怪不怪的问题,金雁总要问“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苏俄教科书过于程式化、千篇一律,金雁很难在其中找到答案。
在学校里,金雁一直是个“问题学生”,总是纠结于一大堆问题中找不到答案。因为工作关系,金雁的研究先后“分叉”到东欧现状、苏共历史问题当中。
1982年金雁被分配到陕西师大苏联历史研究室,金雁就对杨存堂老师说:“你们大家做‘桌面搞苏联史研究,我当‘桌子腿继续我的俄国中古和近代史研究。”当然这一愿望没有得到支持,金雁只好“转战”到现代史领域。
但金雁一直不忘“当桌子腿”的话。一晃30多年过去了,2012年《倒转红轮》一书出版,金雁说:“总算可以还一还历史‘旧账了。”
“趁我还在,要赶紧整理出来”
破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斯芬克斯之谜”一直是金雁长久以来的愿望。
在一个问题没弄明白之前,金雁充满了干劲,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翻资料查原文,坐在一大堆书籍里满头满脸都是灰地寻求答案,但是往往一个问题套着另一个问题,问题越追越多,但思考仍在继续,问题的“辐射”面也在不断扩大。“总感觉结论不够完善,资料不够丰富”。
也因此,金雁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她的办公桌前留下一堆凌乱的手稿,电脑里留下大量的资料卡片、乱发的议论感想和起头写了半截的文章。
有人说金雁与写作有着“神圣的关系”,轻易不肯动笔。但在2011年,与金雁同龄的历史学家高华的去世,这让金雁对于写作有了不同的看法。
“高华的去世给我一个感受,我们50后的学术生命也不像想象的那样长,所以有话还是早点说。”2011年、2012年金雁连续出了两本书,都得到学术界与社会的高度认可。
在丈夫秦晖看来,金雁早该如此做了。
这对学术界夫妻时常一起做学问,秦晖经常能听到金雁在隔壁房间里一惊一乍地大声叫喊“原来如此!”
“一个人做学问未免太自私。”但秦晖催促金雁把形成的东西赶紧整理出来的原因还源于两个人的约定。
“我和金雁约定,谁走在前面,走在后面的那个人有义务为逝者完成大量的半成品和文稿整理。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先走的人是幸福的。试想一下守着电脑里数不清的不是自己本专业的东西,整理的难度该有多大。”
学者在每一个时间段都有自己的认识水平,从来没有一个人要彻底想通了才能动笔,因为思想的认识过程是无穷尽的。
《倒转红轮》刚出版没多久,金雁已经将下一本提上日程,第二本名字暂定为《历史的化装舞会——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变迁》,第三本是讲民粹派的《从人民之子到人民之父》。
这些书籍都是金雁这么多年为自己“解惑”的成果。“我不会再铺新摊子,把这几本写完了,我就退休写好玩的故事。”
在秦晖看来,“金雁写的故事远没有讲的故事生动有趣”。
还原真实的东欧
无论是《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还是《倒转红轮》,金雁总是打破国人对东欧的惯有认知。
在《十年沧桑》中,金雁说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里很好,不用中国同志担心。”在《倒转红轮》中,金雁更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百年历史进行了反省并颠覆了他们在国人心中神圣的形象。
“中国人对俄国知识界的了解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一厢情愿,有人把它浪漫化,有人把它理想化,都是自己在这里臆想。”
所以在金雁从开始写第一本书起就说:“希望把它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要经得起历史拷问。”
金雁的观点具说服力源于她亲身经历并体验了苏东剧变和经济转轨过程。
1991年金雁被派往波兰做访问学者,刚上火车,金雁就开始写信,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火车每停一站,金雁就要下车去找邮局,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看寄给秦晖。
那时候秦晖已经成为金雁的丈夫,两人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双双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秦晖主要研究中国问题,但对苏联、东欧历史转型的关注和研究总是在为中国未来的转型出路提供一面镜鉴,于是夫妻两人在学术上开始了全方位的配合。
信件有时候从波兰、俄罗斯进行国际邮件进行投递,有时候通过熟人带回国内进行投递,这造就了秦晖都不是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收到信件。有次秦晖写信给金雁抱怨说:“每天都要开信箱去摸信,一连好几天没有摸到信了,我的手都被铁皮信箱边缘磨破了,但是还没有摸到信。”
后来金雁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时开玩笑地说:“他当然不是对老婆消息的渴望,而是对东欧信息的渴望。”这对伉俪还以“卞悟”为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探讨中国问题。
在那个普遍学习政治的年代,秦晖口中的东欧消息成为很多陕西师大老师参加政治学习的动力。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金雁正好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红场上,飘扬了69年的镰刀锤子红旗缓缓下降,周围有人流泪有人欢呼,金雁更多的是感到心情复杂。
这个在瞿秋白心中的“革命圣地”充满了理性精神,有灿若星河的智者,那些知识分子为何不及时呐喊?俄国知识分子在忏悔,为何中国知识分子没有?……
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金雁,于是她继续研究着东欧,给自己“解惑”的同时,亦为我们奉上精神的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