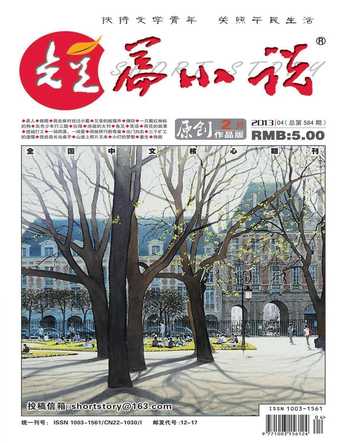论《名利场》中的不和谐与社会价值观
小说《名利场》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成名代表作之一。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初的英国上流社会。作者萨克雷这样说:这部小说没有男主人公,只有两位女主人公,但是她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有着不同的命运。小说《名利场》不单纯是一部小说,它也是一部对社会现状进行描述的缩影。小说中所描述的名利场是一个浮华的世界,到处都充满尘埃,将人们的眼睛蒙蔽,同时也蒙蔽了人们的心灵。在名利场之中,人们各自疯狂地寻找着自己所谓的漂亮位置,进而来炫耀自己。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看不清场外的人,他们所注重的仅有金钱和地位。
一、《名利场》中的不和谐
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没有必然性的丑陋现象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空洞的、被扭曲的,是一种荒谬的特征。这种内容和形式的不和谐造成现象和本质的不相符,使得和谐产生了扭曲,因此就产生了美学当中的不和谐。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到处充斥着这种内容和形式不和谐的现象,如一些腐朽的事物和没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披着美丽的外衣,进而以有价值的形式来呈现,将其本质掩饰在这一假象之下。因此,这种本质和外表的强烈不统一形成鲜明的对立状态,这也正是作者萨克雷所要对其进行嘲笑的本质。萨克雷通过对现实当中的这种荒谬的、表里不一的现象进行分析,重点突出其中的不和谐,进而来揭露事物的真正本质并将其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萨克雷的作品中,这种不和谐主要通过对一些具体形象的渲染来体现。作者将这些本质空虚的人物赋予非常完美、尊贵的外表(如利用华丽的辞藻来形容他们面貌特征等),为大家营造一种虚假的外表和美丽。然后,作者开始對人物进行一些具体行动的描写,进而在动的过程中将他们的丑的本质揭露出来。这样的暴露使得人物的外表和内心存在严重的不和谐,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读者会不由得对这种人物的前后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透视。于是,刚开始的美的假象在加入真假、善恶观念的同时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新的判定标准。在这种对审美感不断淡化、对理性认识逐渐增强的过程当中,读者心中产生更多的憎恨,他们和作者同时对这些丑陋的东西进行裁判,这种讽刺的笑和恨的完美结合使文章的表现力度更加辛辣和无情。在揭露这种不和谐时,作者还采用让人物自我暴露的方法来进行,即同一个人物的行为经常前后不一、不能自圆其说,使他们自身的矛盾顿然产生,与他们冠冕堂皇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这种表现方式正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是丑陋的一种自我毁灭。
在小说《名利场》中,克劳莱小姐一直对利蓓加说一个人的家世并不能说明什么,她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可是这“平等”二字还没有全部落下的时候,这位老小姐便开始指使利蓓加来为她干活,让她给火加煤,给自己改衣服。这种同一时间和场合所表现出的人物语言的反差,其内心的想法不言而喻。还有,这位表面主张平等的阔小姐,一面夸奖利蓓加应该做到公爵夫人,一面在听说侄子罗登娶了利蓓加之后便非常生气,竟然放弃让罗登继承财产的决定。这样的人物自我标榜和实际行动之间所形成的差异,表明人物的形象外表和内心是存在明显对立和不和谐的。克劳莱小姐的这种外尊与内心的自卑通过自我披露使得她立刻从崇高下跌到渺小地位,以前读者心中对她的尊敬之情立刻消失,对其前后言行的不一致一笑了之的同时也更清楚地看到她的真正本质。在这里,作者首先通过人物的自我吹嘘来将其拔高,然后再通过后面的一些行为来对其进行揭露,形成一种虚伪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人物在刚开始的时候将自己吹捧得越崇高,她们反过来却越卑微,这是一种严重的客观与本质的对立,一旦这种华丽的外装被剥去之后,所有的一切都露出其荒唐滑稽的一面,给人一种出奇的意外,激发出人们的轻松感和对人物的蔑视感。在揭露这种丑的本质时,萨克雷有时候还会通过甲人物的口来对乙人物进行攻击。小说中,斯丹恩勋爵有一次不期而至,毫无准备的利蓓加便匆忙上楼照完镜子之后才去迎接这位大人物。她的动作虽然麻利,但还是耽误了几分钟,便急忙向勋爵解释,说自己出来晚的原因是因为在准备布丁。而勋爵却当面反驳说,你明明是在楼上的房间涂抹胭脂。随即,利蓓加反问勋爵自己打扮好看点不好吗。作者借用勋爵斯丹恩的口来解释利蓓加的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同时也通过这一情景向读者展现这两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小说中的不和谐不仅通过人物的自我暴露和互相揭露来展现,同时也通过作者的主观评论来进行评判。萨克雷经常自己出面,反唇相讥,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加入自己的主观议论。通常在故事叙述到一半的时候,作者暂停描述,添加一些富有讽刺意味的话语,或者对人物的话语进行反驳,或者去对他们的用心进行指责,这样的一番感慨直达读者内心,就像自己亲自上去将人物的假面具掀开一样。在早期的英国小说史上,这样的夹叙夹议方式已经在18世纪得到大量使用,萨克雷是对其进行进一步发扬。在小说《潘登尼斯》的序言中,萨克雷指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具有“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版”的特性,是萨克雷进行人物塑造的典型手法,进而缩短了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二、阐释的社会价值观
小说《名利场》的创作风格完全摒弃了原有的创作模式,以一种真实的手段对人物形象进行鲜活的刻画,使得每一个人物都富有生命。现实当中的人们并不能十分准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二者是相互融合的,并不是完全绝对的。这样的好坏都是在相互对比的情况下产生的。就像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她们并不是那种大恶或者大善之人,如利蓓加小时候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姑娘,内心是非常善良的。但是从小所经历的贫穷和苦难使得她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进入上流社会,进而改变自己小时候的困境。这样的手段在常人看来虽然是很不光彩的,但是对于这位一心想飞上枝头当天鹅的丑小鸭来说却是万般无奈的。相反,利蓓加的同窗好友却有着非常好的出身,从小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并没有对金钱的强烈欲望。在她的温柔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非常懦弱的心灵,她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追求的勇气,只是一味由自己的父母来进行安排。作者对这两位女性的描写其实就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描述,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得她们在追求自身幸福的道路上充满坎坷。只有真正能了解幸福内涵的时候,她们才能获得自己的所需。在当时那种物欲横流的华丽世界,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很多年轻的女子都受到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其价值观发生重大扭曲,更多的去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然而,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只能靠金钱来衡量的,物质的追求永无止境,唯有精神世界丰富了,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些名和利的追求并不是人们的最终追求目标。
《名利场》是通过对两个女子的不同命运描述来构造生动情节的。爱米丽亚是一位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小姐,她既单纯又自私。在这种浮华世界的名利场中,她只关注于对自己爱情小窝的建造。她缺乏自知之明,却对乔治·奥斯本非常钟情,而他却只是一位见异思迁的花花公子。对于爱米丽亚,他从没有重视过,对于爱米丽亚对他的一片痴情,他毫不动情。虽然他们后来结婚了,但是一个星期之后,这位花花公子便另有所爱。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利蓓加的命运则是通过她的身世来展开的。利蓓加是一个穷画家的女儿,为了追求上流社会的奢华不顾一切,用尽各种手段,最后身败名裂。凭借自己的姿色,利蓓加从一无所有而摇身变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分子。她将所有的心计都用在寻找有钱的丈夫上。不同于爱米丽亚的是,利蓓加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她爬上上层社会的阶梯,她必须利用好。刚开始,她勾引爱米丽亚的哥哥乔瑟夫,一位富有的税收官,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富有。后来她又和青年军官且有可能继承巨额财产的贵族子弟罗登结婚。在结婚不久,罗登的母亲便去世了,她公公毕脱男爵便向她求婚,此时的利蓓加非常后悔,当爵士夫人的梦想离她既近又远。后来,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她竟然攀上了更大的人物——斯丹恩勋爵。依靠这位勋爵,利蓓加便自然而然地踏入上流社会,并非常有幸地觐见了国王。在她非常得意忘形的时候,丈夫罗登发现了她的这种暧昧关系,对她大发雷霆。丑闻立刻被公开,公爵立即遗弃了利蓓加,她在上流社会的梦想逐渐走向下坡路,然而她仍然本性难改,仍然在这一名利场中到处招摇撞骗,试图再次登上上流社会。
在小说的结尾,利蓓加对乔瑟夫进行再次欺骗,赢得他的欢心之后,利蓓加便对这位愚蠢的税收官进行财产压榨,使得他最后患病而去。世事是无常的,萨克雷发出无数次这样的感慨,但是所有的无奈和叹息都不能说明什么,名利场对人们的诱惑使得她们不顾一切,竟然会去伤害自己的亲人和好友,最终使自己陷入深渊。人生轮回,在中年的时候,这两位女主角的命运再次翻转,爱米丽亚的善良最终使她再次回到了温暖的富裕家庭,而利蓓加的聪明却让她也回到生活的起点——贫穷的生活。作者对这两位女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所有的追求到最后终究还是一场空,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在这种名利场中,所有的繁华都将被洗尽,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淘汰,但是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野心家不放弃,跃跃欲试,想去分得其中的一勺羹,似乎这样的生活才应该是她们所追求的。作者参透了名利场中的这些奥秘,以一种超越世人的眼光来将其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向读者展现这些既可悲又可叹的人物。
三、结 语
通过本文对小说《名利场》中的不和谐与社会价值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束缚,对她们追求自由、独立形成一种很大的阻碍。这种社会使得女人很难得到真正的解放。萨克雷通过对她们的描述来向读者展现这种社会的不和谐和被扭曲的价值观,是当时社会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杨必,译.名利场·译本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李颖.爱米丽亚与利蓓加形象比較[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6(01).
[3] 陆伟芳.对19 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理论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03(51).
[作者简介]
孙云军(1971— ),男,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