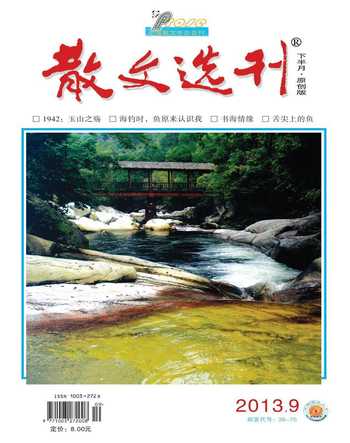丰盛的午餐
洪建生
小时候,我们跟着父亲,租住在生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
父亲苦出身,喜爱和熟悉农活,很快就和农民朋友打成一片,不久便被“三结合”,重新回到公社上班。也就在这一年,我随父亲到公社所在地的一所学校读小学三年级。那时我们全家六口人,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有些窘迫。但生产队给了一块菜地,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生产出一些菜蔬和五谷杂粮,补贴家用,填补了一些空缺。这样,我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到菜地干活。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随父亲。随父亲时,总要做得很晚,直到暮色四起时,才被母亲一遍遍地喊着吃晚饭。
父亲工作的公社,坐落在解放前一大户人家的祠堂里。祠堂里面深邃幽静,高比现在的三四层楼房,白墙黑瓦,从前至后有三进,穿过两道天井。祠堂有许多根两人才能合抱的圆形木柱、四方石柱,它们都耸立在鼓一般形状的石墩上,柱和柱之间是规格不一的冬瓜梁连接,形成了现在已经难以见到的房屋结构。里面的墙体都是用上好的木板隔断,木板下端和地面四周是长条和整齐划一的青石板排列和铺就。地面的材料,据老年人说是用糯米熬成的汁与石灰砂石搅拌而成的,坚实而又平滑,呈浅灰色,上面还分布着浅浅的网状线条。房间分立两旁,临天井的方向一律开了窗户采光。夏天里,常常见有五彩的蝴蝶和蜻蜓从大大的门庭里款款地飞进来,然后又从高高的天井悄无声息地舞出去。
记忆中,公社的干部人数很少,能数得过来也只是十个人出头一点。农忙的季节,干部们推了自行车,戴了草帽,走村串户包生产队去了。父亲虽然是秘书,也是要经常到生产队去的。所以我和父亲一起吃午饭的次数是很少的。白天里公社静悄悄的。中午放了学,我到父亲房间里,拉开抽屉,数出饭菜票,到食堂买四两饭,一份菜,青菜或者豆腐,偶尔也能买几块红烧肉,是很好的了。比在家里的伙食要好一些,而且不用与兄妹们分享。父亲因为工作的需要,占了两间房,一间是卧室,一间做办公用。卧室很小,里面差不多被床、桌子、凳子、箱子、洗脸盆架子塞满了,外面办公间却是空旷得很,靠天井雕花的木窗下,摆了三张三屉桌,两张相对一张横头,聚在了一起。父亲的办公桌上多出一块玻璃台板,上面压了介绍信证明之类,颜色已经泛黄了。有一面墙,靠墙立着两张多抽屉木橱子。木橱的一端有一根木条上了锁,开其中的任何一个抽屉,都要先开了压在上面的木条。开木条上面锁的钥匙是父亲长年挂在裤腰带上。有一回,父亲把钥匙放在了桌面了,我因为好奇,顺手抓在手里玩。父亲看见了,从我手里拿过钥匙,对我说,公家的东西不要乱动。但我感兴趣的是立在我父亲办公桌座椅的背后的一只木架,那上面架着的,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三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
我把饭菜端到父亲办公的桌上,并不急着吃。而是先从报架上然取下一份报纸,通常是三份报纸都要翻一下的,但主要是《人民日报》。这好像是吃饭之前先要进行的一道仪式。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报纸的内容有些空泛,曲高和寡,版面设计难以出新,但让我在中午的时间里,了解到比我的同学多很多的国内外大事。由于中午有充裕的时间,一个人又独占一间办公室,中间并无人来打扰,便一边咀嚼,一边细细地读可口的文章,以至于炊事员阿姨总是跑到窗子底下,催要碗筷拿到厨房去洗。每天读报,我注意看的是周总理同外国宾客的合影照。周总理居中,将右手端于右侧胸腹之间,脸庞清瘦、表情凝重。后来知道,这是周总理最困难的时期,所以到现在想起来,也是久久地挥之不去。此外就是散文、诗歌、雜文,我差不多是每篇都要读一下的。我在这一时段里,对《人民日报》的钟情,成全和培养了我对阅读的爱好。以至于有一次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对全校考试情况进行点评时,举了几个学习用功的同学为例子,号召全校同学学习,我也在其中。对我的介绍,则注重说我在吃饭时间不忘记读报,意思是我的学习精神可嘉。但我要心存感激的是,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使我的每顿午餐都变得丰盛起来,而别的同学,是没有这样待遇的。
此后参加工作,我的办公桌上一度也常年摆放着《人民日报》。只是由于工作忙碌,不能像在父亲的办公室时从容地读看《人民日报》。但是只要有空,或者出差,或者去参加一个会议,我都会把随身携带的《人民日报》悄悄打开,悄悄地阅读。
因为它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份报纸,就好比是初恋。
责任编辑: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