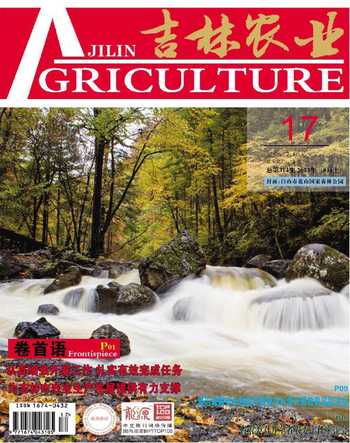摇曳的水蓼花
路来森
我的记忆中,水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青蓼,一种是红蓼。
青蓼,其茎、叶均为浅绿色,开白色小花,穗状,花朵一簇簇缀着。花盛季节,花开如荼,映水而放,远远望去,如星河密布,玄远而飘逸,发幽思之想。若是一单棵青蓼立于水旁,则有一种轻盈、俊逸之态,极易让人想到那正临水照面的清雅、娟秀的女子。青蓼,来得轻,来得淡,来得孤微,很少有大片的青蓼存在。
水蓼中,更多的是红蓼。红蓼,微红的茎,微红的叶,深红的花,红得肥硕而刺目。经常是大片大片地存在着,花盛季节,花开似火。很早,就“燃烧”了我的记忆。
记得小的时候,家门前不远处就是一汪水湾,经年不涸,水草丰茂。每年的春天里,水岸边最早生发出的就是薄荷和水蓼。薄荷嫩碧,水蓼浅红,相映而情趣丰满。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就挎上一个竹筐,来到水边,采摘薄荷和水蓼的嫩的茎叶,采满一筐,挎回家中。用清水将采摘的茎叶洗干净,放入一泥盆之中,再拿大粒的粗盐,反复揉搓,揉至茎叶滋出水渍,盐分进入茎叶之中。然后,以另一泥盆将其盖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即可开盆食用,这就是所谓的“薄荷菜”。薄荷清爽,水蓼辛辣,两种滋味融在一起,食于口中,滋味特别。那些年里,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整个春天,我们都是用“薄荷菜”佐餐,生活倒也有滋有味。
那些年里,我出门就能望见对面的水湾,望见水湾边勃勃生长着的水蓼。朝朝夕夕,红绿盈目。望见它,雨季到来,被水漫漫淹没。立秋之后,水位下降,它又复立于水泽,挺挺然,一副昂然不屈的样子。它变得更红,红得明亮,红得通透,红得沸沸扬扬,全不顾季节的肃杀。每一根枝头,都岔出一串串的花穗,将桠枝压得沉向大地,像是虔诚地俯首。红红的色彩,映于水面,使萧索的秋凉,增添了一份热烈。可是,随着季节的深入,季秋时分,水蓼的花就开尽了,花穗上结满了花籽,只有顶端,还有几粒花惨然地开着,看上去孤独而又落寞。
这个时候,我的祖母知道,水蓼已经成熟了。她会走向水边,选择几棵肥大的水蓼,将其连根拔出。然后,用细绳捆好,倒着挂在庭院南墙的背阴处。看着它慢慢阴干下来,好像要故意锁住一种孤独和寂寞。那时候,我曾经问过祖母:“留着这些干水蓼做什么用?”她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着,可以治蛇伤呢。”我的祖母,似乎忘记了,在北方,秋季之后,蛇很快就要“冬眠”了,怎会出现蛇伤?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水蓼从来也没有用来治过蛇伤,倒是有几次,我的父亲做鱼汤,掐几段放入锅中,说是能去鱼腥。不过,后来我读书,知道水蓼确是能治蛇伤的,至少是有这样的记载。如《唐本草》:“水蓼主蛇毒,捣敷之,纹汁服,止蛇毒入内心闷。”
若干年后,我的记忆里,还晃动着祖母挂在南墙下的那些水蓼。干枯了,凝固了,但季秋里,水蓼的落寞、怅惘,却永远被贮存。
秋季里,水蓼的那种情状,永远成为了我内心一种残败、荒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