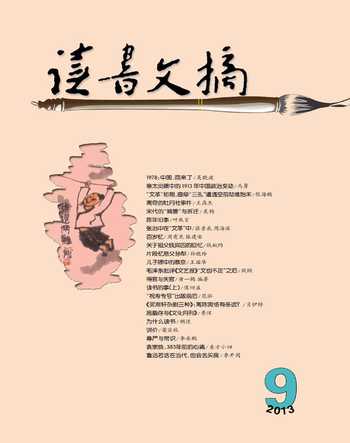读书的事(上)
陈四益


北京胡同里的“小宅门”(中等人家,与大宅门相应,戏称之为小宅门)也多为两扇对开。门上多写有门联,见得多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可见那时门第、传承,同“诗书”大有关系。
“革命”了,就不同了。尽管最初宣传与策划革命的都是知识阶级,但真要“暴动”,冲在前面的倒多是斗大字不识一担的“革命先锋”——亦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读过几天书,对“革命”策划者的理论、方针、计划、措施评头论足,用起来不那么顺手,这在策划者看来就成了“革命”的“障碍”。
所以,革命的策划者大多贬抑知识阶层而抬高无知识阶层。即如《水浒》中的宋公明,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持两柄板斧、不惜性命、唯哥哥之命是从的“铁牛”。于是,策划者便有了“书读得越多越蠢”、“马列主义读多了也会出修正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类高论流传。如果一定要读书,那就只读策划者的书。别的书呢?若与策划者的理论不合榫,大概就属于读得越多越蠢之列了。
不过,在“史无前例”之前,还没有走到极端,不听话的知识人是在不断整肃了,但各种书籍,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古今中外,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多还是可以借阅的。有些书对学生不出借,但教师是出借的;有些书对一般人不出借,但对一定级别干部是出借的。所以然者何?说不清,就那样规定,毫不通融。
譬如,《金瓶梅》,在“我大清”时就列为禁书。民国时,虽不说禁,但仍躲躲闪闪。郑振铎编《世界文库》,收入《金瓶梅词话》,文中每夹有若干行“框框”,一字一框,以示此处共删多少字。到了“新中国”,据闻,反倒是“伟大领袖”说:“《金瓶梅》不可不读”,并在高层会议上向党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推荐。大概因为毛泽东有了“不可不读”的纶音,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印了现装足本《金瓶梅》若干部,规定部级以上干部可以购买一部,也就是仅限于“高层”,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据说经审批也是可以买的,但印数有限,供不应求。此事颇为费解,是因为部级以上干部不怕腐蚀,还是部级以上有此需要?说不清。反正《金瓶梅》虽然有限度地开放,但那是高层,我们这些“低层”,尽管读的文学专业,要想借阅,根本没门儿。
到了60年代初,因为中苏论战,印了一些包括赫鲁晓夫、铁托、卡德尔、热德拉斯等“修正主义”的言论与著作;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又印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再加《第四十一》、《士兵颂歌》、《雁南飞》等一批电影;此外,还有表现所谓“垮掉的一代”的英美小说《向上爬》、《在路上》、《麦田守望者》,70年代又放映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等。电影也都是“内部放映”。不够“内部”的,仍无缘一睹。
到了1966年,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要和旧世界作“最彻底的决裂”,不但摧毁着学校,摧毁着教师,也摧毁着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和文化。不要说那些“内部发行”的“反动书籍”,就是原先公开发行的作品,也几乎一揽子定为“封资修”,锁在书库不准借阅,图书馆也就关起门来闹“革命”了。当然,“革命”的策划者们还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我的一位老师那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伟大领袖”要看什么书,都由他负责配齐。后来听他说到那些书名,大抵都是市面上要“砸烂”、被抄没的货色,而京城一些学者的私家收藏,据后来披露,被抄后,许多也落入了指导“大革命”的“小组”顾问或成员私囊。不属高层也无缘“内部”的人,“合法”的阅读物,只剩下“红宝书”外加“马列”和一个鲁迅一本《红楼梦》了。若不识时务,难免尴尬。
在去苏州的火车上我曾遭遇一次尴尬。因为有一两个小时车程,随手带了本《呼啸山庄》在路上解闷儿。艾米莉·勃朗特的这部小说是公认的“世界名著”。不想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直向我走来,问我在看什么书。那时,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在巡视着不符合“红彤彤新世界”规范的行为。我不发一言把书交给他,听候处置。这位小战士大约从未接触过这类书籍,拿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如何是好。从封面上看,画着一个穿带裙撑裙子的外国女人,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但看内容简介,却又分明写着,反映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话语,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当时,反映阶级斗争的书当然不好归于“四旧”。于是,“当兵的”只好“劝诫”道:“虽然这书反映了阶级斗争,可是不知道的人看到了这些画,还以为你这人觉悟太低呢,收起来吧。”看来这位是温和派,没有横加没收,还讲点道理。在“工农兵”领导一切的年代,我当然不好争论,只能听命。
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我又听说了另一次“尴尬”。上海工宣队进驻大学之后第一个“革命行动”,便是全校性抄检“黑材料”。因为是在“红革会”(好像全称是“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炮打张春桥”之后,所以大学成了抄检“黑材料”的重点,那办法有类于《红楼梦》里的抄检大观园。那天抄到我一位同班学友的宿舍。那位学友忠厚诚笃,因为当着学生指导员,所以住在学生宿舍,书架上大多是“马列”,只有一本《裴多菲诗选》引起了工宣队员的怀疑。因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里有“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最高指示”,所以一见裴多菲三个字便神经紧张,拿着那本书左看右看,不肯放下。直到一个学生看不过去,说:“老师傅,这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选,同那个裴多菲俱乐部前后差了100多年,没关系。”那个工宣队员这才如释重负,把书丢过一边。裴多菲因此逃过一劫。
这两件小小的趣事,可见当时禁书之严。这样大规模的禁书,恐怕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所没有的了。
名为文化革命,却先把文化毁灭,那办法也同为政治大革命,先把所有干部都打倒一样。据说“文革”期间,张治中老先生在天安门上对毛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毛回答:“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不知那些当做“封资修”一揽子查禁的书籍,是否也要等到“革命”后期一一甄别,但至少在当时,给我的感觉,同旧世界彻底决裂,就是要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统统铲除。这样的想法,令人不寒而栗,甚至怀疑是否还生活在一个能够正常思维的世界。
(选自《世纪》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