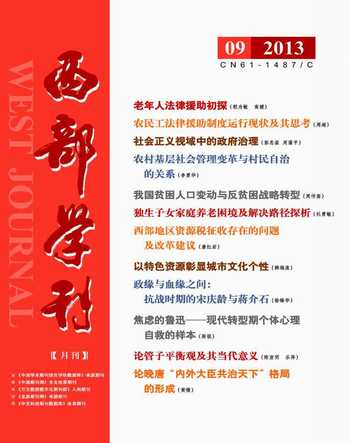冷静现实 锐意求治
摘要:陆贽是唐代著名政治家,他长期从事政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思想。他重视人事,主张积极求治,厉行中央集权,选用贤才,加强君臣合作,形成团结高效的统治集团。其目的在于矫治政府工作中的弊病,提高政府效能,刷新政治,重振唐朝国威。
关键词:陆贽;行政管理;行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2
中国有着漫长而辉煌的文明史,发达而高明的行政管理正是中国文明的标志和基础之一。与之相伴随的是形成了丰富而深厚的行政管理思想。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所讨论的陆贽就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陆贽是唐代著名政治家,他富于政治才干,功绩卓著,对政府行政工作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但长期以来并不为人重视。笔者认为他的行政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此对其行政管理思想进行简要的总结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为唐代著名政治家。唐大历六年(771),十八岁的陆贽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后被选授渭南县主簿,又调任监察御史。德宗即位后,任命陆贽为翰林学士。建中四年(783)朱泚作乱,占据长安,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这一时期,机务繁杂,千头万绪,陆贽恪尽职守,起草了大量诏书,深为德宗倚重。旋被任命为考功郎中。此时,虽“有宰相主大议”,但陆贽“常居中参裁可否”,被称为“内相”(《旧唐书·陆贽传》)。兴元元年(784),朱泚之乱被平定,陆贽被授予中书舍人。贞元八年(792),陆贽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成为宰相。任职期间,他对“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 (《旧唐书·陆贽传》),为德宗所重。后因受裴延龄等的排挤,陆贽于贞元十年(794)十二月罢知政事”,次年又被贬为忠州别驾。顺宗即位后,下令召陆贽还朝,但是诏书未至,陆贽就病逝了。终年五十二岁,赠兵部尚书,谥宣。其著作主要收录于《陆宣公翰苑集》(二十四卷)。
陆贽从政的时期,唐朝开元之际的强盛已不复存在。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是藩镇割据、分裂混乱的局面也就此形成。唐王朝由盛转衰。唐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虽被称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 (《旧唐书·陆贽传》),但实际上缺乏相应的胆识和才干。他处置不当,致有朱泚之乱,自己也被迫出逃。他虽然有求贤之心,却不善于识人、用人,以致“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 (《旧唐书·德宗下》)。陆贽“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 (《旧唐书·陆贽传》),对政局紊乱,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深感忧虑。他全身心投入于繁忙工作中,积极建言献策,希望德宗能励精图治,以挽回颓势,重振唐朝雄风。他写下了大量奏疏,阐述自己的见解,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其在行政方面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
重人事、轻天命——务实、进取的行政理念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它对社会生产和政治秩序都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后盛唐景象不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藩镇据地称雄,不服调遣,谋叛之事时有发生。德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皇位的。即位不久,就遭朱泚之乱,仓皇出逃。德宗遭此变故,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 (《旧唐书·陆贽传》),即认为国家的兴衰完全取决于天命,当前的危局都是天命使然,非人力所及。陆贽对他的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重人事、远天命的思想,主张积极探求摆脱困境的良方。
首先,他上书批驳了德宗的消极思想。他指出“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 (《旧唐书·陆贽传》),即以兴衰系之于天命是不对的。他引用了古代典籍和圣贤的有关论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易》说:“自天祐之。”仲尼说:“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通过这些,陆贽向德宗表明,“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天人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旧唐书·陆贽传》)。总之“天命在人,盖昭昭矣”,天命决于人事,“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 (《旧唐书·陆贽传》),天命因人事治乱的不同而异。故此,应将注意力从对天命的关注、依靠上转到对人事的重视上,妥善处理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
其次,面对天下动荡不安的局面,陆贽鼓励德宗树立起信心。他说:“治或生乱,乱或资治” (《旧唐书·陆贽传》)?,即治可能生乱,乱也可能变治。治乱都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可以相互转化。他又说:“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 (《旧唐书·陆贽传》)?,国家有未遇困厄而败亡的,也有屡遭变乱反而兴盛的。因此,变乱、困难并不可怕。他接着分析说,治而生乱的原因在于“恃治而不修也”,以治为恃,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肆意妄为;乱而达治的原因在于“遭乱而能治也” (《旧唐书·陆贽传》),虽遭变乱而能积极求治,妥善处置。所以,治乱转化的枢纽还在于人事。无难而失败的原因是“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即丧失了谨慎畏惧之心;多难反而振兴的原因是“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 (《新唐书·陆贽传》),即在实践中懂得并做到了敕慎。所以,困厄并不可怕,保持信心,通过谨慎认真地处理可以化解,转而谋得振兴。他向德宗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具体就是要“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 (《旧唐书·陆贽传》),即要约束自己,遵从道理,亲贤远佞等。做到了这些,还“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旧唐书·陆贽传》)天下太平,国家振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总之,陆贽反对畏惧、依赖天命的消极观点,认为天命在人,主张振作精神,积极求治,实现国家复兴。在政治理念上,这是对汉代以来崇尚天命观念的一种否定,表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也是一个务实政治家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寻求救危解弊之方的合理性选择。这种积极奋发的精神贯穿于陆贽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之中。
居重驭轻——行政控制思想
唐朝设立藩镇是为了保卫边境。唐睿宗时,出现了节度使的官名。唐玄宗时,增设了藩镇,并扩大了节度使在军政、财政、民政方面的权力,节度使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北方重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更一人兼领三镇节度使。他们就是凭此发动叛乱的。在平叛斗争中,为了招抚叛将,奖赏功臣,又增设了许多节度使。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实际是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势力。他们不由中央任免,其职位多由子侄或部将继承。他们还自行征收赋税、任命将吏,招募军队,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藩镇割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造成了国家的事实上的分裂,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原则被破坏。其次,他们不向朝廷纳税,使中央财政状况恶化,只得增加赋税,但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再次,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不时发生军事冲突,社会陷于动荡之中。沉重的赋税、连绵的战乱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因此,要想重振唐朝,藩镇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陆贽是中央集权和皇帝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的坚定拥护者。他对“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 (《新唐书·陆贽传》)的混乱局面非常忧虑。他积极主张削弱藩镇势力,重建中央和君主的权威。
在给德宗的奏疏中,他明确指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 (《新唐书·陆贽传》),即须审明轻重,保证本大末小,才能使国家稳固。他通过一个比喻对其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 (《新唐书·陆贽传》),即认为身使臂,臂使指之所以能运作自如,全在于其大小比例合适,治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里,他以王畿为四方之本,以京邑为王畿之本。他认为京邑相当于身,王畿相当于臂,四方相当于指,这就是“天子大权也”(《新唐书·陆贽传》)。他指出前代转运天下之租税,迁徙郡县的豪杰,充实京师,都是致力于巩固国家根本之地。他回顾历史,指出唐初太宗推行府兵制,“列置府兵八百所”,其中五百在关中,使中央拥有足以控制全国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的局面。这是“居重驭轻” (《新唐书·陆贽传》)战略意图的体现。这一举措有力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也是唐朝很快进入全盛期的一个原因。
然而,太平日久,再加上社会变动如均田制破坏、官吏腐败等,府兵制逐渐被破坏,武备废弛,藩镇的势力却发展起来,居重驭轻的局面被打破,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得以以“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 (《新唐书·陆贽传》),唐朝也走向衰落。
可见,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统治的稳固就必须厉行中央集权,实行强干弱支,内重外轻的政策。然而肃宗、代宗都推行姑息政策,藩镇势力得到发展,气焰十分嚣张,同时又有“吐蕃乘虚”(《新唐书·陆贽传》)。到德宗时,在军事上更是穷于应付,军费开支浩大,又被迫增加捐税,这更加重了社会矛盾。
陆贽认为关中是“王业根本在焉” (《新唐书·陆贽传》),必须保证其安全。而“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 (《新唐书·陆贽传》),即应将人才、财富等聚集于关中,使之处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样“一朝有急,可取也” (《新唐书·陆贽传》),发生变乱时,可取而用之。在军事部署上,也要围绕确保关中,强干弱枝的原则进行。藩镇割据是对君主专权和中央集权的严重破坏,危及到李唐王朝的根本利益。陆贽主张巩固关中根据地,逐步削弱藩镇势力,重建大一统局面。其观点是切中时弊的,但没有得到实现。
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和权力划分上,陆贽主张维护中央权威,集权于中央。应该承认,在当时君主政治的条件下,只有统一,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差距显著,统一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陆贽的观点可以给人们提供认识上的参照。
改过与纳谏——行政调节思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是权力的中心,对国家的军政、民政事务有最高决定权。然而,君主的能力、才智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私欲作怪,其行为、决策出现过错,甚至损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也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臣子为君主出谋划策,弥补其才智的不足,还要及时进谏,帮助君主认识、纠正错误。同时,君主也应广开言路,主动纳谏,正视自己的过错,勇于改过。
首先,纳谏是君主的美德之一,是明君的重要特点。陆贽将“谏而能从,过而能改”,视为“帝王之大烈” (《新唐书·陆贽传》),对两者非常看重。他说唐太宗的“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谓盛矣”,即太宗功德卓著,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 (《新唐书·陆贽传》),即人们如今最赞赏和怀念的却是他能纳谏和改过。
其次,纳谏的意义。当德宗问他“事切于今者”时,他回答说“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即要积极听取臣下的意见,这样才能“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 (《新唐书·陆贽传》),使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为正确决策、行政提供智力保障。
对于过错,他引用《传》中:“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话表明,过是难免的,过而能改才是大善。他发现历史上对圣君、明主“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 (《新唐书·陆贽传》),改过、补阙的行为受到普遍的称赞。而且“能改而之善”是智者才能做到的,愚者则只能“耻而之非也”,智人、愚人对过错的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因此,改过既是美德,也是智举。君主应端正对过错和谏诤的态度,勇于改过和纳谏。纳谏有弥补君主智能不足,帮助君主发现、纠正过错和失误的作用,对君主和政治都有益处。
再次,君主需有纳谏的意识和胸怀,要切实做到诚信。德宗说:“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又说:“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新唐书·陆贽传》),怀疑进谏者的动机,认为他们借进谏发泄私愤,牟取私利。陆贽则不赞同他的看法,希望德宗能以诚、信的态度对待臣子及其进谏举动。他表示“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已”(《新唐书·陆贽传》),不能没有诚信。他说“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 (《新唐书·陆贽传》),诚和信都是根本性的东西,缺乏诚信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新唐书·陆贽传》)君主要求他人诚信,自己也要做到诚信。他坚决反对诚信致害观点,认为不能因噎废食,“毋以小虞而妨大道” (《新唐书·陆贽传》)。
其四,去九弊,疏通上下交流的渠道。他认为“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新唐书·陆贽传》),上下之间有沟通、交流的愿望与需要。然而,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是“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新唐书·陆贽传》),上下之间沟通受阻。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九弊。其中,上有六:“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新唐书·陆贽传》)。下有三:“谄谀、顾望、畏懦”(《新唐书·陆贽传》)。陆贽重点强调的是居上位的人应着力避免的方面。他分析认为“好胜而耻过”就会喜欢听谄媚之词而厌恶直言,从而使“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新唐书·陆贽传》),阿谀奉承者得到好处,而听不到忠直之言;“骋辩而炫明”则“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新唐书·陆贽传》),自以为是,妄加猜测,使人不能尽言其所想言;“厉威而恣愎”,则“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新唐书·陆贽传》),不能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批评,使合情理的意见也无法申明。陆贽认为只有革除这几种弊病,才能使上下之情互通。信息流动的顺畅是正确决策和政治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陆贽对这一点的重视是得当的。由于沟通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在上位的人的态度、做法怎样,所以他重点强调了在上者应注意的问题。
改过与纳谏涉及的是行政运作中的调节和制衡的问题。适当的调节和制衡使政治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不致于走向僵化。重调节,不偏执,是儒家的一贯主张,陆贽也继承并阐扬了这一点。不过尽管陆贽言辞恳切,但德宗并非一个圣明的君主,很难真正做到改过和纳谏。
求贤、用贤、管贤——人事行政思想
首先,积极求贤。欲稳定形势,谋求振兴,首先遇到的就是人才问题。形势的发展急需培养一支忠君爱国同时又富于政治才干的官员队伍。陆贽曾担任过主管官员考课的考功郎中,后来又担任过宰相。因而对当时在人才的选用、管理上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他在作了宰相后明确宣称自己:“唯知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旧唐书·陆贽传》),将人才的选用,官员的管理当作自己的要务。
其次,选才用才方针。在人才选用上他主张“求才贵广”,在官员管理上主张“考课贵精”(《旧唐书·陆贽传》)。所谓求广指“各举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即要广泛地、多途径地选拔人才,贵精指“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旧唐书·陆贽传》),即要对人才视实际表现进行严格的考核。他对武则天时期人才的选用和管理的情况非常赞赏。他说武则天践祚临朝,主持政务期间,因为“欲收人心”,而“尤务拔擢”,积极地选拔人才。他说当时武则天“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求才用贤的热情是很高的,而且“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旧唐书·陆贽传》),人才进用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当然“所荐必行,所举辄试”(《旧唐书·陆贽传》),也使人才进用显得过于容易了,质量难以保证。于是其后对人才的任用、考核、汰选就显得很重要了。正是由于当时“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严格的管理使有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不合格者被淘汰。所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陆贽传》),朝廷善于识人,发现、任用的人才也很多。陆贽认为这种状况就是“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结果。
他认为德宗“思致理平”,其“好贤之心,有逾于前哲”,也希望延揽贤才,然而要论“得人之盛”,却“未迨于往时”(《旧唐书·陆贽传》),情况并不好。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德宗“赏鉴独任于圣聪,搜择颇难于公举,仍启登延之路,罕施练核之方”(《旧唐书·陆贽传》),选拔和管理上都作得不好。武则天举用人才的方法,“伤易而得人”,虽然过于容易,却能够得到人才,而德宗所采取的方法,“太精而失士”(《旧唐书·陆贽传》),难以得到人才。这种不当的做法应该改变。他还主张允许台省长官推举人才,自荐属官,增加人才选用的途径。
再次,官员的考核和评价。他认为考核的主要方面包括户口、垦田、赋役、按籍、囚系、奸盗、选举、学校等。通过对这几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个人的实际才干如何,是否称职,从而能合理使用人才,因能授职。考核的结果将作为升迁、奖惩的依据。他主张对于才能出众的要予以拔擢,失职的要予以罢黜,对守常的人则依序而进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这样可以促使官员积极上进,提高官员队伍的素质和工作效率。
官员队伍的素质和官员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效能。陆贽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思考了官员录用、考核、评价等问题。其中的一些看法也是值得今人注意的。
陆贽的行政思想体现了儒家学说正面、合理的方面。他面向现实,积极进取,维护国家统一,重视官员选用和管理,注重政治调节的观念,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实用性,对于现代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唐)陆贽.陆宣公翰苑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刊本.
作者简介:刘学斌(1977-),男,山西长治人,博士后,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讲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研究人员,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政治思想史》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