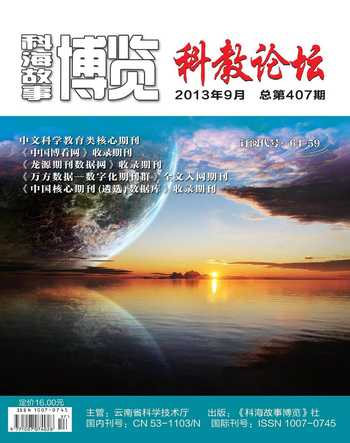浅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文化学途径”及“泛文化”
摘要:翻译与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应该同时注重文化学途径和语言学途径的结合,使译文在回归文化本性的同时能够体现语言关联性。本文分别阐述了翻译的文化学途径和语言学途径,并对现今存在的翻译“泛文化”现象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翻译 语言学途径 文化学途径 泛文化
引言
翻译,就笔者作为一个语言教学的学习者身份来看,其就是运用语言这个载体来进行不同文化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语言是工具,文化是内容;而且翻译也能为语言的教与学提供一个沟通的桥梁。注重语言的流畅还是文化内容的转化与保持?众说纷纷,但可以知道二者应该相互权衡,缺一不可。那么,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文化信息的时候,应该怎样把握它的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让翻译学----这门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的学科,能够忠于其功能本质,服务于语言文化的交流(这里说的“服务”可能过于牵强,但是我们终观翻译的研究,就可以得到一些解释和启迪)。翻译是一个跨语言与文化交流的过程,它通过目的语“再现”
的方式把源语言的信息表达出来,帮助目的语读者了解原作者意欲表达的信息内容并获得与原作者和源语言读者感同身受的思想体验,翻译的目的实质是为了帮助那些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进行信息与情感的交流;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思维再创造”的过程,但“创造”不代表无规则,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与原则。忠实和通顺是两项最基本的要求(贾文波,2004)。那么这里的“忠实”和“通顺”该作何解释?就笔者看来,“忠实”,顾名思义就是要忠于原文的文化内涵、忠于原文的本性;“通顺”,其就是要译者注重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表达方式的语言学途径,即语言的关联性。那么,显然,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学途径与文化学途径应该是互相结合的。
一、翻译的“语言学途径”
最近十多年来, 国外出版了不少用功能语言学(这里所说的“大功能”与N.Chomsky的形式主义相对而言,包括语篇分析、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认知语义学、语用学、认知功能学等)作指导的研究翻译问题的文章和专著(黄国文,2004:16),即用语言学这门学科来指导翻译学科的进行。而奈达也认为翻译研究有四种途径:1、语文学途径(philological approach);2、语言学途径( linguistic approach );3、交际学途径(communicative approach );4、社会符号学途径( sociosemiotic approach )。关于翻译的语言学途径的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一门科学,而翻译学不单单是研究翻译的科学,笔者认为它更是一门艺术,因为科学讲求实际与关联,而艺术讲求表达的美感,比较艺术与科学,只有艺术才会用“雅”来阐述与修饰。对此,笔者查阅资料时也发现,奈达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并试图将语言学、符号逻辑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融于翻译学科。但在后期的论文中,其改变了立场:认为“研究翻译理论是科学,而翻译本身是一门艺术、技巧,不是科学”。这种解释似乎对他早期的翻译语言学途径进行了否定。但这是不是就说明语言学途径完全没有优势呢?其实不然,强调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不但可以表达出连贯语言之美感,也可以在一些结构复杂的句式中帮助译者理清思绪,以便译出通顺流畅的译文,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语言之美。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主要是关于两种语言的对比,即原文与译文的句式、词法、形式、篇章等的对比,以便加强译文语言的关联性。就笔者涉及过的英译汉或者是汉译英的方法和技巧都是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为基础的。国内学者邓巧玉也同样认为:对于英汉翻译实践来说,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 尤其是相异之处,从而掌握它们的特点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比,掌握两种语言的特点,在翻译时就可以自如地运用这些特点,还可以使我们重视一切难译的地方,认真研究同一思想内容如何用不同语言形式来表达的问题(邓巧玉,1999:61)。可见重视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为我们得到结构严谨的译文是大有益处的。
二、翻译的“文化学途径”
关于翻译的文化学途径,笔者认为应先理解什么是文化。而“文化”这个概念极为抽象和复杂,国内外的学者已先后对它下过近200种定义,但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里,笔者选取蔡荣寿学者的定义,即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蔡荣寿,朱要霞,2009)。笔者认为,文化的内容是一个复杂的但又不失完整的真实的表述,不能曲解,不能会错源文化的思想内涵,因此任何翻译都要考虑文化的差异性、普同性、社会性、发展性及功能性,翻译才可能达到让读者理解的同时也不失原文的文化本性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蔡荣寿,朱要霞,2009)来说明:
1.“亚洲四小龙”
误译:the four dragons of Asia
正译:the four tigers of Asia
分析:因为在汉语中“龙”多表达的是褒义,如“龙凤呈祥”、“龙马精神”、“龙腾虎跃“等。而“龙”在英语里对应的词是“dragon”,在英美文化中,“dragon“代表凶残的怪兽,是邪恶的象征。所以“亚洲四小龙”译为英语的时候不应该用“dragon”,而用“tiger”代替。那为什么这里要用“tiger”来代替“dragon”呢?笔者通过维基百科查阅到: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及说英语的非西方国家中,比如印度和孟加拉国,“tiger”代表着耐心、专注、坚定、警觉、深思熟虑的品质,而且在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韩国,“老虎”也有着“王”的象征意义,即对应英文的“king”。据全球唯一一个以动物为主角的电视频道:Animal Planet(动物星球)通过超过50000名来自73个国家的观众投票调查获知(维基百科):老虎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狗,被评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动物,老虎获得了21%的选票,狗20%,海豚、狮子、马分别是10% 、13%、 9%,蛇8%,这里有一个文化的共性在里面,所以这样才能让英语语言的读者真正理解“亚洲四小龙”的含义,也不会曲解了我们中国的“龙”的含义,否则就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像这样的中西文化差异的词语还有很多,比如:“红色”、“六”、“collectivism”、“capitalism“等。
2.Hawkes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译为“God bless
my soul.”用上帝来代替佛教的寿佛。这可能让西方人误以为我们中国人也信上帝。这样的译文就会大大削减中国的文化内涵。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翻译需要考虑双语的文化链接、共性和差异,并相应“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给译者带来更多更严重的复杂情况。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笔者发现,很多人常把翻译这门艺术比喻成“带着镣铐跳舞”,以强调翻译所受的文化约束。因此,在我们翻译是时候,了解并熟悉目的语及源语言的文化是必然的,这样做出来的译文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才会到达交流及共鸣的作用。但是过多强调文化途径是否就是上上策呢?其实不然。蔡荣寿认为,翻译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并受文化的制约(蔡荣寿,朱要霞,2009)。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文化”因素给予过多的考虑是不是就是权宜之策呢?周晓梅认为,对于外部因素的过度关注就会造成翻译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这导致了研究的分散性和无深度性(周晓梅,2012)。显然,如果过度地重视翻译的文化学途径而忽略了翻译的语言学途径,那么所得到的译文必定会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没有严谨的结构的文章不叫文章,最多是句子的拼凑罢了,这对于翻译实践来说注定是失败的。据此,要想得到一篇成功的译文著作,同时兼顾翻译的“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这条原则是译者必须坚持的。
三、翻译的“泛文化”现象
现如今,全球化加快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我国翻译学研究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即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文化转向”,它改变了传统翻译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据此,笔者查阅文献发现研究者将之前的关注点由文本内部语言结构因素转向了外部文化渲染因素,这不仅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内容、新视野,也扩大了宽度,增加了深度,让人们感受到翻译活动的丰富多彩,意识到翻译的多方延展,发人深思。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负面情况———很多研究渐渐偏离了翻译学本性,出现了“泛文化”的倾向。所谓翻译的泛文化现象,是指在翻译学研究中,不将翻译活动作为实际考察的对象,而把从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中借用来的概念、术语、命题等作为研究内容,进行阐释和讨论(周晓梅,2012)。笔者发现,在我们译注的过程中,将两种语言进行转换,为了满足目的语的文化需求,就会违背本土语言的文化内涵,可到最后也无法完全将目的语的文化内涵融入到译文中去,同时也失去源语言的文化本性,于是乎,两者兼失。根据周晓梅学者的研究,笔者总结发现,泛文化现象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翻译理论无根基性;2.翻译研究无系统性;3.深度研究的“平面化”;4.翻译文化的误读误用。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怎样克服泛文化现象及其引起的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1.应该回归本体的翻译研究根基;2.坚持翻译的初衷:忠实与通顺;3.不能胡乱添加任何无关联的成分4.不能够生搬套用其他学科的内容。翻译研究中对文化的关注本来是为了在翻译中更好地保留“异文化”信息,以达到平等交流的目的。但是周晓梅认为,翻译学研究者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他们没有认真消化吸收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更没有将其内化为翻译学本身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翻译学学科扩大的同时,学科边界被模糊了,或者说整个学科也被泛化了。在一些人主张一切都是翻译时,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被消弥,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也混杂不清,让人无法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与特征(周晓梅,2012)。如果是这样,那么“翻译”这门学科就会失去其本性了。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这个时代,如何保持翻译不被“泛化”是值得翻译研究者共同努力的。
四、结语
翻译中需要对等的综合性关系。对于现如今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它的走向必然是语言分析与文化判别的结合,我们应该好好审视翻译的本位研究,给予其正确的定位,树立正确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并正确对待其间的关系,运用语言学的科学理论去处理翻译文本的结构,然后有效运用翻译的文化观保留译作的本土文化,并同时融合目的语的文化知识,注意学科间的相关性,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不能偏离文化的主体,克制泛文化现象,并依靠艺术的眼光、语言素养和文化修养,全面细微地考虑各方面因素以期得到一部优秀的译作。
参考文献:
1.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 黄国文.翻译的功能语言学途径[J].中国翻译,
2004,(5):15-19.
3. 邓巧玉.翻译的语言学途径[J].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61-62.
4. 蔡荣寿,朱要霞.翻译理论与实践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ger_worship
6. 周晓梅.对翻译学研究中泛文化现象的反思与批判[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5):72-75.
7. 张艳丰.再论奈达早期翻译理论中的语言学途径,http://www.cnki.net.
8. 许钧.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J].南京大学学报,
2002,(3):219-226.
作者简介:胡启琴,女,贵州贵定人,中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磨蚀,语言教师发展,语言翻译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