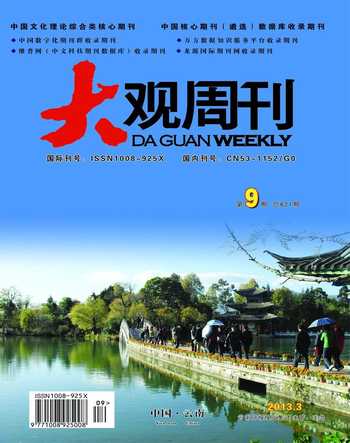逮捕必要认定实务探究
常传龙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11(2013)03-0026-02
摘要: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对逮捕必要作出准确认定是适用逮捕措施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侦查机关以有逮捕必要为由报捕,检察机关以有逮捕必要而批捕或无捕必要而不捕,故逮捕的实质是对逮捕必要性之判断。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规则对逮捕必要性标准作出一些规定,但是实践中对逮捕必要认定标准仍因人因案而异,故有必要对逮捕必要认定进行探究和完善。
关键词:逮捕必要 无捕必要 实践完善
人身自由对人至关重要,而逮捕即是通过行使公权力对此进行限制。逮捕权作为公权力即应受公权制约和私权限制,即逮捕的启动、决定、执行由不同机关分别行使而得以制衡,以有必要才适用而得到人权保障的限制。但实践中的逮捕却呈某种畸形化发展趋势,逮捕的不当适用使其未能保障人权反而威胁着人权。新刑诉法及刑事诉讼规则对逮捕适用作出了修订,既是逮捕制度的发展,也体现了对行使逮捕权的高度重视。故应在实践基础上审视逮捕,使逮捕目的与刑事诉讼目的保持一致。
一、逮捕实践浅探
(一)审查批捕结果
一般而言,逮捕以侦查机关报捕启动,以侦监部门审查、检察机关决定而适用或不适用。实践中审查逮捕后有逮捕和不逮捕两种,其中逮捕分为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不逮捕分为不构成犯罪不捕、证据不足不捕、符合监视居住条件不捕、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其他不捕。虽然实践中逮捕的比例远高于不捕,但捕应以不能不捕为由,因此更应关注不捕的几类。其中不构成犯罪不捕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行为不是犯罪,常被称为“绝对不捕”;证据不足不捕是因证据问题使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达到追诉标准,也称为“存疑不捕”;其他则属于“相对不捕”。[1]因实务中常常注重于事实证据的审查,前两种不捕要求较高、案件数量也相对较少,而相对不捕则在逮捕权自由裁量范围之内,数量也较多。
(二)批捕实务隐忧
1.构罪即捕的风险权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构成犯罪能够导致逮捕适用,但实务中构成犯罪必然导致逮捕适用却成了常见现象。事实上,构罪即捕的决定可能多数是正确的,但是其侵犯嫌疑人权利或威胁审判权的风险要大于其正确决断的风险。由于构罪即捕未考虑到刑罚条件和危险性条件,对没有社会危险性、可能判处轻刑的犯罪嫌疑人,法院基于捕后无罪或轻罪检察机关将要赔偿或考核不利的考量,作出的判决期限不会短于羁押期限,否则将面临抗诉风险。此外,在经法院判决有罪的刑事案件中,95%以上的被告人都被采取了逮捕这一强制措施。[2]事实上,有经验的检察人员只需根据强制措施即可大致判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将会得到的惩罚。一个人有罪只能由法院认定,但是实务中的逮捕与有罪数量关系上呈极大相关性,不当逮捕也直接影响判决结果,这是对刑事审判权的极大威胁。
2.逮捕的刑罚条件已形同虚设。逮捕只能适用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刑法中除了常见的危险驾驶罪等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外,其他都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基于对“可能”的不同认知,审查人员常将该刑罚条件作为一种极容易达到的要件甚至于忽略不考虑。适用逮捕是基于对行为人行为的初步评价而做出的决定,此时审查人员的判断即应类似于法官行使刑罚权,即通过证据审查内心确信行为人当然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只因审查权不是审判权,该处的“可能”应是审查人员内心的“应当”。逮捕的刑罚条件看似简单,实质上却涉及专业化的刑罚裁量,故常常为多数人所忽视。
3.必要性认定的瓶颈。根据新修订刑诉法,逮捕必要性是指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根据取保候审和逮捕适用的条件可知二者的适用临界点在社会危险性上。而逮捕必要性认定之所以不能充分全面展开则在于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上。一是侦查机关同时为报捕机关,受了解案情先入为主的侦查模式影响由其提供的必要性证明材料的客观性难以保证,而事实上实践中侦查机关也极少提供这方面证据材料。二是新刑诉法将律师介入诉讼时间前移以保证嫌疑人权利,但新刑诉法实施半年来我院在审查批捕阶段尚无一名律师介入,但律师在协调当事人赔偿谅解等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三是社会危险性认定业已与实践错位。比如,大多数报捕案件侦查机关已用尽侦查拘留期限,在基层侦查实践中,报捕案件大多证据已基本查清,有的甚至批捕后即移送起诉,那么又何谈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二、审视逮捕要件与适用
(一)逮捕要件的内在逻辑
如前所述,一般逮捕需具备三个要件,笔者认为,该三要件具备两个逻辑:一是三者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二是三者层层递进、核心在必要性。不言而喻,逮捕三要件当然需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实践中逮捕的另一个逻辑却极易被忽视。逮捕的适用即是第二个逻辑的再现。如,某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因不符合刑罚条件,一般不捕;而某人涉嫌交通肇事致两人死亡,可能处三到七年徒刑,但如有赔偿达成谅解,可因不具备社会危险性,一般也不捕。据此可知,逮捕是否适用不在于证据和刑罚要件多么充分,而在于此基础之上的必要性判断。故逮捕实质是对逮捕必要性的判断。
(二)逮捕需慎用
如上所述,逮捕实质是对必要性之判断,因必要性判断体现很大的自由裁量,实践中的逮捕则需慎之又慎。在英美法系国家及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出逮捕是一种司法审查行为,由法官进行审查,体现的是逮捕严肃性、终极性。而我国逮捕审查则由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办理,既缺少法官视野下的专业性,又缺少法官必备的中立性。因此实践中的逮捕必须慎之又慎,当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也能达到良好效果时,必须排斥逮捕的适用。[3]我国的强制措施是一个有机体系,五类措施适用都有临界点,比如基于保障人权又能打击犯罪的目的,可以同时适用拘留和逮捕时应优先适用拘留。目前应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下综合适用五类强制措施,使采取强制措施目的统一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辩证关系中。
三、无捕必要的困境与出路
设置无捕必要不捕目的在于限制适用逮捕,捕之必要是逮捕适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体现刑诉法之谦抑性。我国无捕必要的规定多数在高检院检委会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中,而新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则在此基础上将无捕必要的标准予以法律上吸收确认。但实践中该规则对无捕必要适用期望并未有预期之高。
(一)无捕必要适用在刑诉规则与刑诉法证明上的冲突与化解。
刑诉规则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了可以不捕的特定情况,加之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使不捕决定有了明确依据,很显然这有利于提高逮捕质量。但是在证明机制角度上却不利于人权保障:根据刑诉法第七十九条,审查人员需审查证据以证明存在某种社会危险性,而这里则需审查特定情形的证据比如是否赔偿、是否有帮教条件等,事实上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具有不充分性和偏见性,可想而知,审查后适用该规则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实践中,侦查机关很少去收集学生或未成年人帮教条件证据、甚至也有未开具学生身份证明的。此外,犯罪嫌疑人案发后即被拘留,其赔偿及赔偿意愿也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厘清刑诉法和刑诉规则的关系,刑诉规则以刑诉法为依据制定,有不全面之处当然应以刑诉法为根本准则。实践中应当将规则作为无捕必要的具体参考依据而非唯一适用依据。审查人员仍应当首先依据刑诉法79条对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若存在刑诉规则规定的特定情形,则应尽可能适用以保证犯罪嫌疑人适用较轻的措施。
(二)刑罚条件解释的瓶颈与突破。
刑诉规则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但是罪行较轻却无衡量标准,这就给该规则适用带来了难题。很多人认为应以缓刑最高期限三年为分界,三年以下为罪行较轻。[4]且贵州省院《人民法院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有一条规定“犯罪较轻(指法定刑幅度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5]此处“犯罪较轻”也有了较为官方的释疑。笔者不赞成以三年分界划分较轻与否,因为只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重罪是必捕的,十年以下则都存在不捕的可能性。另,“罪行较轻”和“犯罪较轻”也是出于不同阶段不同人视野中。罪行较轻是一种对罪行的动态衡量,而犯罪较轻是基准刑的静止评判。如,某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徒刑但是存在多个应当减轻的情节,显然不属于犯罪较轻,但是却可能实际判处三年以下,属于罪行较轻。
事实上,1962年美国法学会拟制的《模范刑法典》按刑罚轻重就把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微罪、违警罪四等。[6]很多国家也有轻罪重罪的划分。笔者认为,应当以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相结合,将轻罪、较轻罪、较重罪和重罪与刑法中的常见刑期界点联结。根据目的解释,逮捕中罪行轻重应以有利于无捕必要的扩大适用为目的。对作为公权力的逮捕应合理限制,对私权利扩大解释在法治国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故,轻罪、较轻罪、较重罪、重罪的界点应分别对应三年、七年、十年。相应地,罪行较轻则可以是七年以下徒刑。这也符合交通肇事罪致两人死亡且有赔偿谅解而由公安机关直接取保的实践。
(三)考虑固定因素的局限与突破
刑诉规则一百四十四条的适用,除了需具备罪行较轻且无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之外还需具备其他分组的因素,如第五项中未成年人且悔罪表现且帮教条件,该项分组因素有三个且被固定化,笔者暂且将改组因素称作固定因素,而这些证据因素的全面性收集恰恰是侦查机关所忽略的。刑诉法实施半年来,我院办理的未成年案件中也从未出现过侦查机关向家庭、学校、社区收集帮教条件证据的案例。因此笔者认为,该规则中的固定因素与其他非固定因素应综合运用,不拘泥于同时具备某一组因素。固定因素是认定不具备社会危险性可操作性的依据,但不应是唯一依据。如我院办理娄某涉嫌寻衅滋事案中,因娄某是近临中考的初中学生,案发后有悔罪表现,只是侦查机关未收集帮教条件方面的证据,那么就不能直接以该规则对其不捕。此外,该规则中因素分组后一些条件就难以具备,如蒲某涉嫌故意重伤害案,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后被拘留,因家中妻离子幼父母年迈病重未能协调赔偿谅解,也不能直接使用规则对其不捕。因此应突破该规则的固定分组因素局限性,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直接以刑诉法七十九条为最终依据。
(四)其他因素对捕之必要的影响
根据刑诉规则一百四十四条列举的各组因素,可以对某些嫌疑人不捕,但是对案件社会影响、受害人意见、家庭条件等因素是否予以考虑呢?如范某某涉嫌强奸案,范某某与其未满十四周岁的女友发生性关系并生有一子由范某某母亲抚养,若以涉嫌强奸罪逮捕范某某势必将增加社会矛盾。再如前述案例,蒲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自首后被拘留,因家庭经济困难难以作出赔偿而被捕,倘若不捕蒲某则其有通过劳动或筹钱在审判前赔偿受害人的可能性。故笔者认为,各项不捕因素不能机械适用,而是应有符合逻辑的证明机制,只要存在证据证明不存在社会危险性且能够相互印证则可认定不具备社会危险性。
四、结语
逮捕是一种重要的诉讼保障性措施,但是能否用好逮捕这把限制自由的利刃却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今后有望通过逮捕必要性证明说理机制以及律师介入对抗机制等途径使逮捕更加透明化规范化。逮捕必要性考量毕竟是一种自由裁量,因此也需要有经验的审查人员来行使批捕权,有望将实践中常见的必要性认定因素予以法定化。
参考文献:
[1]徐剑峰,费志国,马红文.审查批捕环节刑事和解初探[A].法制与社会,2011-04.
[2]孙谦.逮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4.
[3]孙谦.逮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8-89.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4.
[5]2010贵州省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三[M].14(7).
[6]储槐植.美国刑法[M].第二版,19.